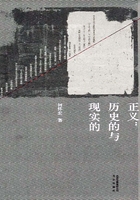毋庸置疑,李叔同先生赴日学艺,肯定不是仅出于一己的爱好,其最主要的,应该是姜丹书先生在《弘一法师传》中所说的,乃是抱着一种“美术淑世”的理想。或以为,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作不得数。“孤证不立”,那么,前引那阕《金镂曲》中的词句,还有李叔同先生在日本成立剧社制定章程时所引他以前的诗句:“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及在春柳社成立时提出“改良戏曲,为转移风俗之一助”的宗旨,可谓是夫子自道了吧!当然,这也可以不算,因为有人可能说这是自视过高,自我感觉太好,自我拔高之语。那么就再举证。李叔同先生在留学期间曾创办过中国近代第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是刊“叙”中,李先生极其鲜明地指出,艺术具有“琢磨道德,促进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之功能,其“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实乃超出一般,“宁有极矣”。这段文字,无疑就是李叔同先生的艺术观,也可视为他留学日本专攻美术的指导思想。还有,与李叔同先生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并一起从事艺术实践与活动的而后成为卓有成就的戏曲艺术家欧阳予倩先生曾对那段历史做过这样的回顾:“老实说,那时候对于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息霜(李叔同别字)。”这段话应该算得上是“当事(时)人”的“举证”了。毫无疑问,所谓“见解”,当指一种明确的艺术观,而消遣玩玩之类的想法是谈不上什么见解的。诚然,李叔同先生确是有他的独到的艺术见解。倘若没有那种明确的艺术观的话,李叔同先生又怎么有可能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作出许多伟大的成就来呢?事实就是如此!
刻苦,勤奋,生活严肃,这是李叔同先生在留学期间给人留下的印象。这样一种学习生活的态度,显见得不是那种抱着好玩或镀金之类心态者会有的。李叔同先生是中国留学生考入日本美术学校的第一人,除在美校专攻绘画外,李先生还到音乐学校学习琴艺,又走访戏剧家学习戏剧艺术,无不取得显著的成就,许多的艺术实践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都居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在日本学艺期间,李先生还办艺刊、建艺社,演剧赈灾,从事多项艺术活动,无形中成为当时这批留学生中的核心,并使李叔同先生成为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具有诸多“第一”的艺术家。如此等等,这些事实,想进一步具体了解的读者,在相关的历史资料上是一查即可找到的。正因为李叔同先生有自觉的救世淑世意识与明确的艺术观,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以至于到了他出家后,不要说国人,就是当初与他有过接触,对他有点了解的日本人也会不时地提起他。以至于后来伶界在梅兰芳等走红后,东洋人士依然会说:“倘使自‘桩姬’(引按,即茶花女,李叔同先生在日本时曾演过这一角色)以来,李君仍在努力这种艺术,那末岂让梅兰芳、尚小云驰名于中国剧界。”如此等等,仅仅是因一代才子弃舍红尘而令不能理解者生起惋惜之情吗?或他的出家实在太富戏剧效果,而使得世人禁不住要挖掘一切与他相关的内容来敷衍说事吗?有这个可能。然即使如此,这本身也是“弘一现象”的一个因素。但如果说事对象平庸无奇不值得一说的话,难道最终不会感到多说无聊,令人生倦吗?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就是不好好去读点书,总不能见好说好,多从正面挖掘、欣赏、赞叹正面人物的正面价值,总是凭想象怀疑甚至矮化历史上一切正面的人物与之事。就像如今一类知识人士,好戏论历史,往往将坏的说成好的,高的说成低的,无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理想与价值,以为能颠覆传统,将一切是非价值抹平,才显出水平,才具有现代意义,才是所谓的理性态度。所以在这类问题上,并非仅仅是反映在如何对李叔同先生日本留学意义的评介上,实是关系到一种学问的态度,对传统的态度,而最终又关系到如何建立起人类价值系统,如何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一根本问题上。
其实,以上话题原本是毋须说得太多的。只是今人对历史,对前贤,既无诚意,又乏恭敬心,自以为是,张扬轻狂。对意义世界的事,不是轻忽,就是不屑。
许多明摆着的,甚至是不证自明的事,却偏偏要扮出一副所谓理性客观、审视一切的姿态,凡事怀疑,叫嚷“拿证据来”!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学者,就是比一般大众高明之处。这些人非但自断圣路,还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所谓的知识精英如此智塞福薄(无缘承继前人的好处,这其实无损于古人,说到底还是他们自己没有福报),要指望着由他们来引领时代,让整个社会慢慢好起来,真的要说声“拜托了”!不过,话说回来,正是因着那些俗见陋识,才促使我们感到有必要这般反反复复地强调体现在弘一法师身上的正面价值与意义。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缘起,或者说是我的问题意识。
七、以人格为背景,从事教育事业
再说留学回国后的李叔同先生,其实早已不是像一般所以为的那样,还是青年时代那般的风流倜傥。那时正值民国初年,不少新潮文人大多感到事业有成,来得也容易,难免有点心躁气浮,但李叔同先生则显然与他们不同。先是他在由陈英士先生等创办的《太平洋报》担任文艺主编(一说主编为柳亚子)。报馆里的编辑,都是“南社”成员,他们在工作之余,大多混迹在歌场酒肆,还有那位来自日本的着僧装的苏曼殊也厕身其中,而唯独“弘一法师孤高自持,绝不混入”,完全脱去了旧时公子哥儿的习气(在留学日本时已是如此了)。也正是李叔同先生那不随俗流的表现,所以能给旁人,甚至一般的“小职员”(作者孤芳自称)留下不同凡响的印象。
稍后,李叔同先生脱下西装,换上粗布的长衫马褂,又投身于教育事业。据与先生同时从事教育的同仁姜丹书先生回忆,“上人自为人师后”,即“刻意于本身之修养”,“已为恂恂儒雅之布衣君子”。他的学生曹聚仁也曾这样追思道:“(对于弘一法师)这样艺术天才,人总以为是个风流蕴藉的人,谁知他性情孤僻,律己极严,在外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狷介得和白鹤一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性情孤僻”的老师,对学生却充满着爱心,“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爱是互动的,学生们也自然会生发出对这位“我们的李先生”(这是同学间对李叔同先生带有感情的称呼)一种“最不会使我们忘记”的情感。作为老师的李叔同先生,他对学生的爱,既有具体而微的关心,如学生刘质平、丰子恺等在生活学习上所得到的帮助;更有一种纯是体现在精神上的照明,这是一种更高境界更有感染力的爱,它没有功利,不带夹杂,潜移默化,止乎纯粹,完全是凭借人格的魅力,人格的力量,无言地流向每个人的心田,影响着每个学生人格的发展。诚然,“他平日很少责备学生。然而学生却视之如父兄,从不敢轻慢他”;“所谓‘望之严然而即之也温’,学生对他的衷心折服,纯由他的真诚所感召”。
于是乎,受老师精神的感召,“对于(李叔同)先生的功课(音乐美术),大家都心悦诚服地想做得好;目的不在分数,只是希望先生能因此而更悦,更欢喜”。正如夏丏尊先生所回顾的:“他(李叔同)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其重视热爱的程度,竟然到了把这两门课“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要”。
其中的原因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同时也是“由于他的感化力大”。
但归根结底,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
教课,能得到所有学生的重视;为人,“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按理说,如此的事业与人缘,无疑都可算得上是成功的。
但李叔同先生似乎对此并不满足。他还要追求更大的世俗事业?还要求得更高的荣誉?乃至财富,地位,权力?显然都不是。为方便说明,得先把话题发散一下,谈谈有关知识分子问题。
我总觉得,20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态,可粗分为上半叶与下半叶两大截。上半叶要比下半叶理想,而上半叶也是前期要比后期好。晚清民初一直到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无论新潮旧派,一般都有他们的道德理念,有他们的淑世情怀,有对理想的执著与追求。虽其中也夹杂着不少的功利心,但此功利也并非纯以个人计的,多少带有公心成分在,基本上是出于强国富国的诉求。
至于上半叶后期,已是差强人意,种种蛊惑人心的主义学说层出不穷,义薄耻寡者也渐渐地多了起来,道、道心、道德这类词语则开始慢慢地退出社会的主要话语系统之外了。而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更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愈来愈不像话,乃至于到了现在能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都成问题(那些有职称,有学位,发表过论文,出过著作者与这一身份没必然关系)。
知识分子身份难保,造成这种“集体堕落”的内因外缘多重而又复杂,在此只强调与本文题旨有关的一点,即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往往少有向上一着的自觉,缺乏求道学道之心,更不要说弘道之志了。当然,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良知,不可能为社会提供积极有益的价值理想,不可能成为引领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了。人格出不来,又怎能得到他人的尊重?看清了这一点,读者就会理解如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弘一法师之选择出家学佛作为他的归宿不理解(甚至有认为李叔同出家为的是治疗长期以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实在是因为这个世道下沉得太快,有道心有道德意识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不会去思考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也不会去体会道对人生的意义,更不会理解佛教所说的出家乃大丈夫行为这句话的分量。坦率而论,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假如还算有的话)如果不是那样的不争气,我们的教界如果有不少像(有一小部分像也好)弘一法师那样一心办道,僧格挺立的僧人的话,那么我认为,今天我们纪念弘一法师的意义显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彰显、重要了。也正因为如此,着眼于道(求道、弘道)的层面来发掘、豁显弘一法师人格僧格的特点及其时代价值,才应该是我们今天纪念弘一法师的中心与重心。
八、出家——追求人格的圆满
有了上述这番说明后,或许不用多说,读者也能料到笔者一定会将李叔同先生最终进入佛门视为向上求道的值得赞叹的非常之举。
诚然,这个判断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当事人”自己没有说过他出家的动机,可供世人分析的最直接资料就是夏丏尊先生《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记录他与刚出家时的弘一法师在杭州虎跑寺的一段有名的对话:“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我们从夏先生那句看似简短实很带感情的话中可体味到问者的感伤与深深的遗憾。然这时,就刚刚取得出家人身份的弘一法师而言,对于眼前那位“晨夕一堂”的多年好友,想曾在一起探寻人生理想,讨论教育意义与方法,如今却有了僧俗之别,真有点恍如隔世之感,千言万语,一时间又从何说起呢!人生许多事,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且如没有真信仰,有些道理说了对方也未必理解,总不见得开口伊始就来一番说教吧。如今用这种较为轻松的语调化解老友“感慨万分”的情绪,又省却了许多需要解释但一时间实难解释清楚的“麻烦”,倒不失智巧,很有点外交家的敏捷呢。
应该是这样的。人生不是儿戏,出家也不是儿戏,如此严肃的人生大事,想一个有理智的人会仅仅由于受了一句“刺激”话就草率地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不过话说回来,虽说弘一法师选择出家学佛的道路自有“宿因”,但与夏先生确也不是没有关系可言。当然,这个关系不可能仅仅是表面化的“刺激”,而是有着与其人生发展的理路相一贯的逻辑。这个理路,就是对“向上一着”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