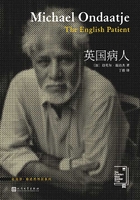他是我哥的发小,父亲是陕北的老红军,母亲是河南的老八路,把两大省份整合到一块儿就是他的名字一一秦豫。
如果把我哥的狐朋狗友排排队的话,这个秦豫理应打头儿。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效仿桃园三结义把自己的手指割破喝血酒,反正老在一起混。
这群人中,数秦豫和我哥份儿最足,恨不得合穿一条裤子。
秦豫在我老爸他们眼中是个捣蛋孩子,他的名字形同虚设,我爸管他叫咣咣。咣咣是土语,就是老没正经一门心思钻研旁门左道的意思。
渐渐地,咣咣的名字只能委委屈屈地在户口簿或者是老师的点名册上显示。户口本经常被锁在箱子里不见天日,点名册更没用,学校早停课了。秦豫的名字再响亮,在我爸他们这些正统的老头子们的记忆中就此消失,张口就是咣咣、咣咣的,让秦豫很没面子却又无可奈何。
我爸都不叫他秦豫了,我们还等什么?从此,秦豫这个名字再也无人提起。
那是个是非完全混淆的年代,咣咣和我哥他们无学可上,闲着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受罪,不生出点儿事儿闹出个动静啥的对自己对这个社会都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于是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扒墙头,堵烟囱……他们这些作为被我爸痛斥为歪门邪道,可咣咣和我哥不这么想。咣咣说,咱从现在起就要使劲儿忙活点儿,老爷子们都是老革命,以后咱得接班当个将军司令啥的,最不济也要混个参谋长吧!顿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孟子绝对想不到,这句话让咣咣从此有了坚定不移的行为准则,敢情那些循规蹈矩的好孩子才不堪大用呢,咣咣和我哥他们觉得不能对不起孟子。
咣咣说:今儿晚上月黑风高,哥几个得有个行动,把老爹的枪都偷出来咋样?敢不敢?谁要草鸡,趁早说话。
谁想当草鸡?我哥他们都是响当当的“铁公鸡”。当然,不是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应是火烧油烹刀劈斧剁经折腾的铁制公鸡。
于是,这个特别行动队于当天夜里,分别悄悄潜回家,又悄悄把各自老爹的手枪摸出来别腰上,在“三柏一顶”那儿会面了。
小城里有个无比神秘的地方就是这个三柏一顶。三棵双人合抱不拢的千年古柏一字排开,中间一棵高大挺拔,两边两棵相互依偎,树冠连在一起,像个大伞盖,由此得名“三柏一顶”。人们传说树上住有仙人,平日香火不断,树身系满了红布条,那些梦想招宝聚财,祛病消灾,避邪转运,祈子求福甚至还拖儿带女认树做干娘的人成群结队络绎不绝。
夜黑得像浸在染缸里的老黑布,咣咣和他的这个别动队从四面摸了过来,先是拍巴掌,学布谷鸟叫对暗号,然后把蒙着红布的手电筒无比警惕地晃了三晃,确定是自己人后才迅速凑在树下,把枪亮了出来。
每个人手上都有把沉甸甸的裹着红绸的手枪,打开来看,蓝幽幽的,冷气飕飕。蛇牌撸子,双笔箭,全是好枪——咣咣很老练,如数家珍。不过,我哥和大江拿的是空枪,咣咣的枪里却压着满满一梭子子弹。他得意极了,我哥和大江他们傻了眼。
怎么把枪偷出来的不说了,反正都是非正常手段。我哥偷枪时把我指使到门口替他把风,说是有人来就假装咳嗽。我紧张地站在门口,嗓子痒得要命却不敢有一点儿声响,我怕我哥说我假传情报,有负重任。至于咣咣,他有四个弟弟,这个家庭儿童团端着自制的红缨枪分别埋伏在门后,树旁,楼梯口,以保证咣咣从容不迫地偷枪并迅速撤离作案现场。
咣咣炫耀完了手枪,忽然问:哥几个想不想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嚯,太刺激了。
走!
咣咣带着大家来到了一口枯井前。
谁先来?
哥几个都跃跃欲试又心中忐忑,没有人敢动子弹上了膛的真家伙。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做了叛徒,反正咣咣刚想振臂高呼,我要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时,就听到“啪——”一声脆响。
闭眼捂耳朵的哥几个一愣,确定那声音不是枪声,而是从咣咣的脸上发出来的。
接着就是咣咣他爸的怒吼声:一群混蛋!
哥几个立马抱头鼠窜,转眼就没了踪影,只有咣咣被揪着耳朵押回家中。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我哥被老爸按在沙发上胖揍一通,十天内只能趴着睡。大江一个礼拜不敢露面。咣咣的脑门儿上有俩鸽子蛋大小的疙瘩,很对称,就像他家藤架上悬着的紫葡萄的颜色,半个月都没见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