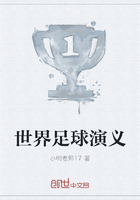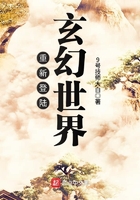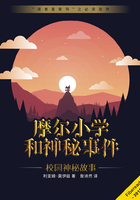1989年3月底至5月初,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我在美国游历了四十天。行程将尽的时候,邀请者告诉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柏丽纳斯镇,有一个“中国文化研讨会”你参加不参加?我说,参加。于是我就从旧金山去了柏丽纳斯镇。到了会上一看,才知道除了我之外,与会者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就想,那就只用耳朵,听吧。没想到,却听出一个非说不可的话题来。
会上有一位也是从外国来的白皮肤的教授,不断地批评和挖苦中国人。他是个“中国通”,据说当年曾经和“工农兵大学生”一起上过大学,所以,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听起来并无障碍。从普通民众、学生青年到知识分子,他无不指责。因为他是“中国通”,他挖苦的常常就比较细,连一些中国艺术家脸上留着的大胡子也挖苦到了。不过,对于我们这些读着《阿Q正传》长大的中国人来说,这位教授的挖苦倒也并不太苦。终于,这位教授的话锋从“大胡子”转向了对整个中国艺术家的评价。他说他所认识的中国艺术家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创作怎么才能讨外国人的喜欢,在画家圈里就格外地明显。连续用了两天的耳朵之后,这一天的下午终于轮到我做“专题发言”。我对那位教授说,中国有一句俗话,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你说的那种只知道讨外国人喜欢的人肯定有,而且肯定还不少。这和我在美国几十天,天天在电视里都能看见的肥皂剧和多得不能再多的广告,是一码事,那都是垃圾。就像美国的垃圾不能代表美国的艺术家一样,中国的垃圾也不能代表中国的艺术家。我对他说,你认识多少中国艺术家我不知道,但是我所认识我所知道的艺术家、文学家都是非常真诚的,比如史铁生,比如王安忆,比如莫言,比如在山西我身边的朋友,比如我自己。
说到我自己,我写小说从来就没有想过外国人喜欢不喜欢,甚至连中国人喜欢不喜欢我都不想,我只想自己喜欢不喜欢,我写小说的时候只想下面出现的这个句子,这个词,这个字,是不是我自己最满意最喜欢的,别的一概不管。我曾经和陪了我一路的翻译蔡先生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我就是掉进白油漆桶里也还是不管用,身上染白了心里也还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是无法选择的,就好像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深刻地了解甚至精通一种文化是一码事;与生俱来所赋予、所体验、所经历的生命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码事。而艺术创作所依靠的恰恰是后者。我告诉那位教授,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些吕梁山区的农民,他们手上拿的镰刀还是新石器时期就定型了的,他们播种用的耧还是两千年前西汉人赵过发明的,他们每天用来填饱肚子的食物是玉米面窝窝和马铃薯——他们自己管那叫山药蛋。但是,坐在牛车上用玉米面窝窝、山药蛋填肚子的人,和坐在汽车里用热狗、牛奶、鸡蛋填肚子的人都是人,他们在人的意义上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吃玉米面窝窝手里拿着镰刀的人,照样有他们的幸福和悲哀,他们的幸福和悲哀也照样是人的幸福和悲哀。我告诉他我有一句话——“人们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出现了堪称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这个杰出不只在中国杰出,就是拿到国际上也照样是杰出的,只是有些人还没有了解、还没有认识罢了。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就是这样的杰作。可是一说到作家和作品,人们就总要说到“局限性”,其实人本身就有局限性,人只能有两条腿、两只胳膊、一个脑袋,而不能像螃蟹或蜘蛛那样有好多条腿;连地球都有局限性,它只能是一个大致的球体,而不能是一个任意多边形,它也只能非常单调地按照固定的轨迹围着太阳转,而不能天马行空到处自由飞翔。这实在是很大的悲哀。可这悲哀并不独属于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
所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天下午,在柏丽纳斯镇当着许多“鼎鼎”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我心直口快地说了这些话,和一些另外的话。会后不少人向我致意表示赞同。尽管五六年过去了,那天下午会场上的气氛和场面依然历历在目。随着时间的冷却,当初那个“不快”的感觉渐渐平服了。但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命题却越来越巨大地逼在眼前,那就是当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们杰出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表达只被看作是“中国的”而不被看作是“人类的”。事实上几乎所有欧洲和北美的杰出作家和作品,在被人评价的时候都会被冠以“深刻地表达了人类的处境”“深刻地描写了人类的苦难”“深刻地体现了人类之爱,和人的尊严与荣耀”,等等等等。在这个用“人类的”三个字所组成的神圣之山上,云集了所有欧洲和北美的艺术大师和他们的作品,需我辈仰视才见。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超民族、超国家、超文化、超时空的大写的“人类”,为什么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我们的作品就与此无缘?不仅无缘,而且还常常会被别人或是“无意识”或是“下意识”地排除在“人类的”之外。最有讽刺意味也最常见的是我们自己,也在做着这样的排除。难道中国人真的不在“人类的”之内?或者说,这个人类到底是——谁的人类?
用卡夫卡和鲁迅做比较就尤其鲜明。卡夫卡1912年写出了《变形记》(1915年发表),鲁迅1918年写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卡夫卡1922年写出了长篇小说《城堡》(1926年出版),鲁迅1921年底开始发表《阿Q正传》,并于三年后的1924年陆续开始了最具深意的内心独白式的《野草》的写作。
在《变形记》中,那个说德语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大甲虫,也还是逃脱不掉文明的欧洲社会对他的强求和压迫,也还是逃脱不掉自己内心深处那一套做人的规矩,并最终死于这些冷漠的强求和规矩。那是一幅关于“人的异化”的最绝妙也最触目惊心的缩影。在《狂人日记》中,那个疯了的弟弟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竟然只看见“吃人”这一件事情,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只看见“吃人”两个字;最可悲的是他只有在变成一个癫狂的疯子时,他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他看清了真相,他在别人的眼睛里也就成了一个不明事理的疯子。为了突出这个令人胆寒的疯人的两难处境,鲁迅先生在小说的序言里意味深长地将“真事隐去”,让那位正常的兄长大笑着告诉大家,他的疯弟弟“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在这里,卡夫卡和鲁迅对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都坚持了一种彻底的批判和否决,都表达了一种深刻的、人被自己建造的文化所异化的无可逃避的处境。而《城堡》中的K和《阿Q正传》中的阿Q,不但都只选了一个单独字母做名字,连他们的来历、籍贯、职业、长相也都同样是模糊不清的。K在一个莫名之地,在一群冷漠如鬼魅的人的包围之下,经历千难万险,最终也还是无法进入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堡。在这部没有最后完稿的小说里,据说卡夫卡设计的结局是:K弥留病床之际,城堡来了通知,他还是只能留在村里而不许进入城堡。这是一个绝望的结局。而阿Q在经历了自己种种可笑可怜的“精神胜利”的努力之后,也终于因为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枪毙。包围着阿Q的也是一群冷漠、麻木、可怕的人,这一群人竟然因为阿Q是被枪毙而不是被砍头而感到无趣。阿Q最终被面对的人群所拒绝,没有姓氏,没有钱财,没有体面,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爱情,他最后甚至连自己死刑画押的那个圆圈也没有画圆。阿Q的结局也是一个绝望的结局。在卡夫卡的笔下这个永远无法接近、永远无法战胜、永远无法终极判定的“城堡”,成为一个荒诞的寓言和一个多义而又悲冷的象征。而永远无法确认自己,永远无法超脱自己,永远无法战胜别人,永远无法进入人群的阿Q,也是鲁迅笔下一个最丰富、最多义,也最令人悲哀的寓言和象征。如果说在《阿Q正传》中还因为一些具体的社会环境的描写,而可把阿Q只看成是中国人的象征,那么到了《野草》中,鲁迅先生就已经彻底地排除了具象的一切细节,达到了一种高度的抽象和象征:那个只乞求虚无和灰土的求乞者,那个破碎在灯影里的“好的故事”,那个毅然决然走向坟场的过客,那个于噩梦中“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死去的自己……面对这令人无比寒冷惊骇的文字,就仿佛面对着一面不知年代、不知来历也不知作者的斑驳冰冷的巨大石碑,那令人费解却又直指人心的言说有如天启。
在卡夫卡和鲁迅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前后,都各自经历了一场历史的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文化传统和自信心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同样辛亥革命打倒皇帝,和随之而来的这场革命淹没在军阀血腥无耻的屠杀之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自信心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在这两场毁灭之中,欧洲产生了他们的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卡夫卡;中国不但产生了自己第一位现代文学大师,也产生了自己新文化运动最杰出的精神领袖。正是表面上看来全面反传统的鲁迅,成为中国文化能够不死的象征和源泉。借用一句时髦的理论术语,鲁迅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奇理斯玛”。如果从这一点上来比较,鲁迅是远胜于卡夫卡的文化巨人。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说出这些常识,实在是因为在这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常识背后那个截然不同的判断:说到卡夫卡,人们的和我们的评价常常是“人类的”“人性的”“人的”,等等,等等,总之,是超时空、超民族、超文化的。而说到鲁迅,则往往是“中国的”“中国人的”,等等,等等,总之,是“有局限的”“是一部分人的”。现在关于鲁迅的论著数不胜数,可有谁说过鲁迅的“人类的”意义吗?可有谁从“人类的”角度出发看待鲁迅的文学著作?外国人不这样想也就罢了,我们中国人这样想过吗?
在这里又碰到一个常识。人们会说卡夫卡在绝望的时候并无另外的文化做依靠和希望,因而是彻底的绝望。而鲁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绝望的时候,心里却还藏着对西方文化的信任,还盼望着把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到中国来,因而鲁迅的绝望是还有希望的绝望,当然是有局限的绝望。但是我想,如果说在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还有半句“救救孩子”的“理想”,那么到了拿革命烈士的鲜血来治病的《药》,到了《阿Q正传》,到了《孤独者》,尤其到了《野草》,鲁迅先生以他极其彻底的怀疑和也是极其彻底的孤独,早已超越了狭隘的文化视野,而达到了对人的极其深刻的表现。
如果我们陷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当中而难以看清的话,只要把聚焦的视点向后移动一下就会一目了然。曹雪芹的《红楼梦》算不算“人类的”文学呢?他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是不是“人类的”悲剧?是不是对于“人类的处境”的深刻的表达呢?再向前看,苏东坡、关汉卿、杜甫、李白、屈原……算不算“人类的”呢?就他们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世界上可以与之比肩的人有几个呢?这里又遇到一个常识的问题。在有了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所有“后殖民”理论的今天,我的这些问题早已不是问题,早已被理论家们“说明”了。西方人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了他们武力的和经济的殖民的同时,他们也更加深刻更加霸权地推行了西方的“话语权力”,因而我们这些西方以外的人,只好站在西方话语的外边说话,只好站在那座“人类的”高山的脚下向上仰望。而其实那座高山原也不过是一座被一部分人用手搭建起来的山,并非全世界的人类共同搭建起来的高山。不过,全世界的人类共同自觉自愿只搭建一座山的事情,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我还是想回到常识。在有了这些所有的理论、所有的争论之前,人类不是已经有了许多许多堪称杰出的艺术作品了吗?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阿尔卑斯山,或是只有喜马拉雅山,只有乞力马扎罗山,岂不是太单调、太可怕了吗?世界上各个不同传统不同文化的艺术家,难道是为了某个好理论才创作,或是为了“话语权力”才创作的吗?难道是为了表达“人类的”这样一个理念才动情地歌哭的吗?难道艺术是一个预谋吗?如果一切都是可以预设的,那人类这个物种该是一群多么乏味的生命!这一切似乎都是常识。可是一切的误解和错误也都是从常识出发的。我在这里无意贬低理论,而只是想强调创作的不同。而事实上所有真的新理论的产生,也正是在对以往被旧理论设定了的世界的打破中获得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的魅力与价值和艺术是等同的。——那是一种创造力的体现,那是一种对人的丰富。
我在评论我妻子蒋韵的小说集《失传的游戏》时,曾经对她的那些故事说“这是活生生的与所有的古典和现代的理论都无关的人的处境。这是人在文化外套的极限之外被碰破的伤口”。其实,这也是我的自道,也是我对一切杰出艺术的看法和追求。可惜的是,现在满眼所见,到处都是故意制造的伤口,到处都是精心化妆的美丽。人们以这样的制造和化妆来换钱和惑众的同时,正在失掉的是自己感知幸福和痛苦的能力,正在失掉的是生命本身,是生命最为可贵的原创力。
当卡夫卡满怀悲哀和绝望,无可奈何地徘徊于“城堡”之外;当鲁迅断然拒绝了人群,孤独、悲愤而又一意孤行地坐在自己黑暗冰冷的怀疑之中;他们敏锐而深邃的内心被丰富的生命体验所充满的,绝不是“人类的”这三个字可以尽述的。
让我们坚守常识,让我们坚守自我,让我们坚守诚实,让我们在对自己刻骨铭心也是自由无拘的表达中,去丰富那个不可预知、天天变化的“人类”。——当然,这只是对真的想从事艺术的人而言。
1995年5月21日写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