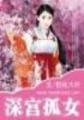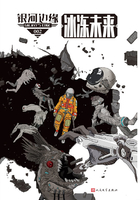——纪念李霁野先生诞辰110周年
中国古人向往过“米寿”(88岁),更向往过“茶寿”(108岁)。霁野师生于1904年4月6日,年轻时医生预言他难以活到40岁,年老时又有医生预言他肯定能活到100岁,但这些预言都不灵验。他于1997年5月4日去世,享年93岁,虽未能庆祝“茶寿”,但仍属于“喜丧”。
但单凭活得长还不足为“喜”,每个人要给人间留“喜”,除了年龄,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业绩。霁野师是诗人,写过语体诗,也写过格律诗。霁野师并不认为他的诗都好,但他要求自己确有真情实感时才动笔,决不为写诗而写诗。他尤喜好散文随笔,认为这种文体取材广泛,凡风俗人情、奇闻趣事、人物书籍均可以作为素材,在抒情中兼发议论,行文如跟友人炉边漫谈,备感亲切。鲁迅说霁野师的小说感觉敏锐,“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也道出了霁野师散文创作的特色。我认为霁野师的《给少男少女》《意大利访问记》都是散文随笔中的上乘之作,但目前文学评论界对这些作品研究还不充分。不过,霁野师事业的中心还是翻译,他“在国内外的译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43页)。在《李霁野文集》九卷中,译著多达五卷,其他各卷中也都有涉及翻译的文字。
霁野师有多方面的贡献,这无疑是令人敬重的。但可敬的人不一定可亲。如果学者、教授身上染上了“学者气”或“教授气”,那反倒可能拒人于千里之外。霁野师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有人情味的人。他对花鸟昆虫都喜爱,都欣赏,能从中发现奇妙的美的境界。他喜欢旅游,写下了《江河抒情》《罗马漫步》等散文佳作。年近八旬,他还揣着一颗童心翻译出囊括了不少爱情诗的抒情诗集《妙意曲》,真是“青春虽逝余情在,花谢花开仍动怀”(《题〈妙意曲〉》)。为了辅导孙子孙女阅读唐诗宋词,他专门编写了《唐人绝句启蒙》和《唐五代词》这两本普及性读物。小孙子喜欢玩冲锋枪,他利用1978年参加“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之机先到上海买,未买到又到广州去找。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示,如广州没有再到北京买!这就是爱心博大的霁野师,可敬而又可亲的霁野师!
霁野师的翻译成就跟鲁迅的扶持、奖掖密不可分。他15岁在安徽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英文课本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方夜谭》简体本,这培养了他对翻译的最初兴趣。19岁跟韦素园从安徽到北平,入崇实中学读高中,开始借助字典编译短文。1925年夏秋之际,在鲁迅的倡议下,未名社正式成立之前,霁野师也正式踏上了翻译历程。从那时到去世的70多年间,霁野师的主要译著多达18部,其中重印次数最多的是英国作家夏洛特·勃朗蒂的长篇小说《简·爱》。这个译本经鲁迅介绍,曾作为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单行本印行。茅盾指出,霁野师的译本跟伍建光的译本各有特色:伍本有删节,故宜于一般读者;李本逐字直译,更适合于文艺青年。据说毛泽东也读过此书。虽然不能单纯以此判定译文的质量高低,但至少能说明这个译本读者面比较广泛。霁野师的其他译本也曾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被侮辱与损害的》《虎皮武士》《难忘的一九一九》等,也都是我们这一代人风华正茂时喜爱的读物。但翻译给他带来的并不都是掌声和喝彩,还有迫害、痛苦和烦恼。比如他因为翻译过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这是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大学曾经采用的文艺理论教材,被北洋军阀政府的侦缉队关押了50天。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颠沛流离中花四年半的时间译完了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但译稿却在战争中完全被毁。这对于一个翻译家是何等沉重的打击!他翻译的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有思想,有文采,深受海峡两岸读者的欢迎,但某出版社重印时,错字漏字多得惊人,让译风严谨的霁野师十分气恼。
未名社的正式成员除鲁迅和霁野师外,还有台静农、曹靖华和韦素园、韦丛芜兄弟,共六人。社务最初由韦素园主持,但1926年底他大量咯血,一病不起,社务由霁野师义务主持,为此他花费了青年时期最美好的五年时光。鲁迅认为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成员都“愿意切切实实、点点滴滴的做下去”;虽然存在期不长,却出版了不少“相当可看的作品”,“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有人因为未名社的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跟霁野师都出生在安徽省霍邱县叶集镇,就惊叹于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将他们四位并称为“未名四杰”。但霁野师发自内心地反对这种提法,他并不认为叶集这个小镇真的风水好,而且认为除开鲁迅以外,未名社其他成员“都无大成就”(1975年11月7日致陈漱渝的信)。他认为他们之所以“小有虚名”,是因为“讨了时代的便宜”(1986年5月8日致邹十践的信),因为“五四”以后文坛人才较少,翻译人才更少,所以应该用“未名社成员”这个提法取代“未名四杰”的提法。
当然,鲁迅对未名社也有所批评,如认为他们“疏懒一点”,“小心有加,泼辣不足”,又向来不发展新成员,以至于社务乏人。鲁迅更不满的是未名社后期有的人“所取多于应得”。不过,鲁迅的这些批评均见于私人信函:有的是出于对同人的厚爱——爱之深,责之严;有的是出于误会;有的是明确有所指,如认为“所取多于所得”、说话“往往不可信”的是诗人韦丛芜,而不是其他人。未名社1931年准备结束的根本原因,是社员情况发生了变化:韦素园因重病英年早逝,鲁迅在上海,台静农、曹靖华基本不过问社务。韦丛芜情况则更为复杂,一言难尽……但直至临终之前,鲁迅对未名社的基本评价并未改变,对霁野师的友情也未改变。
在研究未名社的过程中,必然会碰到一个颇伤同人感情的问题,那就是鲁迅批评未名社经济管理不善。这也是导致鲁迅1931年宣布退出未名社的直接原因。鲁迅同年10月27日致曹靖华的信中提到,未名社欠他三千余元版税,答应结清,而尚未付,担心会要不回来了。事隔四十多年,曹靖华先生准备把鲁迅致他的信结集出版。霁野师建议曹先生在此信后加一注释,说明所欠鲁迅版税后来大致已清,但被拒绝。曹先生表示他当年远在苏联,不了解社务,而且对鲁迅的书信不能随便加注。这样就使得在韦素园病后长期主持社务的霁野师难免背上黑锅。
碰巧的是,1975年我发现了鲁迅1935年11月14日致章雪村的信,白纸黑字证明未名社所欠鲁迅版税“大致已清”。我又提供了另一份鲁迅博物馆保存的《未名社账目结束清单》,由霁野师和韦丛芜共同签名盖章,李何林先生亲笔代写,把账目交代得更加清楚。真相是:霁野师应取版税1264.37元,结束时尚存601.97元,并未擅用未名社公款。透支版税的是韦氏兄弟:韦素园长期卧病,欠社款1667.668元;韦丛芜有病,经济上又欠检点,也透支853.933元。韦丛芜本人也承认,他长期向未名社出版部借钱。1929年7月至10月,每月借二三十元,后来“逐渐提高到五六十元,甚至七八十元,这给未名社出版部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未名社始末记》)。霁野师顾及当年跟韦丛芜的交情,不愿向上海的鲁迅说明真实情况,更不愿刺激命在旦夕的友人韦素园,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好在40年后,这些隐情终于大白于天下,还了霁野师一个清白。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谢意,视我为“朋友”,也正是这个原因。
不料1987年,未名社经济事再起风波。这年9月,霁野师在《鲁迅研究动态》第2号上读到了韦丛芜的《未名社始末记》一文,反应十分强烈,甚至退回了鲁迅博物馆增聘他为鲁迅研究室顾问的证书,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当时的想法是,除开霁野师所写的回忆文章之外,其他有关未名社的史料保存不多,既然韦丛芜有这样一篇未刊稿,也不妨刊登出来供研究者参考。凡回忆文章总难免有主观色彩。如果韦文有失实之处,其他人指出订正也就可以了,不会有明白人对回忆录的说法全部采信。最近通读霁野师文集中所收的书信,才知道他盛怒的原因:一是因为他怀疑这篇文章是韦丛芜的亲属提供的。这是误会。韦丛芜这篇文章原保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是我看到后交鲁迅博物馆的刊物发表。文章写于1957年3月3日,刊登时,韦丛芜已经去世九年了。二是因为韦丛芜的文章中说到1931年未名社准备结束时,他从开明书店领到一张三千元的支票,请周建人转交鲁迅。霁野师认为这是韦丛芜在无中生有,是对鲁迅和周建人二位的大不敬。因为未名社欠鲁迅的3073.66元,直到1935年11月才由开明书店大致结清。韦丛芜文中所提“三千元支票”一事,霁野师跟李何林早已给他去过信,指出这是误记。如今原封不动地重新发表这种误记,会把好不容易澄清的那潭水重新搅浑。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诚信,欠债不还是被人鄙薄之事,更何况是欠了鲁迅的钱未还。所以,站在当事人的立场,霁野师认为刊出韦素园的文章实属“荒唐”,实属“混账”,并无不可理解之处。如果发表这篇文章时先征求霁野师的意见,并在韦文误记之处加条注释说明真相,这一场风波也就不会发生了。这是我的疏忽导致的过失,是我一生中应该吸取的一大教训。
鲁迅跟未名社之间发生的版税纠纷本属经济问题,不过后来也有学者往政治方面硬扯,其根据是鲁迅1931年11月10日致曹靖华的信中的一句话:“霁野久不通信,恐怕有一年多了。”这位学者分析道:“这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毋庸讳言,又带有较强烈的感情色彩。因这一年是白色恐怖极为严重,鲁迅处境十分艰难的一年,他盼望朋友来信的心情是相当殷切的……”这段分析给我的印象是:霁野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跟鲁迅疏于联系,是出于对“白色恐怖”的恐惧,害怕被鲁迅株连,大难临头独自飞,使殷切盼望朋友关心的鲁迅失望、伤心。这种理解显然不符合鲁迅的本意。鲁迅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远在苏联的曹靖华想将一部短篇小说译稿交未名社出版,要跟霁野师联系。但是霁野师1930年秋已受聘至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英语系教授兼主任,由韦丛芜来负责未名社的社务。霁野师一年零八个月未给鲁迅写信,仅仅是对有关社务问题“不愿说,也无从说起”(《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跟“白色恐怖”云云是完全不搭界的。
谈到霁野师的政治倾向问题,他晚年还遇到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1987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刊登了一篇《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1936年四五月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拟定了一份采访鲁迅的问题单。她当时正在撰写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文艺运动》的长篇论文,准备收入斯诺选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而后再进一步扩展成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所以问题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斯诺从北平到上海,当面征询了鲁迅的意见,并把鲁迅的回答直接记在问题单上,事后又补充自己的回忆,加上自己的看法,整理成了这份“谈话纪要”。“纪要”中有一句话涉及霁野师:“李霁野是翻译家,倾向右翼。”
由于这段“谈话纪要”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有明显的讹误和不准确的措辞,并没有经过鲁迅审定认可,所以《新文学史料》编辑部于当年9月25日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部分在京的老作家和学者进行讨论,我也忝列为参加者之一。会后霁野师跟另一位与会者围绕“倾向右翼”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现在反思起来,当年的论争双方都动了感情,使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其实,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会再有人单纯用政治倾向来评价学者、作家和翻译家的学术功过。说到“倾向右翼”,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但现在学界不也对胡适的是非功过平心静气进行了具体分析吗?
至于霁野师是否“倾向右翼”,他已经用自己93年的生涯进行了有力的证明。我认为,霁野师虽然并不热衷于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但确是一位被“五四”狂飙唤醒的新型知识分子。他的老家叶集就在红军大别山区根据地以内,跟革命根据地金家寨相隔只有45公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恽代英、瞿秋白对他产生了直接影响。他的友人如任国桢、赵赤坪、范文澜、曹靖华、韦素园、李何林、台静农等不是共产党员就是进步人士。未名社存在期间还掩护过王青士、冯雪峰、宋日昌、郑卫华、王林、李俊民、潘漠华等一批党的干部。1928年,他的二弟李耕野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秋,他应许寿裳先生之约到台湾任省编译馆名著编译组主任,热情宣传“五四”新文化。1949年4月,他逃离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湾,到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人把他的入党说成“归队”,因为组织上早就把霁野师视为自己人了。试问,世界上会有这种“倾向右翼”的作家、学者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唐弢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鲁迅一向对未名社成员有好感,如对曹靖华、韦素园、台静农等都很好,对李霁野也如此,我怀疑这个‘倾向右翼’的‘李霁野’,可能是未名社的另一翻译家韦丛芜之误。”我认为唐先生这一判断完全正确。这可以用韦丛芜本人的回忆来印证。韦丛芜在《未名社始末记》一文中写道:1930年7月,他计划跟周作人合作办一份“纯文学性”的《未名月刊》。“这时青君(按:指台静农)在中法大学预科教书,霁野在孔德学院高中部教书,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出我意料,他们竟说我是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来办未名社出版部,违反了未名社的传统。至于办纯文学性的《未名月刊》,他们更不赞成,并且说鲁迅先生在上海参加了左联,我们应该在北平响应他。我当时觉得他们的意见很积极,大概也可以代表鲁迅先生的意见,因而认为自己思想落后了。他们提议办一个旗帜鲜明的左联刊物……”请看,政治上左翼、右翼的分界,在如何办《未名月刊》的问题上就是这样泾渭分明!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左翼文坛公认的盟主,台静农是北方左联的筹备人和常委。霁野师也与李俊民、杨刚等参与了北方左联的筹备工作,并由评论家以群先生介绍,列名于左联成员名单。可见,鲁迅认为韦丛芜当时“倾向右翼”是符合实际的。
要澄清以上问题必然还会涉及埃德加·斯诺。斯诺是众所周知的美国进步记者,一位热爱中国的异邦人,也是鲁迅的朋友。但他整理的谈话记录稿中出现不少错误,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一是由于他当时对中国文坛的情况了解有限;二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或口头翻译失误。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斯诺是“贤者”,同时也不必“为贤者讳”。比如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率先比较全面、比较客观地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的红色根据地,功不可没,但书中也有瑕疵和失误。我为此写过一篇史实考证的文章。斯诺和宋庆龄之间也彼此视为朋友,但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对宋庆龄有好几处歪曲和错误的报道。宋庆龄认为这样描述自己既不诚实也不友好,坦率地写信告诉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并郑重地委任路易·艾黎向斯诺本人转达(参阅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斯诺接受了这些意见,认为宋庆龄的批评“很有道理”(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9页)。
斯诺整理的这份谈话记录除了对李霁野的评价有误之外,还把《晨报》副刊当成了《申报》副刊,把艾寒松当成了杜衡,把戴望舒误为穆木天。据这份“谈话整理稿”,鲁迅“不喜欢但丁”,认为他是“一个很恶的人”。但鲁迅的准确意思是:“回想起来,在年青的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佩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什么鲁迅当年对但丁缺乏亲近感呢?他后来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做了解释:“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可见鲁迅阅读但丁的感受也有一个深化和变化的过程。在这份并未正式发表的谈话记录中,把霁野师说成“倾向右翼”,绝对不能代表鲁迅的观点。
前文提到,霁野师是鲁迅扶持、奖掖的文学青年,霁野师对鲁迅的感念之情更是至深!未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塔》,接着出版的还有鲁迅的译著《小约翰》、杂文集《坟》、回忆散文《朝花夕拾》。霁野师对鲁迅的敬爱,还表现在珍爱鲁迅手稿这种细小的事情上。鲁迅对自己的手稿并不在意,一般的报刊和出版社发表作家的文章后也将原稿毁弃,以致流失到小贩手中用来包油条。但未名社却将鲁迅的文稿另抄到副本付印,使《朝花夕拾》的手稿完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霁野师1936年4月从英国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拜访鲁迅,留下了愉快难忘的印象;万没想到半年后鲁迅遽然去世,这次竟日长谈之后师生从此天人永隔。霁野师在当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霁从师逾十年,所蒙情惠无量,常感愧。”同日致友人孔另境的信中说,他跟鲁迅“相处逾十年,深知此公热情满腔,是一难得的真诚心,一旦失去,颇感生之空幻”。为了同样以真诚心回报鲁迅的情谊,他长期协助许广平照料鲁迅在北平的母亲和遗孀,甚至垫钱接济鲁迅之母。当时周作人月薪逾400元,但1938年1月至9月,周作人只给老母送过15元零用。周作人夫妇间月去看一次母亲,坐坐而已,他们的孩子是从不上门的,可见友情有时能胜亲情。1976年,霁野师决定撰写《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他在同年2月19日致我的信中说:“我所以决定写点儿有关未名社的事,主要是你的督促,此外也因为可以减少误传。”李师母刘文贞回忆,霁野师撰写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常常情不自禁,老泪横流。也就是在撰写这些文字的日子里,霁野师常常梦见鲁迅,醒后有隔世之感,曾作诗记之:
一
握手言欢一瞬间,重温四十余年前。
堪伤死别与生离,难诉心头事万千。
二
恩师遗训未尝忘,益友音容忆断肠。
梦里相逢频回顾,中宵不寐细思量。
霁野师跟鲁迅相识相交12年,撰写这些两首诗时年已72岁。我跟霁野师相识相交22年,马年岁首撰写这篇忆念文章的时候,我已73岁。时光都到哪儿去了,我也真搞不明白。在《李霁野文集》(九卷本)中,收录了霁野师给我的书信54封,留下了他扶持提携我的文字记录;但他实际写给我的书信应该超过此数。在霁野师离我而去的18年中,我以他为榜样,笔耕不辍;也努力学习霁野师的风骨品格,对国家、对师友常怀感恩之心,在遇到坎坷曲折时也力图像他那样坦然面对。1984年初,霁野师将1928年至当时的五十多篇随笔结集为《温暖集》,书前用英国诗人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的一句诗作为序诗:
我在生命的火前,
温暖我的双手,
一旦生命的火消沉,
我愿悄然长逝。
一个人何时“悄然长逝”,往往不是本人能够决定的事情。但亲情、友情、师生之情,都是生命之火的燃料。它不仅一直温暖着我这颗畏寒的心,还将用无限的光芒照亮我十分有限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