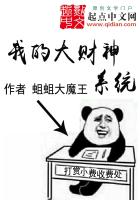元旦过后,期末考试的来临将为这个学期划上句号,下学期就是高一下了,不过,比起学期的结束,更有一件事使我们不舍与眷恋。
小马,最终完成了实习期。虽然我们在平常的逗哏打趣中曾半开玩笑地邀请她留下任教,但现在,她还是得离开了。
老姚把自己的课和语文课调换,为了让小马能上完最后一课后去火车站。
每个人都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没有人讲闲话,没有叽叽喳喳的吵闹,但也有像我这样的家伙接一下小马的话,弄的大家哈哈大笑,当然,也有小马。
下课铃响起,欢笑声却没有因此而被打断,小马交给我这个捣蛋鬼一封信,让我当众读了出来。悠长又缠绵的回忆在一张纸上被尽力地铺展开来,读着读着,我想起都德的《最后一课》,只不过,此刻的场景,并没有小佛郎士和韩麦尔的忧伤,是什么呢?也许是期待吧。
伴随着最后一个无言的句号的散去,我坐了下来,我们一齐鼓掌,作最后热烈的送别,小马在讲台上鞠了一躬,留下一面笑靥,走了出去。
期末考试。
我进步了一点,一切似乎进展顺利,老姚也对我勉励了一番,家里的紧张气氛有所舒缓。
然后,在考试后一个星期的延时课之后,寒假开始了,半个月的假期囊括了一部分的春节,因此,尽管有不少的作业,我还是有时间和父亲回一趟老家。
父亲开着车,母亲与妹妹两人都晕车,在座位上昏睡着,我听着音乐,静静地漠然地望着远方,熟悉的高速路,绿色的树与横条向后拉扯,看着窗外。老家越来越近,我却始终觉得我是个有血缘关系的漠视者。
今年的年夜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老房子里进行,而是在一家饭馆里,订了一个包厢,里面还配置了播放器之类的设施,能点音乐。
一行人进了包厢,十几个人显得有些狭窄,上至爷爷,下至重外孙女,除了几个没来的,马马虎虎算是四世同堂,大伙儿吃的吃,喝的喝,第二代的老男人大谈起了生意经,妇女讲起了养儿育女,第三代的几个人更是拿来好不容易淘来的青岛啤酒对饮,虽然有几声怂恿,但我未成年,况且母亲也一再声明我是“读书的伢”,怕我“喝苕了”,我没有碰那泛着白沫的杯子,拿着一本《狂人日记》,他们看了看我手中的书,也就不再说什么。
妹妹与侄女争夺着播放器的使用权,一个要《两只老虎》,另一个要《小兔子乖乖》,最后两个小家伙的吵闹停火,一致同意播放《聪明的一休》,两位妈妈松了一口气,像是刚刚阻止了一场世界大战。
爷爷坐在几个儿女的中间,呆坐着,接食过送来的饭菜,只有白胡须随着咀嚼在上下挥舞着银白色的微光,一手拿着拐杖,一手搭在腿上,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子女。奶奶虽不能下厨,但还能吃饭,只是筷子像线上绑的蚱蜢跳动着。靠在边上的几个子女在对话和关照老人间切换,不时爆发出关于某一话题志同道合的欢笑,老人们却依旧没笑。
包厢里的灯不亮,又加上天黑,屋子里显得昏暗。几个孩童的争吵与尖叫,几个孩童母亲软硬兼施的恫吓和安抚,几个青年人饮了酒的笑,几个长辈生意经的评头论足,使房间里很是热闹,老人的咀嚼声被淹没了。我早已吃完了碗中食,手机没电,躲在一旁看书。
饭局终了,大伙儿开始讨论住宿,父亲接受了大姑妈的好意,想着妹妹也有侄女可以一同玩耍,随即领着一家子住下。
住过几日后,父亲带着一家子告辞。“爸怕是撑不住了。”大姑妈在父亲临行前说,父亲只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上了车。车走远了,远景在车扬起的尘土里散尽。
“爷爷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了。”父亲开着车,望了一眼镜子,说着。
“哦。”我了然无趣地回答。
“到时候,你也要和我一起回来。”
“要是上课呢?”
“请假。”
“你是亲孙子,你必须得回来。”
父亲扔下这这句话后便不再开口。
脑袋倚在玻璃上,我再次看着窗外。正是夕阳将落,灿烂的余晖粉饰着熟悉的道路,两旁的绿植在深绿与金黄中披着迷人的光彩,仿佛聚光灯下的演员。
这大概是熟悉的路途与今天的夕阳最后一次相遇了,我无端地冒出这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