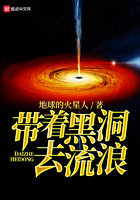他似乎相信了,专注的看着路,速度更快了。我收了枪,把枪放在口袋里,但手也在口袋里握着枪。谁知道他是不是假装相信的呢?
一口气跑出了几十里地,我开始盘算还要不要继续,因为这样的距离已经相对安全了,再继续跑下去,只能是离边境越来越远。而且他已经问了好几次要去哪里,我只是告诉他继续开,照此下去,他迟早起疑心。
迎面开过来另一辆卡车,因为路窄,双方都放慢了速度,开始小心的差车。就在两个驾驶室重叠的瞬间,我听到了叫喊声。
竟然就是那个瘦猴!那个把我当物体随意装卸,肆意脚踹的廋矮的司机。更可恨的是他竟然能够如此神奇的一眼就认出我来。这不能不说是天意,要知道这么长时间了,我的变化是自己在溪边洗脸时都不能从倒影里认出自己的,而他却可以。
估计我对于他早已是化成灰都认识的了,也不知道他在想象中虐杀过我多少次?总之一定是刻骨铭心的了,若不然,凭什么一眼认出我?
我的枪响了,子弹钻进了身边司机的太阳穴,接着第二枪,瘦矮的家伙胳膊中了弹,两辆车子顿时擦住了,好在速度极慢,若不然,我有可能极其悲剧的死于车祸,那就太搞笑了。
莫名的愤怒让我不断的扣下扳机,一直把弹匣打空,最后几颗子弹几乎只打在了车身上,因为两辆车的驾驶室已经基本错过了。
失去控制的车子尽管速度慢,却不能完全停下,我迅速的跳出了驾驶室,却发现根本没有落脚之处,司机为了让路,早已经把公路利用到极限,半个轮胎都悬空了。
我直接掉落在河滩上,刺骨的疼痛从脚脖子传来。不敢逗留,我用狙击枪当拐杖使劲离开跌落的位置,没撑出几步就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卡车砸了下来。
万幸,几步之遥,差点就给他们俩殉葬了。真要是一起上了路,那这黄泉路上还不相互殴打得鼻青脸肿?怕是阎王见了,也会暴怒,狠拍龙书案:放肆!永世不得投胎……。
爬到对面山坡的时候,已经累得不行,左脚疼痛倒在其次,使不上劲全靠枪身支撑,我学过哑巴,可没学过瘸子,拄拐杖爬山何其艰难?然而不能停,那两辆卡车很快就会被人发现,那车身上的弹痕一定会促使他们搜索周围。
从来没有这么累过,累到每一次呼吸都感觉到肋间刺痛,“拄拐”的双手似乎关节都肿胀了,每抬起一次都钻心的疼。而全身湿漉漉的就似乎格外的沉重。
好不容易又翻过了一道山梁,打死我也走不动了,被子弹杀死也比活活累死要强。我倒地开始休息,可刚一躺下,口水带着腥臭就直往嗓子眼里钻,胃里的东西几乎是喷涌而出,而后是久久不息的翻江倒海,直呕得我像被抛在岸上的鱼,咧着嘴急促的喘息。
稍稍恢复点知觉后,我把附近够得到的草叶往嘴里塞,试图咀嚼出一点味道来掩盖残留在牙齿缝隙里的血腥。
就算在极度倒霉的时候,也并非全无幸运,比如这次纵然很要命得扭伤了脚,却并没有骨折,要知道这可是从好几米高的路上直接跌落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歇过一阵之后,我开始行动,不过基本等于是在爬行,我得赶在天黑之前找一处安全些的藏身地。还能有什么地方?自然是山洞。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出乎意料的苛刻,方圆几里地竟然都没能找到一个勉强可以容身的山洞。
只能妥协,在小溪边的石头缝里坐了下去,管不了太多了,能掩护多少算多少吧。我把受伤的脚泡在水里,冰冷刺骨。心里却很希望能再冰冷一些,能够像冰块那样使受伤的组织收缩,减少里面的淤血。我太需要尽快恢复行动能力了,这关乎生死。
只是这样很消耗体力,到了夜里,寒冷来袭,又决然不敢生火,身上依旧还是半湿的衣衫渐渐冰凉,不得不离开水边,躲在树底下去避那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风。
第二天的午后,我才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山洞,若是有的选择,我决然不会在此逗留,因为这个山洞的口子是一道阴暗的裂缝,勉强可以爬进去,里面也很局促,只能蜷着身体。我惟一能做的改善就是在附近收集了一些冬天里枯萎了的杂草。老实说,舒适程度并不比一个野猪窝强,更可恶的是它总给我不太好的感觉,不知道是因为太小,还是因为太阴暗。
就这么痛苦的窝着,又是一连好几天,试过很多次,脚伤还是无法跑动,只好这么熬着。直到脚尖着地不再那么钻心的疼,我才决意离开。
去哪里呢?为了安全再次深入敌国腹地?还是再试一次靠近边境?我纠结了很久,最后还是不由自主的选择了前往边境。
就算要死,那也死在家边吧!说不定战友们冲锋到此还能替我垒一座土坟。然而,他们认识我吗?身上没有任何一点来自咱们部队的元素,无论怎么看都是越军的狙击手。看来,收尸的希望实在渺茫。
这次行动很慢,一来根本走不快,二来吸取了教训,知道他们人多,且四处都有,需要格外的小心翼翼。
为了确定方向,不得不爬到一个山顶上去。
我站在山顶四处张望了一会儿,估计此地距离那次被围捕的地点大概还有二、三十里地。心情也就稍稍放松了一些,不太远了,又还算在危险区域之外。
正要抬脚离开,一种火辣辣的感觉突然从腿上传来,低头一看,裤子破了两个窟窿,血流如注。
狙击手!该死的。
这是一片相对开阔的区域,四周几米远都没有有效的掩体。逃跑显然不现实。
怎么办?
我猛然倒在地上,四肢抽搐,尽可能的模拟人中弹将死的情形,这一点,我是很有经验的,看过很多次了。心底不断的念叨:够了,别再补枪了!
几秒钟的安静之后,我知道再挨子弹的危险基本散去了,手脚也基本不动了,完全一副尸体状。
又过了十多分钟,我估摸着那家伙应该正在前来查看的路上,根据自己中弹和听到枪声的时间间隔来判断,他应该就在附近某个山坡上。这就意味着他需要下到山沟再爬上我所在的山顶,有一段时间他会看不见我,这就是我等的机会,而且,应该就是现在。
忍着剧痛,我突然翻滚起来,一口气滚落到附近的草丛里。没有枪声传来,看来确实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我脱下衣服,撕下一段布条来扎紧了伤口,血流得厉害,但不是喷涌出来的,应该不致命,子弹偏外侧,骨头还没断,要活下去,就要靠自己再拼一次。
我把衣服丢在方才中枪的位置,特意在下边塞进一些杂草使其稍稍隆起。然后藏身到草丛里,把沾了血且很明显的草叶抓断了去。然后架起了狙击枪,方向是根据方才中弹时自己的身体方向来判断的。
又过了很久,疼痛越来越剧烈了,二十几米外的草丛里才露出一个人来,端着枪,指着那个空虚的“尸体”。
老兄,也不用瞄准镜看一看?他似乎对刚才那一枪信心十足,又或许我的死亡表演太过逼真。
我的枪响了,他向后倒去。
爬到他的身体边上,发现子弹穿透了胸膛,终于轮到我来看他表演了,很显然,他的表演完全真实。
有一句形容世事难料的古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在战场上,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半秒钟生,半秒钟死。
而天气也极其容易变化,很快就乌云密布了,我收拾了他留下的十多颗子弹,爬回了那个局促的山洞。检查了伤处,子弹并没有留在里面,这是好消息,可是伤口被削去了足有两个鸡蛋大小的血肉,决不是几天就能恢复的了。
很沮丧,命运注定不让我靠近边境;很担忧,担心伤口化脓,那样的死法有些悲惨。情绪很不稳定,雨却一直不断,连采草药都成了奢望。
我翻看了一阵从那个军官尸体上搜到的笔记本,一个字也看不懂,里面还夹了一支圆珠笔,让我可以在大半本的空白页上涂鸦,开始尝试记录过去的经历,断断续续就留下了几十页的笔迹,越写越感觉像是在写遗言,每一句都像是最后的诉说,身体一点点的枯萎下去,死亡确实越来越近,而这一次,我完全没有抗拒的力气了。
我不知道这些文字会不会被人发现,但这不重要,本来就不是留给别人看的,不过是自己打发空虚的方式罢了,就算被人发现了又能怎样?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时候,我连完整的骨架子也许都剩不下了。
雨下得太久了,我记不起这是连着第几天的雨了,大概多半的时间我不是昏迷、就是游离在昏迷边缘。我尝试过按压伤口,希望疼痛可以让自己清醒一些,但不起作用,从衣服上撕下冒充纱布的布条早已经被血污凝结成黑褐色的硬块,纵然使劲压迫,也不过渗出几丝暗淡的血水,没有半点疼痛,兴许将近半个月了,早就麻木了,这该死的伤口!
不清醒的神志让我无法给这几十页文字添上一个攀得上某种“意义”的结局,但不妨碍我再擦一次伴随我太久了的SVD,我叫不出它的全名,只能从枪托上认得这个简称,也或许不是它的名字,但这也没有关系,我也没有机会向别人介绍它。
雨天的山洞对它是不利的,最少应该上点油,但这也不可能了,只能用袖管反反复复的擦拭枪身。子弹还很充裕,我决定任它浪费了,昨晚还曾动摇过这个想法,因为夜晚总带着某种诡异,一度想用子弹结束这生死边缘的游荡。挣扎良久,但最终还是不能,我不能这么做,尽管太多应该去做的事都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不自杀,算是最后的自我安慰吧。我太需要安慰了,从阿媚她们离去之后,从那夜里毅然决然的告别那小寡妇,我身边再没有出现过能与我说话的活人,所以,只能暗自设立一些准则,聊以zi慰、自持。
虚弱的感觉一阵一阵的袭来,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阵倒下,失去所有知觉、然后渐渐冷却。躲不掉,那就干脆点吧,心底里开始期盼这一刻尽快来临。纯粹的等待实在煎熬,我所能借用的方式就是翻开本子,把写给自己的文字再从头读将下去。
直到肌肉完全失去控制,任由本子掉落在地,眼睛再也无力睁开,整个世界空洞洞的,只剩下虚无、只有真空,身体不再有任何重量,飘乎乎荡漾在半空里。
再见了雪鸳,再见了阿媚。
蜘蛛,老头子和阿姨、魁子、小傻以及阿布,还有那枉死的猎人,我来了……。
命运真是机关算尽,我这样浑身鲜血的人是连一抔黄土都配不上的,能够腐烂在一个山洞已经算是莫大的恩赐了,至少算不得曝尸荒野。
知足了,为这没有凄惨彻底的结局,为遇上了梅儿和雪鸳,为了很多人。
阴阳路原来是不存在的,至少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的,但是却有热量,有人声,或高或低,或远或近的传来,似乎还有隆隆的炮火、哒哒的机枪……。
“……醒来,必须醒来!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这句话似乎很清晰,我没有听完整,但后半部分却很真切。见鬼去吧,都死了,还跟我提任务?还必须完成?我活着那么长时间也才接过一次任务,就此死在异国他乡的山洞了,这时候,哪个死鬼在和我提什么任务?
我似乎有了一点意识,仿佛睁开了一下眼睛,但强烈的光立即把眼睛锁上了。
“他醒了,眼睛动了”,一个女人的尖叫无比尖锐的传入我的耳朵。
“快,把翻译叫过来”,一个粗壮的嗓音响起。
“能听到说话吗?”,声音就在耳边,是个低沉的男声。
“嗨,他听得懂个球啊,你用点药,等翻译来了慢慢问”,粗壮的声音再次吼道。
“谁啊,我怎么听不懂”,我本来是想大声吼的,可却使不出劲,嗓子干裂,声音嘶哑低沉不说,还导致我后半句几乎发不出声。
“他听得懂,是醒了”,哪个原本低沉的声音此刻兴奋了起来。
“哟,还懂汉语?看来是个秀才”,粗壮的嗓音此时也放低了一些。
“我在哪里?”,我努力把这句话说得尽可能的清晰。
“你在医院,中国解放军的医院”,低沉的声音特意放慢了语速,一字一句的回答道,似乎怕我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