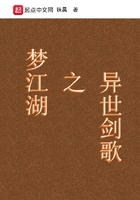灯火阑珊的街道旁,有一栋开发商不愿意光顾的孤楼。它靠着四周的商铺以及一堵破破烂烂的石墙堪堪构成了一个院子。我有幸能住在这样的一个院子里来眺望远处的繁华。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盘着腿赤裸着上半身坐在床上,旁边是一张陈旧的木桌。由于木桌的存在,这个房间看起来有些拥挤。木桌的前面是一张凌乱的双人床,床上的被子枕头胡乱的扔着,床单上有很多褶皱。而桌子的后面是一块木板,上面铺着脏兮兮的褥子和床单,大小刚好能够睡下一个人。
桌子的左边是一排柜子,中间的矮柜上有一台大屁股电视,我也不曾见过它发出光亮和声响。其余的柜子上有放着米油盐,也有放着衣物。不堪岁月洗礼的柜门早已歪向一旁,露出了里面油腻腻的物件,偶尔还有几只蟑螂一闪而过。
我用力挠了挠脖子后的红疙瘩,一阵舒爽过后又是难以忍受的瘙痒,这样的红疙瘩在我身上还有很多。但是人的神经总是很奇怪,关注那一处地方的话,其他地方倒是感觉不到了。我望了望发黑的墙上,上面有着密密麻麻蚊子的尸体以及一摊摊污血。
我很希望它们能够知难而退从而留住它们的性命,但千百年的漫长进化早已注定了它们的命运。
我很想关掉那扇窗户,但室内污浊的空气像一把锥子一样刺激着我的鼻子,夏日固有的燥热使我的后背激起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人类总是趋利避害的,小小的瘙痒挡不住本能。窗户仍然开着,望去竟是一片漆黑。
我盯着眼前的两个大碗,一个盛着几块烙至金黄的死面饼,另一个盛着撒着胡椒粉的土豆丝。我等了一会,也没有新的东西摆在桌子上了。
我撕了一块饼放进嘴里,又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机械的咀嚼着。由于需要吞咽的物体较大,唾液无法完成给食道润滑的任务,我的喉咙里仿佛塞进了一块烙铁。饼的干涩以及胡椒的辛辣一股脑冲上了我的头顶。四处寻水无果,我只得伸长了脖子,用唾液安抚我火辣辣的喉咙。土豆丝给我的感觉并不好,我只得再度吃了几块饼结束了这次晚餐。
我的面前还站着一个中年男人,说中年似乎也有些不当,毕竟他的头发已经半白,稀疏的头发也不足以遮挡头皮。阳光暴晒下黑棕色的脸庞上沟壑纵横,身体也略显干瘦。他冲我笑笑,露出一嘴黄板牙来。“再多吃点,别吃不饱。”他显得有些局促,两只粗糙的手交叠在一起互相揉搓着。
他的手背上遍布疤痕,其中一条甚至延伸到手肘关节处。看起来就像一只蜈蚣在手臂上扭动一般。
我拒绝了他的好意。
我从床上直起身来,随意披了件衣服,穿过昏暗的走廊,推开破旧的木门。木门痛苦地发出一声昂长的呻吟,在漆黑的楼道中显得格外响亮。
楼道比室内更为来得昏暗,被晚风吹得啪嗒作响的铁窗勉强透过一丝光亮,以使得我可以看到一片片朦胧的轮廓。
我缓慢地走下楼梯,虽然脚底都是一团团幽暗,并且鞋底传来一阵阵与异物接触的不适感。但我依然走得很轻松。
经过转角,一道瘦高的影子逐渐拉长,一点忽明忽暗的火星摇晃在楼道中间。我经过他的身旁,那影子突然停住了。借助零星的光亮,我看到那其实是个形如枯槁的男人。黑暗中只能看到他的鼻梁,眼窝黑洞洞似乎没有眼珠。
他抬起手臂扔掉烟头,手臂上一排针眼触目惊心,他转过身来,面向了我。
我虽然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我觉得他的眼神里都是掩饰不住的疯狂。
如此狭窄漆黑的楼道里,被一个丧尸一股的男人盯住,我本来就不太好的心情变的更加糟糕了。
“吴浪,你要记得这是在哪里。”
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完全不像一个年轻人发出的声音。
“抱歉。”那个影子说话了,残破的身躯里发出的声音出乎意料的清脆,使我想起了外面世界十六七岁的少年。
他捡起还在冒着火星的烟蒂,佝偻着身体渐渐模糊,最终消失在黑暗中。
我认识这栋楼的绝大部分住户,他们大多数都是被欲望所吞噬,或自由过了头的人。外面的光明世界早已不接纳他们,只能躲进城市里的犄角旮旯,躲进黑暗舔舐伤口。
这些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最后可以容纳他们的地方,可以不必在逼迫中变得更加疯狂,可以在稳定的黑暗中忏悔,妄图做出改变。
我走出院子,沿着纵横交错的小巷前行。黑暗渐渐从我身边褪去,路灯昏黄的灯光也开始零碎地撒在身上。不知道过了多久,眼前突然变得豁然开朗起来,一条宽阔的大路,路边明亮的灯光,路上呼啸的车辆,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
这座城市在北方扎根,虽然经济发展比不上沿海城市,且在北方地区也不比其他城市繁华,但所幸气候还算宜人,四季分明,人们过得也算舒适。
我在路边的车站停下了,面对着来来去去的汽车,和路上斑驳的树影。灯光将我的影子拉长投射在路中央,随着车辆的往复不断曲折着,突然被压缩成短短的一条。
透明的玻璃上映出了我苍白的脸庞,我还没来得及正视自己,那脸庞就转向一边去了。随之看到的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投币箱,一个疲惫的司机,和一扇半开的窗户。
我在司机审讯的眼光下将一张揉着皱皱巴巴的纸票塞进了那个箱子,走进了车厢。
晚风透过敞开的车窗卷进车厢,一排扶手随着车厢的晃动在有规律的摇摆。后排角落里坐着几个沓拉着眼皮的中年人,因为疲惫整个身子都陷进了座位里,头则随着车子的前进不受控制的晃动着。
最后一班的汽车总是如此,甚至那几个中年人我还似曾相识。这个年纪的人需要为两代人维持生计,承受压力,这一点回家的时间可能就是他们一天中除了睡眠时间外最长的休憩了。
在不知是电子合成还是录音的报站声落下后,我回到这个我已混迹两年的学校了。是的,我还可以走进大学。我曾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就只能生活在黑暗中了,没想到我还可以成为国家力量发展的预备队中的一个成员。
虽然我所学习的东西和我当初梦想的背道而驰,但是我很珍惜这段日子,因为我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再次陷入泥潭,再次和这些来之不易的光明擦肩而过。
我伪装的很好,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名普通的学生。有标配的三两个朋友,不上不下的成绩,广泛的爱好,无波无澜的生活。既不被别人喜欢,也不会让人生厌。
但我很清楚,我内心深处的阴暗,手里的血腥,终究会在某天爆发,摧毁我现在珍惜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