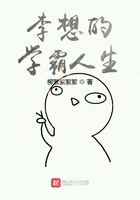“定州府尹……”宋瑾的手指在木桌上一下一下地敲着,“可是姓刘?”
“正是。”秦空点了点头,“冯太师早年与一外室育有一子,名唤冯渊的。因着这冯渊是外室之子,不得入冯家族谱,也一直住在外头。但毕竟是冯太师血脉,仍是丰衣足食养大了,养出了一身的富贵病,不过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就染上了花柳病,没过多久就死了。谁知他死后,有一风尘女子拿着一枚冯家玉令闹到了冯府门口,怀中还抱了一个不过月余的婴儿。女子在冯府门口叫嚣,道是她怀中的婴儿是冯太师的孙儿,若是冯府的人不给她个交代,她就和孩子一起撞死在冯府门前。冯家怕事情闹开了丢人,将她放进了府中,以她所说,这孩子是冯渊的种。冯渊与这女子交好,后来女子有孕,冯渊便用这枚冯家玉令哄着她把孩子生了下来。谁知孩子生下来没几天冯渊就咽了气,一个烟花女子带着孩子,毫无谋生之计,这才带着孩子闹了过来。”
“这女子也是个聪明人,她专门挑着人多的时候,带着孩子举着玉令在冯家门口闹了一通,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进了冯府,冯家也不好对她动手。后来冯家给了她一大笔银子,封了她的嘴,对外只说这孩子是冯渊遗孤,生母在生下他时就夭折了,冯太师体恤孩子年幼,做主将这个孩子过继到了庶子冯潮房中,从了冯家孙辈的名,名唤冯之坅。”秦空笑道,“冯之坅倒是个争气的,取了功名,在京中做了个小官。他的养母是冯潮的小妾,给他做主了一门亲事,便是定州的刘氏。”
宋瑾不屑地笑了笑,道:“难怪竟能如此猖狂。”
“定州刘家仗着自己与冯家的这门姻亲,又是父母官,在定州作威作福。”秦空神色仍是如常,说出的话却有些颤抖,“一边吃着皇饷,一边搜刮民脂民膏,还纠结了一群土匪和地头蛇,任凭他们欺行霸市,拦路抢劫,只要交了银子,一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秦先生。”宋瑾打断了他,“你既然知道冯家势力滔天,与我说这些,就不怕我也与他家有所勾结吗?”
“秦某寒窗苦读十余载,却不是个踏实本分的读书人。如今我既然敢在京城四处散发《凌州故》,就不怕丢了这条命。”秦空笑道,“况且我自恃有几分识人之能,看得出王爷绝不是与冯家一丘之貉。我自小失了家人父母,多年来无依无靠,今日这些话说与人听了,就算一死也可瞑目。”
“呵呵。”宋瑾微微一笑,“先生费尽心血,如今若真的一死,岂能甘心?”
“小人费尽心血,自是有心中所追所求之物。”秦空抬起头来,“那么王爷为了小人费心费力,又是在追求什么呢?”
宋瑾眯起了眼睛盯着他,并不开口。秦空接着道:“若小人没猜错,今日皇上处罚王爷的旨意应该已经到了王府了吧?”
“先生神机妙算。”
“昔日我在林府门口第一次看见王爷,王爷对我出手相助之时,我就知道王爷与那些权贵有所不同。”秦空的脸上带上了些真诚的郑重之色,站起身来对宋瑾拱了拱手,“王爷与我确有救命之恩,若非王爷施以援手,我的这条腿怕是都要废了。”
宋瑾摆了摆手,道:“无妨,不过举手之劳罢了。”
“不过最令在下惊奇的,是当日从林府跑出来的新娘子,今日竟然已经是四王妃。可见时移世易,事实皆不可料。”秦空话锋一转,“王爷为了娶这位王妃,实在是费尽了心思。”
“哦?”宋瑾面不改色,“先生何出此言?”
“那日在下本是在林府门口乞讨,彼时喜宴方开,林府的家奴把在下赶到了一旁的小道边。”秦空笑了笑,“小人恰巧看见了那日大闹婚宴的怀孕女子,只不过她身后还悄悄跟了一个黑衣人,那黑衣人走起路来全无声响,而且身形隐得巧妙,若非我看得仔细,实在难以察觉。直到她冲进了林府,那黑衣人才悄无声息地离开。”
秦空说到此处,指了指站在不远处的离桥,道:“就是这样的黑衣人。小人不才,对重要的人和事向来过目不忘,依我看这位壮士和昔日那黑衣人,身形确有九分相似。”
宋瑾眼中露出几分凉意:“先生这般聪慧,当知过慧易夭之理。”
“自然知道。”秦空丝毫不惧,“那日王爷派王妃来救在下,我再见到这位壮士方才将前事联系起来,方才说得也不过是猜测罢了。说到底,王爷的私事与我无关,我在意的,是王爷所求之物是否与在下相同。”
“那么本王就要请教一下先生了,您所求为何?”
秦空顿了顿,字字铿锵有力:“君为尧舜,臣为稷契。”
宋瑾听了他的话,先是小声笑了笑,随后似是再也忍不住,仰天大笑道:“好一个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先生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自然清楚!”秦空声音也大了三度,“如今朝中君不君,臣不臣。王爷可看看罢!为君者一心想得是如何制衡权术,为臣者一心想得是如何笼络人心,有谁肯为了这苍天百姓想一想!下月即是春闱,届时能中选的有志寒门学子又有几人?如此下去,朝中尽是尸位素餐之人,我南陵国运又当如何!”
他大概是太过于激动,又或许是这些话在他心中已经埋了许久,如今一口气大声说出来,他整个人都有些颤抖,可是他目光炯炯,眼神明亮。宋瑾原本已经有些想不起那日林府门口一定要将一对花镯还回去的乞丐,可此刻那双眼睛与记忆中的眼睛重合起来。他不禁起身,对秦空郑重地行了一礼,拱手道:“先生虽然身处困境之中,但一颗济世报国之心实在令人钦佩,宋瑾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