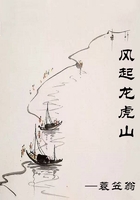“看也看了,可以让贫道走了吧?”道人收剑入鞘,漠然看向陈庭安,却是心中有气。此番来前,他本已起了一卦,乃上中之像,哪知最后却是赔了灵符,又折了颜面,无功而返。
“道长见谅!”陈庭安惭愧一笑,急忙退开,却是因自己三番两次拦住道人而颇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此时便是有心想留,也不好再留。
道人哼了一声,大袖一拂,负剑走远。众人这才欢呼一声,纷纷围了上来,一边痛骂那道人狂妄,一边惊叹着陈庭安谈笑之间退强敌的神通法术,知道他将长驻此地,心中亦安定许多。
陈庭安一一谢过,待众人走远,又听梅阿公交代了几句,方抱起球球,关上庙门,回到房中。
“球球,你可知道那葫芦籽的底细,究竟是个什么灵物?”陈庭安知道球球天生异种,冥冥中便有一些记忆传承,开口问道。
“我毕竟启智不久,纵然有些记忆,也都十分模糊。不过那葫芦籽应该是枚灵种,只是不知是何品类,感觉有些不祥,还是少接触为好。”球球蜷在陈庭安怀中,懒洋洋开口。不过还好此间没有外人,不然见它开口,怕是要吓一大跳。
“嗯,既然如此,以后再遇到那道人,倒是可以跟他提醒一下。不过他大概会以为我在唬他,诈他那枚葫芦籽呢。”陈庭安心想,摇头笑道。
“唔,不用理他!”球球正躺得舒坦,顺爪探去,从陈庭安手中捞过一团灵气,眯着眼愉快吞吃起来。小庙之中,午后阳光洒落,树影婆娑,却是十分静谧温暖,又哪像个潜龙卧渊之地?
此厢,一人一猫独享清静。那边,道人却怀着满腹闷气回到清风山,入了观中,也不打坐,径自拉过被褥大睡一场。次日起来,又去松林中捉了一只长尾山鸡,用松枝烧了,就着壶中猴儿酒吃个干净,方觉得气顺了些。
偏在这时,观外又传来一阵扑棱扑棱的声音,却是一只翼长九尺的白色大鸟,掠着一双羽翼从天而降,正落在松林空地上,又将浑身羽毛一抖,却化作一位面容冷峻、双眉高挑、身披白大羽氅的白衣秀士。
“二哥却来作甚?”道人心情方变好一些,见了这年轻人,又开始有些烦躁,不耐道。
“听闻三弟得了县令敕封,入了祀典正统,有朝一日大道可期,特来相贺!”白衣秀士扬眉一笑,方看见道人正愁眉锁眼、唉声叹气,好奇又问:“看三弟这幅模样,莫非二哥消息有误?”
“二哥消息倒是灵通,可惜此番好事,却被贫道自己搞砸了!”道人见白衣秀士哪壶不开提哪壶,心中更生懊恼,闷声回道。
“哦?竟有此事?”白衣秀士惊讶,他知道自家这位三弟,虽然平时行事有些荒诞,但真本事还是有几分的,不过小小一座长安县,也没听说有什么大人物,竟能让他铩羽而归,忙问究竟。
“唉!”道人一言三叹,便将其中经过简要说了一遍,为了掩饰颜面,难免又将陈庭安说的更厉害了几分。
白衣秀士听完,又问了几处细节,抚掌便笑:“三弟,你向来狡黠,这次却是身在局中,一个不慎,上了那庙祝的当了!”
“二哥此言何意?”道人见秀士突然发笑,本来有些恼怒,此刻听他开口,勉强压下怒火,闷声问道。
“三弟你想,那庙祝与你争斗三场,可都是你先提出?”秀士一问。
“正是,我本以为自己这三项神通已是十分玄妙,没想到竟被他不动声色破去,着实让人难以想象。”道人不知其意,闷声作答。
“那你二人,除了三轮比试,那庙祝可还曾显露别的手段,有甚奇妙之处?”秀士二问。
“没有,除了破去我三项神通,那庙祝再未显过其它手段,也不知他到底有何神通。”道人再答,依然不乐。
“三轮比试,你可都是感觉周遭灵气枯竭,法术难以维持,不攻自破?”秀士三问。
“正是!”道人此时,也已有些回过味来,惊问一声:“莫非?”
“大概便如三弟所想。”秀士点头,笑容一敛,眼中寒光闪过,冷声道:“那庙祝,大概本身并无甚了不得之处,只是掌握了一门奇妙功法,能够枯竭灵气。”
“而三弟你平生最得意之三大妙法,一旦施展,必须要从外界源源不断汲取灵气,如此方能维持。因此那庙祝正是击中你的法术短板,让你不攻自破。”
秀士说完,道人也已完全明白,起身站起,狂怒一声:“那道人竟敢如此欺我!”接着却又颓然坐下,“罢了,只怕那庙祝能够习得如此妙法,实力怕还不止这些。我既输了,终归还是自己学艺不精,不争了!”
道人心灰意冷,那秀士却不肯作罢,冷笑道:“三弟当真如此没有信心?我看你那上上之卦,怕是倒应在了这里。”
“嗯?二哥此言何异?”道人抬头,奇道。
“三弟你想,我等修行,莫不是要心境圆融,定心神于那清静之中,如鱼吞水,缓缓吐纳天地灵气,如此方能得一点裨益,其过程可谓十分温和。”
“但那庙祝,却能在刹那之间让一地灵气枯竭,衰你法术,灭你神通,这样的霸道功法,你可见过?”秀士冷笑又问。
“还真是从未见过。”道人坦言,“不过世间功法万千,这倒也并不稀奇。”
“若真只是一门破灭神通的功法也就罢了,怕只怕,那庙祝习得却是一门吞纳之法,于刹那之间鲸吞蟒吸,以致一地灵气枯竭。”秀士一叹,心中更生向往。
“怎么可能?”道人闻言一惊:“那天地灵气,如此浩大,我等修行之时,便是不慎多取了一些,也要担心如那拦河束水,一泻千里,浑身爆裂,这世间又怎么可能会有如斯功法,这般神通,这般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