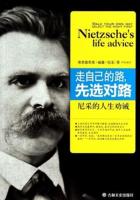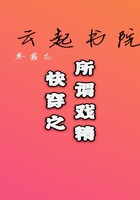叶适对心性之学的这种批评,是建立在自己对儒家之道的独特体认的基础上的。按照叶适的理解,儒家之道的精神绝不在心性等内在的层面上,而是在典章制度、名物器度等外在的人文世界之中。他说:“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贤经世之业,非习为文词者所能知也。”“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是叶适关于道物关系问题的典型表述,是理解叶适说体认的儒家之道的关键。在叶适看来,儒家之道不在内在的心性层面,而在外在的“物”之中,他之所谓物,是指从自然、人事到信仰等与人相关的一切领域,道的存在与这些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牟宗三先生所理解的叶适之道是“全部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中的有形有迹的器度和无形无迹的事件属于叶适之所谓物,其中的精神性内容属于叶适之所谓道。
叶适把道落实到“物”中去,这与同时代的道学家或把道与心联系起来,或与性联系起来,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长期以来学者们把叶适当作事功学代表的原因之所在。但是,把儒家之道推展到外在的器物层面只是叶适对儒家精神所作体认的一个方面,他在把儒家之道推展到“物”中去的同时,也架设好了把道拉回到主体内部的桥梁,那就是他所说的“习学”。与道学所指示的心性内在、慎独成圣的道路不同,叶适指示的是一条“习学成德”的内圣道路。叶适说:“《洪范》言九畴天所赐,而作圣实本于思,其他哲、谋、肃、乂,随时类而应,则思之所通,诚一身之主宰,非他德可并而云也。然傅说谓‘惟学逊志’,‘道积于厥躬’;孔子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思学兼进者为圣。又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是则学者圣之所出,未学者,圣之所存,而孔子教人以求圣者,其门固在是矣。”“圣”无疑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目标,既指个体道德的完美,又希望个体对自身之外的世界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内在的个体自觉与外在功业的统一。叶适说“学者圣之所出”,并认为这是孔子教人求圣的不二途径,都清楚地表明他希望通过“习学”实现致道成德理想的思路。这是叶适的“习学之道”外王内圣哲学的最终落脚点。
叶适是通过经典解释学来呈现自己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也是在经典解释学中对思孟后学乃至朱陆之学展开批评,这就要求他在经典解释中运用的具体方法与同时代学者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方法中彰显不同的旨趣。叶适解读经典的方法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经解经的方法。叶适阐释经典,发挥经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从中梳理出一个体现儒家精神的“道”来。他所体认的儒家之“道”与同时代的其他儒家学者所体认的道不同,叶适认为儒学在受到了佛老等异端思想的浸染之后,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语言概念都受到了二氏之学的影响,其他学者所体认的道都已不是纯粹的儒道,而他以醇儒自律,“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返本溯源在儒家原始经典中体会儒家真精神,力求在先秦儒家的意义上使用概念,并通过概念去把握儒家精神。叶适在从事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在解释经典的时候,总是试图把各部经典打通,把不同经典中讨论相同问题的有关论述都集中到一起,使问题明确化,为自己对某部经典中某一问题的理解获得更多经典依据的支持。如叶适在讨论诗风的正变问题时,提出一个与传统说法不一样的见解,传统上都认为诗词和旋律是区分风之正变的根据,但叶适则认为诗风之正变应当以是否出于“道”,即是否与儒家精神相一致作为根据。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叶适在就诗论诗的同时,也援引《尚书》的内容作为论据,说:“论《风》《雅》者必明正变,尚矣。夫自上正下为正,固也;上失其道,则自下而正上矣,自下正上,虽变,正也。《小序》谓‘政教失而变风发乎情’审如其言,则是不足以自正,岂能正人哉!今之所存者,去其感激陈义而能正人,非谓怨愤妄发而不能自正也。舜皋陶庚歌,风之正也,五子述禹戒而作歌,得为变乎?”如果按照传统上以诗词和旋律为化分诗风正变的标准的话,叶适认为《尚书》中《五子之歌》尽为怨愤之词,则应属于变风,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以诗意是否处于“道”为标准去衡量各诗之正变,就不会出现经典之间的矛盾了。
又比如,叶适在阐述《周易》有关阳刚之德的问题时说:“观《易》以五阳并进,一阴乘之,乃有决去之义,犹曰‘孚号有历,告自邑,不利即戎’,然则非如是者不决,而犹有惧焉,盖德以畜言,不以决言。……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后已者(应为: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然则刚贵长而不贵极,决者,长之极,而势之不得已也,善养刚者,不使之至于极也。”叶适把乾道又称为刚德,是他在阐发《周易》这部经典时重点发挥的内容,与多数学者在理解《周易》时注意其中的阴阳对待思想不一样,叶适把“独乾”、“独阳”、“刚德”作为《周易》的中心思想,把乾道理解为天地万物的主宰力量,也是他所特别注重的人文世界的主宰力量,并以此作为自己哲学的形上学根据。叶适在阐发刚德的时候,把《易》与《论语》联系起来解读,意指他之所谓刚,不是孔子所反对的无谋之勇,并在培养刚德的时候,要注意分寸,不可使之达于极致。
以经解经的方法是叶适诠释经典的最重要方法,这是由他为学的目的所决定的。叶适为学的目的之一,是要为儒学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剔除其中自两汉以来所受的佛老哲学的影响,还儒学以本来面目,把他认为属于真正的儒家之道阐释出来。叶适为学的这一目的决定了他所能依据的材料就只能是儒家的原始经典,不可能借助后儒的解释,因为两汉以后的儒者都有受二氏之学影响的嫌疑,他们对经典的解释和发挥都不可靠。为论证某一问题,叶适只能运用原始经典,通过经典的相互诠释来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
第二,经史结合的方法。永嘉学派从他们学派的实际创始人薛季宣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史学的研究,他们的这一为学路向对日后绵延数百年的浙东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他们的批评者如牟宗三先生则干脆讥讽道“其所成者结果只是辞章考据而已”,话语不免刻薄,所论亦非公允,但也道出了永嘉学的一大特色,即特别重视史学。叶适与其他永嘉学者一样,在“以经制言学”的同时,也注重把对经典的解读与史实、史事结合起来,力图使自己的观点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并把这一点作为重要的学术标准确立下来。如叶适说:“‘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杜预所谓‘须数句以成言’者耶?史法、经法,孔子所加损焉者甚矣,经史之传,学者亦慎焉可也。”在叶适看来,经有经法,史有史法,两者都是学者所应注意的内容,“经史之传,学者亦慎焉可也”。至于为什么学者要特别留意于史学,因为史学可以服务于经学,最终为讨论哲学问题提供史实依据。他说:“以万章所问舜、象、禹、益、伊、百里奚事考之,知昔人固多汩于所闻而不订之理义。岂惟昔人,而后人亦莫不然。然后人之谬妄,则不如昔人之甚者,以后之史详而昔之史略也。然订之义理,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若孟子之论理义至矣,以其无史而空言,或有史不及见而遽言,故其论虽至,而亦人之所未安也。如孔子事,耳目最近,然苟非载籍,则壤地不殊而见闻各异者多矣。”任何理论都必须是经得起实践和事实检验,于史有据方能令人信服,否则就是空言。孟子心性天统一的形而上学理论显然是不符合这样的学术要求的,形上理论当然也不太可能难获得历史事实的支持。叶适遂以为孟子之论义理是“无史而空言”。永嘉学确立这样的学术规范,反映了他们鲜明的学术特色。
第三,经典结合现实的方法。这是叶适为学特点的显著体现,也是他外王思想的表现之一。当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在阐发经义时,对经典中的义利等道德问题慷慨激昂,令座中听众泪流满面的时候,叶适把对经典的解读与南宋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一方面希望从经典中获得对现实有益的启发,另一方面,也以现实有效性作为评判经典的一个重要依据。
如其在讨论《孟子》时说:“掌固‘造都邑,则治其国与其守法,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职焉’。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禹汤以前不知何如,而周司马之任如此,故虽小侯陋国,各有阻固,不得轻侵,而存者数百千年,孔子亦言‘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盖不如是则无有为国也。而孟子乃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此说既形,儒者世祖之。今长淮连汉荆襄,犬牙处绵数千里,无复阻隔,敌之至,我常荡然,而我之于敌,尺寸不能至也。此今世达议论,有国者不知讲,以存亡为戏,奈何!”叶适所引孟子两句话的下面几句是《孟子·公孙丑下》“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是孟子仁政学说中极度推崇道德力量、忽视物质力量,以道德代替政治思路的一个表现。叶适以南宋朝廷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的现状说明说明这一思想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并引《周礼》、《论语》等材料佐证。其目的是为说明《孟子》所标榜的道德政治在现实面前的软弱。
叶适卒年在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是南宋乾淳之际学术繁荣中最后谢世的学者,而且他哲学活动的高峰正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六年。我们不能说叶适关于儒家经典诠释的旨趣和方法在当时具有纠偏导正的意义,但他应该是看到了时代学术的偏颇,有感而发才集成《习学记言序目》。今天我们阅读他的著作对此应有同情之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