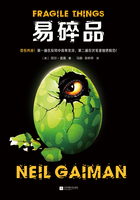四月末的一个黄昏,玛莉拉从妇女缝纫小组回家,猛然察觉到冬天已经伴随着欢乐的战栗结束了,而春天,却总是给人带来最为哀愁复古的情绪,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最青春最为快乐的情绪。玛莉拉没有分析过自己的思想,她可能以为自己在想着缝纫小组、工具箱,还有小礼拜堂的新地毯。在她的深虑之中,落日之中,红色的田野充满在淡紫色的雾气里,尖锐的杉林阴影覆盖了溪流上方的牧场,猩红的枫树环绕着没有任何波痕的池塘,灰色的草地下,埋藏着悸动和苏醒,春天已经在地面上铺开了。玛莉拉从容自若的脚步因为这最初的喜悦而变得轻快敏捷起来了。
透过繁茂的树林,她柔情的眼神落在了绿山墙,窗户将阳光折射出几道光芒来。玛莉拉沿着潮湿的小道走,想着穿过噼啪作响的杉林回家,就有一张铺好的桌子上面摆好了茶点,而不是像安妮没来时冷清一片,心里就十分知足。
结果,当玛莉拉进厨房时,觉察火是熄的,哪儿也看不见安妮的身影,这当然触怒了她,她已经告诉过安妮五点钟把茶点准备好,但是她现在却必须脱掉衣裳,自己准备做饭。
刚好马修从地里回来了。“等安妮小姐回家的时候,我得好好教训她,”玛莉拉毫无表情地说,她比平时更为用力地用刀子劈开引火用的木头。马修进来了,静心地坐在角落里等他的茶点。“她兴致勃勃地和戴安娜出去玩了,写故事,或者练习什么对话,就是这些无聊事儿。她根本就没想过要负点责任,这种事儿她想都不想,我可不在乎什么艾伦太太说她最伶俐了,最怜人了,她可能是很聪明可爱,但她一脑子胡话,以后还不知变成什么样呢,一个怪念头接着一个怪念头。但是,雷切尔太太今天在缝纫小组里说的话真让我恼火!我可真高兴艾伦太太站出来为安妮说话,要不然我就会冒出难听的话了。安妮有不少的缺点,上帝知道,这我没法否认,但是我在引导她,又不是雷切尔太太。如果加百利天使住在安维利的话,也会有人挑他的毛病,就是这样的。我告诉安妮今天下午得待在家里做事儿,她没有任何理由跑掉了。这可就是她的问题了,我以前还没发现她这么不听话,根本不可信,我现在可真后悔碰见她!”
“嗯,我不知道,”马修聪明地心平气和地听完了,而且他已经饿了,觉得最好还是让玛莉拉毫无障碍地把怒火爆发出来,他有过这种经验,假设没有被不知时候的争论打断,她这种时候手里的活会做得更快,“你太快下结论啦,玛莉拉,你在肯定她不听话之前别说她不可信,也许她有什么原因呢。”
“我叫她待在这儿,她不在,”玛莉拉反驳说,“她能有一个合适的说法给我是很困难的吧,当然啦,我知道你会帮她的,马修,但不是你管她,而是我。”
天黑了,晚饭也做好了,仍旧没有安妮的踪影,她没有匆匆地上独木桥或是走上情人之路,气喘吁吁地对忘记的事儿表示抱歉。玛莉拉淡漠地洗好了盘子,收拾好桌子,紧接着点了根蜡烛到地窖去,然后上楼到安妮的房间,她点亮了放在桌子上的蜡烛,看见安妮躺在床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
“上帝啊,”吃惊的玛莉拉问,“你睡了,安妮?”“没有。”安妮低缓的声音。“那你病了?”玛莉拉焦切地问,走到床边。安妮更深地把自己埋进枕头,就像她打算永远躲开别人的眼睛似的。
“哦,不要,玛莉拉,求您了,走开,别看我,我彻底的失望了,我再也不会在乎谁是班上头一名,谁的作文最好,谁在周日学校合唱团唱歌了。现在这些芝麻绿豆的事再也不重要了,因为我知道我从今哪儿也去不了了,我的方向迷失了。求您了,玛莉拉,走开,甭看我。”
玛莉拉被弄的莫名其妙了,“安妮·雪莉,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又干了什么了?马上起来,我说马上!好了,怎么了?”
安妮迷茫般的滑落在地板上,“看看我的头发,玛莉拉。”她的声音十分小。
玛莉拉抬高手中的蜡烛,认真地凝望安妮的头发,头发厚厚地滑到她的背上,看上去的确有点古怪。
“安妮·雪莉,你把头发弄成什么样啦?天哪,是绿色的!”
可以说它是绿色的,要是它真的算是种颜色——奇怪、阴沉、像青铜色一样的绿色,混合着一道道的红色,看上去就更可怕了,玛莉拉这辈子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奇怪的东西。
“是啊,是绿色的,”安妮低沉道,“我觉得没什么比红头发更惨啦,但现在我明白了,绿头发比它糟糕十倍。哦,玛莉拉,您现在知道我有多惨了吧。”
“我现在看见你弄成这样子,但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玛莉拉说,“立刻到厨房来,这儿太冷了,告诉我你都干了些什么?有时我希望发生点有趣的事,你都已经两个月没烦恼了,我知道就快了,现在说吧,怎么搞的?”
“我染的。”“染的?染发!安妮·雪莉,你知道不知道这事儿过分邪恶了!”
“我知道,我知道有点儿邪恶啦,”安妮坦承说,“但是我感觉邪恶能把红头发给吞噬了也是值得的,我算过这代价,玛莉拉,此外,我希望在别的方面做好点来弥补。”
“好啦,”玛莉拉嘲讽地说,“要是我觉得染发值得的话,我至少得染个体面的颜色,反正我是不会把头发染成绿色的。”
“但我没计划把它染成绿色啊,玛莉拉,”安妮垂头丧气地说,“我邪恶有目的呀,他说会把头发染得像乌鸦一样黑呢,他向我担保说会的。我怎么会猜测他呢,玛莉拉?我知道受人怀疑是什么感觉呀。艾伦太太说我们只要没凭证的话,就不应该怀疑别人说的话。我现在有证据啦,绿头发就够了。可是那时候我没有绿头发呀,我真心真意地相信他的话。”“谁说的?你在说谁呢?”“今天下午来的小贩啊,我从他那儿买的染料。”“安妮·雪莉,我告诉你很多次了!别让那些意大利人进屋来!我本来就不想让他们在附近打转!”
“我没请他进屋呀,我没忘记您说过的话,我出去啦,很认真地关上了门,就在台阶上看他的货。并且,他也根本不是个意大利人,他是个德国犹太人,有满满一大盒有趣的东西,他告诉我他要努力工作,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弄出德国。他讲话的时候流露出那么动人的感情,我都被他感动了,就为这个,我想买点儿他的东西来帮他。紧接着我就看见一瓶染发水,小贩说它能把什么样的头发都染成黑色,而且不褪色,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自己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这种诱惑太难抵抗啦。但一瓶要七角五分呢,我只有五角钱,我觉得他的心十分善良,因为他说因为是我,他就卖五角了,这和扔了没啥两样,所以我就买了。他一走,我就上楼来了,用一把旧发刷顺着他说的方向梳,我把一瓶都用尽了,哦,玛莉拉,当我发现把我的头发弄成这种颜色时,我悔恨自己这么不纯真啦,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在后悔。”
“好啦,我希望你的后悔有个好结果,”玛莉拉严肃地说,“你这回可得睁开眼睛瞧瞧了,看看你的虚荣心把你带到哪儿去了,安妮。上帝才知道该如何办,最好还是先洗洗你的头发,看看可不可以。”
安妮听话地洗头,使劲地用肥皂和水冲洗,但这不过是把她原来剩下的红头发又给洗成绿色了,小贩说不褪色果然真真切切,尽管在别的方面不得不怀疑他的真诚。
“哦,玛莉拉,我该怎么办?”安妮流泪着问,“我活不下去了,人们可以记得我其他的失误,止痛油蛋糕,把戴安娜灌醉,冲雷切尔太太发火,但他们忘不了这次的事儿了。他们会觉得我不值得敬重,哦,玛莉拉,‘准备欺骗时,我们编了张混乱的网’,这是首诗,但它是真的。哦,杰西·派伊会如何笑啊!玛莉拉,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我是爱德华王子岛上最悲伤的女孩子!”安妮的不快乐延续了一个星期,这一次,她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每天洗头发。戴安娜是外面唯一知道这个可怕的秘密的人,但是她庄重地发誓永远不说出去,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她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到了周末,玛莉拉决然地说,“没用了,安妮,这种染料不褪色,你得剪头发了,没其他的办法,你这情况可不能出门。”
安妮的嘴唇抖动了,但是她已经感觉到了玛莉拉的话是真的,她悲哀地叹了口气,去拿剪刀了。
“马上剪了吧,玛莉拉,剪光它。哦,我的心都碎了,这种感觉一点儿也不浪漫,书里的姑娘由于发热病把头发剪掉了,有的是为了钱把头发卖掉了,我认为要是这种原因的话,我就不会有现在的一半难受了。然而因为染了种可怕的颜色把头发剪掉就没法说服自己了,是吗?要是您不反对,您剪头发时我会一直哭的,根本就是场悲剧啊!”
安妮哭了,可是没一会儿,她上楼去照镜子,反而因此绝望平静了。这种事儿可不适意,得尽可能温和地说,玛莉拉的活儿做得很利落,剃得非常靠近发根。安妮立即地把镜子反扣在墙上。
“我再也不照镜子了,直到我的头发长出来。”她兴奋地宣布。
然后她又猛然把镜子立起来,“我必须照镜子,这是种惩罚,我一进房间就会看见自己有多丑,况且我不会幻想出头发来的,我从没想过我对自己的头发有虚伪心,可是现在我知道了,即使它是红色的,但它很长很厚而且是卷的,我下面的鼻子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安妮剪短的头发在学校掀起来波浪,但让她安慰的是,没有人猜出这里面的真正原因,甚至连杰西·派伊也没有,但杰西会错失良机地告诉安妮,她看上去活生生就是个稻草人。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安妮那天晚上告诉玛莉拉说,玛莉拉因为头痛正躺在沙发上,“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对我的处罚的一部分,我应该接受。人家说你像个稻草人当然不好受,我想回嘴的,但是我还是没有,我只是不屑一顾地瞅了她一眼,然后就原谅她了。原谅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厚道,是吧?我已经努力地想体现得好些了,我再也不会想让自己变美丽了,当然啦,做个好人相当好,我知道,但有时就是知道也不容易。我是真想变好的,玛莉拉,就像您、艾伦太太和斯苔丝小姐一样,长大了成为您的骄傲。戴安娜说等我头发长长了,就围着脑袋扎条黑色丝带,在一边打结。她说一定会很漂亮的,我叫它发网,这听起来相当浪漫吧,但我想得太多了,对吧,玛莉拉?您的头还痛吗?”
“我的头好多了,今天下午痛得很要命,我的头痛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必须去看医生了。至于你的喋喋不休,我不知道我还介意不——已经成为惯性喽。”
这是玛莉拉表达喜爱的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