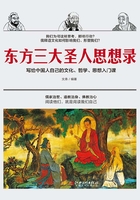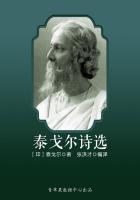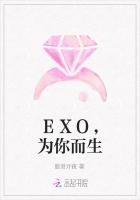吴宓在晚年撰写的《吴宓自编年谱》中对他留美期间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学至哈佛大学,从而结识梅光迪颇多感慨:“按后来事实之因果论之,则宓若在1918—1919学年,仍留勿吉尼亚大学,而不来到波士顿转入哈佛大学,则与梅光迪君在美国末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并不获由梅君导谒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则后来必无《学衡》杂志之编辑与出版。而宓一生之事业、声名,成败、苦乐,亦必大异,而不知如何。总之,一切非人为,皆天命也。”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吴宓流露出的淡淡的遗憾,吴宓的遗憾折射出整个学衡派的悲剧性命运。假如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思想,宣扬另外一种主张,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会迥然不同。然而也许真如吴宓所说冥冥之中宿命的安排,他们选择了文化保守主义这样一条不归之路。这一选择不仅造成了他们个人命运的坎坷多难,而且更令他们心痛的是,他们倾注了心血和真诚的“主义”却自始至终少有人同情和共鸣,反而招致尖刻的批判。这些批判有的纯属意气之争,有的来自文化学术界,而有的则是政治批判。面对这些批判,学衡派一度还能针锋相对,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无力回击,甚至保持缄默。
实际上本论文前面的内容已经揭示出了学衡派悲剧命运缘由之所在。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思潮。而从历史实际来看,现代化的道路是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侵略以后必然的选择。美国学者艾恺在分析这一必然性时说:
现代化到来的必然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1.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效果则见于能有效地动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物力,并且在国家体制的有效管理下和民族国家的理念之催化下,强化这一国家和地区。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作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
2.现代化在物质生活中所起的成效显而易见、立竿见影,而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隐患,则难以察觉。现代化真正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就拿个人的社会生活方面为例,它造成了社会的群体向个体的转变,功利观念的加强以及个人私利的计算,这一倾向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有增无减,发展趋势难以预测。
再者,个人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一旦提高水准则如同上瘾,而难以解除欲望,套句中国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可见,现代化实是任何国家必须选择的不可逆的道路。近代以来中国正是在这条道路上艰难前行。学衡派的主张.无疑是向现代化宣战。有学者将吴宓比喻为现代的堂吉诃德,实际上整个学衡派的行为也不啻为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面前,是古非今式的道德说教无论如何都显得苍白无力。
来自东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现代化的责难都认定现代化造成了人的价值的沦落。必须承认,这一指责并非没有道理。与现代化紧密相连的过分的功利化、理性化往往对人类的心智和肉体造成严重的戕害。这一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对于现代化的质疑几乎与现代化的历史同样长久,并且逐渐形成一股思潮。学衡派在近年来被人重视与中国学者开始对现代化道路进行反思有密切关系。可是问题在于,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出的药方是否就是更好的选择,是否真的能够真正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药方实际上就是道德理想主义。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都把道德价值看做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他们总是不厌其详地罗列种种的道德规定性,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活着,而有悖与此的生活选择则不被容许。他们理想的图景就是要造就一个“人人为尧舜”的社会。或许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能够实现某一种价值,但是却往往只能允许实现这一种价值。然而人的个性丰繁复杂,单一价值的实现往往是在牺牲丰富的个性要求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样,必然造成对个体选择的忽视乃至压制,这实际上是对人的价值的最大的不尊重。学衡派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常常“发思古之悠情”,在中西方的传统社会中发掘道德理想的资源。的确,在东西方的传统社会中,都以单一的道德价值为主宰,但这一现象的发生存在着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有其历史合理性。而进入近代,西方社会已经走出中世纪,个体的价值被发现,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已经吹响了个性解放的号角,在这样的背景下再鼓吹单一的道德理想,强调个人对群体无条件的服从,就是最大的不道德了。学衡派的悲剧即在于此,他们真诚地希望寻回人的价值,却无意中在阻拦中国人追寻生命价值与尊严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学衡派又被一些学者寻找回来,他们从学衡派的思想遗迹中发掘出了人文主义的旗号,重申高扬人的价值。孰不知这种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内核的人文主义极端轻视个体的自由选择,正是对人的价值的蔑视。
学衡派后来成为独断和不宽容思想作风的受害者,而在他们本身的思想中,独断和不宽容的倾向又是那么的明显,这是学衡派悲剧命运的又一体现。前文我们反复申说,无论是学衡派自身标榜的人文主义,还是后人给他们定位的文化保守主义,其思想实质都是一元化的道德理想主义。近代中国思想界,存在着形形色色诸如此类的一元化道德理想主义。由于受传统思想方式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社会现实的影响,这些思想都具有很强排他性。当某一种“主义”为当朝所用,其他的思想必然就要受到排斥和批判。有时我为学衡派成员个人的命运扼腕叹息的同时,会忽发奇想:如果学衡派的“主义”成为庙堂之学,其他学派会不会遭受与他们同样的命运?
那么学衡派学说的价值在哪里?其实给他们以适当的定位并非难事。在现代化的社会中,道德理想主义并非没有位置,善永远都应该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与现代化共生的商业社会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道德理想主义经常批判的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道德沦丧、价值失落、精神空虚以及科技发展给人类造成的灾难等等,并非是危言耸听,而确实是困扰人类社会的发展甚至生存的巨大问题。而道德理想主义则不失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一群人以维护道德的角度给予社会以批判、警醒的压力是非常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不要让这种批判成为依附于权力的独一无二的声音。多元并存和自由选择应该是最为理想的境地。
朱学勤先生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的结尾处对于道德理想主义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与新生作了极为精彩的论述,作者不惮其繁,抄录如下:
1.对历史的道德化要求,应从先验目的论转变为经验过程论。这一转变不是放弃理想主义,而是改变理想主义相对世俗形态的存在方式:从居高临下转为平行分殊,从空间扩张转为时间延伸。至善理念永远是可近不可即的目的,目的只有相对于过程才有意义。过程不是既定目标的当下空间,而是先验与经验相伴生的时间延伸。只有把道德要求从空间化为时间,才能切断观念形态走向意识形态的通道,才能避免道德理想变为一家独大、一时横溢的道德灾变。
2.对政治的道德化要求,应从谁来统治(Who govern)转变为如何统治(How govern),从哲学化统治,转变为技术性统治,以垂直上下的道德增压转变为平铺制衡的制度规范,以制度规范领袖,而不是让领袖凌驾于制度,在制度外搞“广场短路”。制度规范独立于“善”,独立于道德观念,以不善为大善,以非道德为最道德。制度独立于“善”,却是“善”的固态凝结,是政治体系内部道德要求的集中体现。一句话,永远放弃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王”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