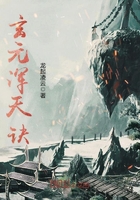江枫回到家里,草草地吃完了中饭,便给孔祥炫打了个电话。他要孔祥炫马上到江城新建的展览中心去跑一趟,专门看一看高明珠的油画展览,尽可能看得仔细一点,回来后马上将观感告诉他。孔祥炫有些奇怪,忙问他为何要让他去看高明珠的画展。江枫说:“我不想把意图告诉你,防止你预先带着框框。等你回来后,咱们再好好谈。”
一个多小时后,孔祥炫回来了。他脸色通红,头上冒着热汗,嘴里呼哧呼哧地喘气。闯进江枫的客厅,未及坐下,他便圆睁着眼睛骂开了:“他奶奶的,太无耻了!简直是彻头彻尾的欺骗!省委组织部长的女儿竟干这种丢人的事!……”
“看样子,你这一看,收获不小啊!”江枫说。
“收获太大了!”孔祥炫愤激地大声说,“这些天来一直闷在心里的这个谜,今天终于揭开了!小钟画了那么多画,想不到摇身一变,都变成高明珠的大作了!这些画,至少有十五幅,小钟在画的时候,搬进搬出,俺都亲眼见过!尤其是那幅叫《河岸》的画,是小钟在夏天画的,画的是古运河畔的一条林荫大道,他前前后后画了有半个月!”
“看来,小钟为了救妹妹,昏了头……”
“我也是这样想,为了钱,他把自己卖了!”孔祥炫愤愤地说,“而高明珠和她的那个当组织部长的父亲,还有那个当秘书长的丈夫,为了让自己、让女儿、让老婆快速出名,都昧了良心,利用小钟急于救妹妹而没有钱这个‘软肋’,弄虚作假,欺骗世人!他奶奶的,这是用金钱收买艺术的肮脏交易,这是一场欺世盗名的骗局!”
“为了这,小钟已经够难过了。”江枫让孔祥炫坐下,冷静地说,“他曾经为这件违心的事一再反省,说自己‘无地自容’,痛苦得如‘万箭穿心’;他帮助林荫编排导演《莲蓬人》,并且引用鲁迅的诗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我想,他出卖画作,实在是迫于无奈,应当给予谅解。而高部长他们一伙,倒是不能宽恕的,一定要揭露!”
“江老师,你看应该怎么做?”孔祥炫扑闪着深沉的眼睛,果敢地说,“俺可以随时作证,哪怕上法庭,俺也会挺身而出!”
“我想,他们做这种不光彩的事,不会只是孤零零的一桩。咱们得存个心眼,留心观察,倘若问题确实严重,到时候还得依靠组织。”江枫虽是一院之长,但始终只与学生和学术打交道,像今天这样的事还是头一回碰到,出于知识分子起码的道德操守,他觉得不能视而不见,姑息宽恕,但具体如何办,却拿不出主意;到临了,他与一切正直的教授学者一样,只会想到“组织”。在他们心目中,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就是“人民政府”,再不然,就是“公安局”、“派出所”,或者是“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对,江老师,你说得对,咱们最后得向组织举报!”
待孔祥炫一走,江枫又给伊露挂电话,将孔祥炫看到的问题告诉了她。伊露在电话里连连道谢,说:“你这个信息太重要了,说明咱们的怀疑确有道理!我这就去向总编汇报!”
挂完电话,江枫长长地吁了口气。他仰靠在沙发上,感到身心从未有过的疲惫。今天,当他看到高明珠的那几幅蝴蝶画时,他心里曾再次掀起了波澜。他想到了在蝴蝶池畔与高明珠的邂逅,想到了那条也叫“花花”的小狗,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与妹妹一起在春深如海的苏州乡下,在金黄金黄的菜花丛中追逐蝴蝶,快活得像疯了一样。“哥,蝴蝶,好看!”他仿佛又听到了那满含稚气的叫喊,听到了妹妹的喷泉般清亮的笑声。要不是赵璧辉那次断然否定了他的猜测,说不定今天他又会怀疑高明珠就是他的妹妹。然而现在,高明珠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的令人厌恶,叫人鄙夷啊;假如她真是她的妹妹,他会高兴吗?毫无疑问,这样的妹妹,只会让他感到难过,感到羞耻,感到痛心!她简直丢尽了他的脸!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妹妹,她的纯真无暇的妹妹绝不会变成这般摸样!可是,高明珠,这位高官的掌上明珠,竟然也爱蝴蝶,竟然也爱菜花,竟然也有一条叫“花花”的小狗!这些巧合,差一点对他造成了误导!这使他感到气愤,也感到不平。如此自私虚伪、追名逐利的女子,也配爱上这么美丽的蝴蝶、这么辉煌的菜花、这么可爱的小狗?现在,让他深感庆幸的是,高明珠并不是他的妹妹,赵璧辉为此而又一次训斥了他,讥笑了他,说他“犯了方向性错误”。看来,他的被训斥,被讥笑,真是咎由自取!然而,这位让他如此厌恶的女子,今天晚上竟然要带着丈夫前来登门拜访,她到底安着什么心?再说赵璧辉,这个一旦得势便官腔十足、盛气凌人的“小滑头”,今天居然对他表示了出奇的热情,这又是为什么?……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江枫做好了接待这一对不寻常的夫妻的准备。
晚上八点钟光景,江枫刚看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赵璧辉和他的老婆果真上门来了。因为这教授公寓所在地是个高高的平台,至今只有一条三十六级台阶的阶梯式通道可以上来(上平台的大路正在修筑),他们的汽车便只能远远地停在学校后门口的空地上。但那条也叫“花花”的小狗,却跟着它的女主人一起进了江枫的家门,而且与高明珠一起坐上了客厅的沙发。高明珠居然旁若无人地把它搂在怀里!
“老兄,你中午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溜了?我在扬子大酒店等了你半天!”赵璧辉这第一句话,乃是用责备来表示亲昵。
“江老师,我那次不是说了吗?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赵璧辉一直心存感激,想来谢你,可他就是太忙,一直抽不出时间,实在不好意思!好在时间还不算长。这不,今天乘展览会的空挡,我们赶紧跑来了。”高明珠不愧是高官之女,善于交际,八面玲珑,一番话说得十分得体。
“事情早已过去,咱们还是不提了吧!”江枫心里涌出几分厌恶,他努力克制,才不让这厌恶形之于色。面对老同学,他开门见山,实话实说,“今天赵秘书长在百忙中亲自登门,想必有重要事情吩咐吧!”
“哎呀,江老师,你这么说就见外了!还是老同学嘛,有什么好吩咐的?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感谢你!”高明珠说着,从随身带的一个棕色的手提包里(江枫一望而知,这跟林荫一样,是从意大利进口的“阔气”皮包!)掏出一个鼓鼓的大信封,站起身来,郑重地递到江枫面前,“江老师,这是我俩的一点心意,实在算不了什么,还望笑纳!”
江枫并不推辞,他接了那个信封,掂了掂,沉甸甸的,看样子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他右手捏住那包钱,对着左手的掌心轻轻地拍打,望着他的老同学笑道:“赵秘书长,你恐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你有什么吩咐,不妨直说。”
“我想问你,你看了今天的书画展,觉得怎样?”赵璧辉见江枫并没有拒收那包钱,一下子变得神气起来。
“你自己觉得怎样?”江枫似笑非笑地反问。
赵璧辉没有想到,江枫接了那包钱,不但没有对书画展赞一声好,反而用并不友好的口气反问他,这使他不胜尴尬。他好容易克制了自己的愠怒,仰起脸来,对着天花板说道:“我想,这个书画展,你如果觉得还看得下去,那么我倒想借助你的大名,请你写篇文章,宣传一下,哪怕只有千把个字。我想你还不至于拒绝我吧!”
“哈哈哈!我的秘书长老弟,想不到你如此抬举我!我的文章千把个字真能值这么多钱吗?假如我根本不要钱,我想你总不至于硬要我写吧。”江枫笑着,走到赵璧辉面前,将那包钱扔还了他。赵璧辉没有去接,那信封从他身上一直滚到地上。
“江老师,你这是——”高明珠从沙发上弹跳起来。她的善解人意的“花花”也随即“汪汪汪”地朝江枫叫了三声。
“我的秘书长老弟,今天难得你上门来,因为是多年的同窗,我想奉劝你几句话,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听?”江枫望着满脸愠怒的赵璧辉,恳切地说。
“好,你有话只管说!”赵璧辉仰倚在沙发里,没好气地说。
“咱俩师从林帆先生快要十年了吧,你还记得林先生在讲课第一天一再强调的话吗?”
“对不起,我没有你那么好的记性!”
“这话,后来成了咱们的座右铭,你总能记起来了吧!林先生说,不管做什么学问,都不能忘记四个字——务实求真。”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赵璧辉脸上的肌肉抖了抖。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做学问应该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
“你说,谁不老实了,谁又弄虚作假了?”赵璧辉脸色变青了,他指着江枫气咻咻地说。
“汪汪汪,汪汪汪!”那小狗也也朝江枫一个劲地叫。
“我看大家先别激动,这里面肯定有误会。”高明珠忙陪着笑脸,站起来劝架,“江老师,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一点?”
“我想,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那你就起来举报揭发嘛!”“嘭”的一声,赵璧辉一掌拍在面前的茶几上。
“赵璧辉,你这么激动干什么!”高明珠再次站起身,劝住丈夫,笑对江枫,“江老师,是不是有人对我的画发生怀疑了?甚至猜测这些画并不是我一个人画的?”
江枫脸色严峻,点了点头。他心里寻思,她总算有一点自知之明。
“啊哈哈哈,江老师,你相信这会是真的吗?”高明珠忽然大笑起来,她笑得那么自然,简直看不出一点虚假和做作,“告诉你,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这也正是我们要请你写文章的原因。我认为,一般的参观者对我的画产生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并不懂得油画。这就需要我们做必要的宣传和引导,帮助他们提高欣赏水平。这里面牵涉到很复杂的学术问题。江老师,你愿意听我讲一讲吗?”
高明珠的圆滑和世故使江枫震惊了。有道是,“偷来的锣鼓敲不得,”她倒好,不仅敲了,还脸不红、心不跳,振振有词,说出一番大道理来!他打定主意,先不揭穿她,且听听她到底说些什么。他随即笑着点点头。
“江老师,你知道,古往今来,国外油画的流派是相当多的,有古典主义,有现实主义,有浪漫主义,有象征主义,有表现主义,有超现实主义,还有野兽派、立体派、印象派、后印象派等等;各个派别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都大不相同,有的粗犷,有的细腻,有的质朴,有的华丽,有的圆熟,有的稚拙。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明白我的画为什么风格不一致,好像不是一个人画的。这是因为,我在不同的时期,学习了不同流派的油画。过去的几年,我迷上了古典主义,我对十七世纪法国最伟大的风景画家克劳德.洛兰尤其崇拜。洛兰的画风细腻精致,特别注意光线的运用,每幅画都像照片那样逼真。我画的《河岸》就是学习了他的风格。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画里的每一棵梧桐树,我都画得那么逼真细致;林荫道上的每一缕阳光,我都经过精心处理。最近几年,我又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被称为‘印象派之父’的法国大画家莫奈,就是我学习的目标。是他的那幅伟大的传世之作《日出印象》,将我领进了印象派的艺术大门。这以后我又迷上了后印象派的杰出代表梵高。江老师,你可以看到,梵高的那种粗犷的画风,在我的那几幅菜花蝴蝶画里,表现得非常鲜明:质朴的画面,粗硬的线条,辉煌的色彩,给人一种粗疏笨拙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独特的风格!……”
江枫的眉头不知不觉皱起来了,一股无法遏抑的怒气在他胸膛里奔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怀着极大的耐心听取一个人在他面前如此明目张胆地撒谎。这个与他妹妹一样年龄女子,穿戴得如此华美,长得又是如此漂亮,可是她的心灵却是如此的低俗,如此的卑下!这一番话,显然是事先精心编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那见不得人的真相。既要当婊子,还要树牌坊!天底下竟有如此不知羞耻的事!幸亏他多了个心眼,预先查明了真相,否则说不定被她大大地忽悠一通以后还莫名其妙!
“你的绘画理论学得不错。”他好容易克制了自己的怒气,望着高明珠,努力用温和的口气,缓缓地说,“你对绘画艺术有着很执着的追求,并且渴望能早日出名。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这一点,你一定比我更加清楚。刚才我特别提到当年我们的恩师林帆先生说的话:不管做什么学问,都不能忘记四个字——务实求真。从这四个字出发,我要坦率地说说自己的想法。今天看了你的画展,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你绘画的基本功还不够扎实,一些技巧还不够成熟。而你又急于成名,这样就带来一问题,就是你的画显得比较粗糙、稚嫩。不管你如何用流派、风格来作解释,都掩盖不住这个遗憾。至于艺术风格,我看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形成的,它是在艺术创作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以后创造出来的一种特色。这种特色,是以深厚的艺术功底为基础的。你的作品,恕我直言,欠缺的恰恰是艺术功底。而你的另一些画,无论构图、设色、用光,都相当老练、精当,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相比之下,反差确实很明显。参观者怀疑这些作品不是出于一个人之手,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江枫突然住了口。他发现客厅里的气氛像进入了寒冬,一下子冷到了冰点。赵璧辉的脸色愈来难看。他的高高翘起的二郎腿神经质地摇晃着,鼻子不住地哼,发出一声又一声冷笑。而高明珠,一张本来好看的脸蛋,此刻绷得紧紧的,从脸颊到脖子,全胀得通红;她的胸脯在剧烈地耸动,可以听到她大口喘气的声音。
“也许,我说得过于直率了……”江枫忽而有些心软了,他望着高明珠,抱歉地笑笑。
“什么直率!你分明是用‘莫须有’的罪名,要把这个展览一棍子打死!”赵璧辉终于暴跳起来了。
“江老师,这是你自己的看法,还是听了别人的话才这么认为?”高明珠红着脸问。
“此话怎讲?”
“比如说,是不是伊露跟你说了什么?”
“我跟伊露确实交换了看法,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
“你不会不知道吧,这个人历来喜欢兴风作浪,以造谣诽谤为能事,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上次的帐,我们还没有跟她算呢!”赵璧辉咬牙切齿地说。
“江老师,我没有想到,真的,我没有想到……”高明珠涨红的脸上满是怨艾和沮丧,大颗的泪珠从她颊上滚落下来,“我一向对江老师是那么尊敬,可是,今天,想不到……”她猛地一转身,乘势扑在赵璧辉身上号哭起来。
“起来,我们走!”赵璧辉扶起他的夫人,大声说,接着又对江枫吼叫道,“今天,你要对你的话负责!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花花”临出门时,也对着江枫拼命嚎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