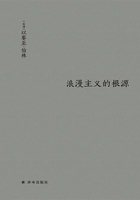“闺阁中历历有人”,这七个字,包括多少美丽的诗化生命,这些诗化生命与秦钟一样,像一面一面的镜子使贾宝玉看到自己的不肖,自己的丑陋。曹雪芹着写一部大书,正是通过他的自我谴责(对“我之罪”的承担)而让这些诗化生命继续生存于永恒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以免和自己的形骸同归于尽。中国最伟大的作家的“忽念”,即在一个神秘的瞬间中的灵感爆发,使他重新发现罪,也重新发现美。没有对“我之罪”的感悟,没有对男子世界争名夺利之龌龊的感悟,不可能理解那些站在此一世界彼岸的诗意生命是何等干净。只有心悦诚服地感到自己处于浊泥世界之中的丑陋与罪恶,才能衷心赞美那些与浊泥世界拉开距离的另一些生命的无限诗意。忏悔意识、罪责承担意识之所以有益于文学,就在于作者一旦拥有这种意识,他就会赢得一种“良心”,一种“自愧”,一种大真挚,一种对美的彻底感悟。
俞平伯先生虽然发现《红楼梦》的“忏悔”,但归结为“情场忏悔”却显得狭窄。其实,《红楼梦》既不是现实伦理关系上的“悔过自新”,也不是简单的情场忏悔,而是在对诗化生命的毁灭感到无限惋惜的同时又对自己无力救赎的衷心自责。《红楼梦》的作者及其人格化身与“闺阁中历历有人”的关系,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这些诗化生命的关系,有真情在,但不能简单称做“情场”,这是一种真正的诗化生命场,一种超越浊泥世界的童话场。福柯在《性史》中说西方人都是忏悔的动物,他们从中世纪开始的忏悔主题都是性真相的自白,卢梭的《忏悔录》也有此余绪。“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着名作家郁达夫的《沉沦》,也是性自白。
忏悔文学被某些学者称做自白文学,就在于此。这种作品的长处是敢于撕下假面具,正视人性自身的弱点,但它却把自白的勇敢本身视为写作的目的和策略,未能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红楼梦》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并非性自白,也不仅是情场自白,而是展示一种未被世界充分发现、充分意识到的诗化生命的悲剧,或者说,是一曲诗意生命的挽歌,而这些诗化生命悲剧的总和又是由一个基督式的人物出于内心需求而真诚地承担着。于是,这种悲剧就超越现实的情场,而进入形而上的宇宙场,换句话说,就是超越现实的语境而进入生命宇宙的语境。王国维以《桃花扇》和《红楼梦》代表中国文学的两大境界,前者是国家、政治、历史之境,后者是宇宙、哲学、文学之境,曹雪芹的忏悔意识正是附丽在宇宙之境中。
贾宝玉的基督承担精神,还可以从他的爱伸延到女子之外的一切人这一角度来说明。
从世俗的批评视角看,会觉得贾宝玉情感不专,爱了那么多女子,是个泛爱主义者。实际上,他在情爱上注入全生命、全人格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林黛玉。林黛玉是同他一起从超验世界里来的唯一伴侣,他对她的感情深不见底。对其他女子,他也爱,而且也爱得很真,也很动人,然而,所有的爱几乎都是精神之恋性质的所谓“意淫”。他爱一切美丽的少女,也爱其他美丽的少男,如对秦钟、棋官(蒋玉菡)、柳湘莲等,这不能用世俗的“同性恋”概念去叙述,这是一种基督式的博大情感与美感,是对人间最美的生命自然无邪的倾慕与依恋,因此,其中任何一个生命自然的毁灭,都会引起他的大伤感与大悲悯,都会使他发呆。他尊重任何一位女子,尽管在林黛玉与薛宝钗之间,他更爱林黛玉,但是,当家庭共同体把他推到薛宝钗面前时,他绝对没有力量损害薛宝钗,也正是这样才造成了林黛玉的悲剧。他对林黛玉有负罪感,对薛宝钗也有负罪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不仅爱属于净水世界的冰清玉洁的少女,而且对那些属于泥污世界的男人,尽管不能不与他们为伍,但他对他们也没有仇恨,甚至也是以大悲悯的心情对待他们。他的异母弟弟贾环,是个鼠窃狗偷、令人讨厌的劣种,常常和他的母亲一起加害宝玉,但是宝玉从不计较,仍然给予兄弟的关怀。有次贾环赌博输了,大哭大闹,唯有他去安慰说:“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别处玩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弃了这件取那件。难道你守着东西哭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得个自烦恼。”在这种开导中完全是兄弟的挚爱与温馨。还有,对那个粗暴又粗鄙的霸王,无恶不作的薛蟠,贾宝玉也可以成为他的朋友,和他一起打酒令。从表面上看,是俗。实际上是贾宝玉齐物之心与平常之心的另一种表现。尤其是他被父亲痛打之后,因宝钗知道与她哥哥薛蟠有关,正要询问,贾宝玉说:“薛大哥从来不这样的,你们不可混猜度。”(第三十四回)居然为薛蟠承担过错。
更加类似基督的是贾宝玉身上有一种舍身忘己的精神。他处处都先想到别人。他与基督出身于贫贱之家不同,是一个贵族子弟,而且是最受宠的子弟,但他总是忘记自己的身份,一点也不觉得比别人优越。他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问黛玉身上有没有—块宝玉,黛玉说没有时,他就扯下自己的玉石往地下摔。他身边的丫鬟,在世俗的眼中,只是一些奴婢,但在他心目中,和他完全平等,甚至比他还高贵。他不像其他贵族子弟那样,认为奴婢为自己服务是理所应当的,而是对她们充满感激。当他被父亲打得皮肉横飞的时候,听到袭人一席悲情的话,就感动不已,觉得自己被打没什么,而她们的爱怜之心才可珍惜。《红楼梦》第三十四回描写他被打之后见到黛玉的哀戚,他“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心中自思:‘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
假如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在疼痛中,玉钏儿给他端来莲子羹,不慎将碗碰翻,将汤泼到宝玉手上,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得,却只管问玉钏儿:“烫了那里了?疼不疼?”屋里的两个婆子议论此事,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说他家宝玉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气。他自己烫了手,倒问人疼不疼,这可不是个呆子?”另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吧’。你说可笑不可笑?”贾宝玉就是这样一个“忘我”、“忘己”的人,一心惦念牵挂别人的人,这确实是“呆”、“傻”、“糊涂”,但恰恰是这种性情接近神性。人的修炼,不是修炼到世事洞明,极端精明,而是应当修炼到如贾宝玉似的“呆”和“傻”。
基督出身平民之家能有爱天下平民之心自然宝贵,而贾宝玉出身贵族之家却能对奴婢充满挚爱,更为难得。康德说,所谓美,就是超功利。贾宝玉的精神之美,正是这样一种超越等级之隔尊卑之隔的纯粹感情之美。《红楼梦》中的《芙蓉女儿诔》,正是这种美的千古绝唱。这是一首可以和《离骚》比美甚至比《离骚》更美的绝唱。《离骚》吟唱的还是个人不被理解的悲情,而《芙蓉女儿诔》却是一个贵族子弟对奴婢的讴歌。这曲子,完全打破人间的等级偏见,把女仆当做天使来加以歌颂,这是一项划时代的了不起的文学创举。它礼赞这位名叫晴雯的奴婢为最纯洁的芙蓉仙子:“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这首长诗,不是“国”的主题,而是人的主题,个体的主题,生命的主题,是对宇宙的精英与人间的精英最真挚、最有诗意的肯定,它打破千百年来中国文学的“政治、国民、历史”的主题传统,开辟了“神圣诗篇属于美丽的个体生命”的审美格局。可把这首诗视为圣诗,它是真正的文学经典与美学经典。
虽说贾宝玉与基督的精神是相通的,但是,两者仍然有差别。这个差别最根本的一点是基督已经成道,而贾宝玉却只是在领悟中与形成中,他还未成道,还是一个“人”,不是神。换句话说,他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基督。一个完成,一个未完成。未完成的基督开始还沉浸在色欲之中,他与秦可卿、秦钟的关系都是一种暗示。所以,他还必须彻悟。而引导他从世俗色欲升华到爱情的是林黛玉,是林黛玉的眼泪净化了他,柔化了他。林黛玉是把贾宝玉从“泥”世界引导到“玉”世界的女神。
3“还泪”的隐喻
笔者曾把基督教的“原罪”概念引申到“欠债—还债”的责任情感:人既然被确定为生而有罪,那么毕生的无限救赎就是必要的。每一个行动,包括日常的琐事和职业活动,都可以看成是赎回先前“原罪”的活动。因此,生命就是一个忏悔和救赎的过程,就是一个“还债’的过程。换句话说,有罪的另一种非宗教的表述方法就是负有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只有倾听良知的呼声,感到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欠了点什么,才会努力弥补这个欠缺。努力的过程也可以描绘成归还——归还欠债——的过程。这就是说,从原罪的引申意义上说,忏悔的过程就是确认债务和还债过程。
《红楼梦》的忏悔意识很形象地表现为“欠泪—还泪”意识。
欠泪—还泪意识首先表现在小说文本中的故事结构:男女主人公的前身神瑛侍者(贾宝玉)与绛珠仙子(林黛玉)曾有过一段因缘际会。仙子原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女体。后来得知神瑛侍者下凡,她也跟着下凡,并抱定在凡间用眼泪还清“甘露’之债。第一回就有“还泪”之说:
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