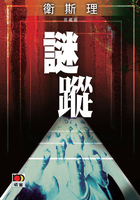那瓶昂贵的ChateauLatour我一滴未沾。但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摄入了可以放倒一头猛犸象剂量的廉价酒精。每一个宿醉的早上扛着快要裂开的脑袋走进办公室,我都怀疑自己把这辈子的酒量都透支了。可是天一擦黑,就又发现自己对酒精的渴望依旧炽热,原来出于自我保护,身体会把自己锻炼得愈发迟钝,或许也就愈发顽强。
为了避免反复陷入愤怒和屈辱的回味之中,我寄情于为自己炮制各种身心快感,热情地张罗着聚众饮酒,活跃在亲戚朋友的家庭牌局,买回各种口味甜腻的冰淇淋塞进冰箱,把家中电视换成四十六寸大屏幕,并配齐最近时兴的各色电脑游戏光盘,甚至还在日本网站上订购了一架价值不斐的高倍天文望远镜,想着说不准可以验证下小时候舅舅讲的华富村UFO事件。
记得看一本科学杂志上的文章说,真正掌控人情绪的终极物质是大脑中的多巴胺,酒精、赌博、美食、购物,甚至好斗、痴情,看似丰富多样的行为其实殊途同归,最终目的无非是刺激多巴胺的释放,让身体接收到“愉悦”的信号。曾经的热爱、钟情、依恋、动心,原本以为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全部物化为化学反应—身体成了培养皿,精神本无一物。想到这里,我忽然害怕自己没法再对任何人或事一片深情。
但人没那么容易超脱,即便在这个纯粹理性的多巴胺科学命题里。因为这些化学作用产生的快感让人上瘾,让人无力断然拒绝,放弃追求。于是就像被挟持一样,尽管恐惧,还是重新斟满了杯中的酒,欣然刷卡买下第无数双球鞋,殷切地为某支球队掷下赌注,点燃人生中又一支香烟,或许某个时刻,再次为一个女人心动。
又是礼拜五,下班时已经入夜,于是跟同组同事转战铜锣湾一家经常光顾的火锅店。贵宾室里的电视已经调到体育台,正在直播英超曼城对切尔西的比赛。场上比分胶着,火锅里热汤翻滚。眼睛望着慢镜头里球员大腿颤动着的肌肉群,嘴里咀嚼着筋道的肉丸。
我努力给自己的生活制造出一派沸腾景象。赌徒Michael和李公公因为买了这场比赛的足球彩票格外投入,摩拳擦掌,污言秽语,恨不得钻进屏幕里指挥战斗。我自小视切尔西为自己的主队,真情付出十余载,输赢心重,荣辱感强,多巴胺四溢。
突然电话响,是短信:“发email了没?”发信人显示“余春娇”,最近在公司后巷抽烟时认识的红发浓妆女孩,样子可爱。今天下午抽烟聊天的时候,我给她讲了当年华富村发现UFO的事,并且答应她把那件事的相关新闻发给她。
英明的李公公曾经有言,全面禁烟造就了一个机会—上班无端多了个泡妞的地方。如果没有禁烟这件事,即便在同一座大厦里上班,也鲜少有机会认识别的公司的女孩,如今附近几栋大厦的资源得以共享,江湖儿女得以加深了解,促进和谐,贡献良多—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officehour里发生,薪水照付。见她主动发来短信,我不由得感到几分惊喜,诚然本能而已,没有别的。
“Nothomeyet!”我回复。
“Whatrudoing?”
“嘿,我说你们俩是看球啊还是玩电话啊?”Michael对我吼,我四下一望,入职只有半年的黑仔也低头跟电话较劲。我低头继续回余春娇短信:“Hotpot,u?”没打算支声。
黑仔有反应,乜斜着眼望着Michael,“关你屁事!”场面有点儿尴尬,好歹Michael比黑仔资深,被如此抢白实在没面子。公公解围:“啧啧啧,后生可畏呀!公司就是需要这种不畏阶级观念的人么。Michael你以后好好用他喽。”
“朋友生日,唱K-ing。”收到春娇回信。
“喂,出去抽烟。”公公捅捅我肩膀,我收起电话,揣上烟,跟他走了出去。
“新妞啊?”公公点上支烟,漫不经心地问我。
“我也是黑仔那句—关你屁事。”我的眼睛没有离开过电话。
“靠,”公公撇嘴走开,骂了一句,“小心‘子宫’癌啊。”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没听明白一脸疑惑。
“大拇指啊!”
“靠!”我笑骂一句,电话又响,春娇说,“有点无聊。”
我发出邀请,“Wanttotakeawalk?”赛季还很长,想看切尔西的比赛,每周末打开体育台即可。而一个相貌还不错的女孩向你诉说“有点无聊”的心情的机会,却并没有英超赛程安排得那么紧密。
“Where?”她接受了我的邀请。
我想了想,输入三个字:“六个六。”就往旁边一条街上的SevenEleven便利店走去。据春娇所说,我们第一次碰面的地方并非公司大厦的后巷,而是这家便利店。但我饮酒断片,并不记得。“六个六”则出自我那天酒后的荒唐行径,由于很白痴,我不打算在这儿复述,权当是一个特别的暗号密码吧。总之春娇会意,我在绵绵细雨中抽了多半支烟的工夫,她打着伞出现在我面前。
“呃……你这是怎么意思?”春娇顶着一条长辫子,烟熏眼妆化得像两个窟窿,眼线就快要开到耳朵边上,红嘴唇鲜艳欲滴看着比白天大了一圈,活像一个刚从盘丝洞里跑出来的小妖精,吓了我一跳。
“一朋友过生日,cosplayparty呗。”她那口气好像在说我少见多怪。
我的眼睛没法不盯住她的前胸,耸得太夸张,把运动衣顶得老高,好像下巴底下开始就是乳房。“玩儿这么high!这里头是什么啊?”
春娇故作大方地挺挺胸脯,运动服被顶出两个尖尖:“哈哈,厉害哟!麦当娜!”
我忍不住大笑:“哎,是不是低头都看不见自己的脚啊?那你就直接穿出来嘛。”我凑过去,瞄着她胸前,“有多厉害?我看看?”
“神经病!”春娇笑着推了我一把,“大马路上露出来我怕吓着小孩……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不知道啊,一边走一边想吧……”我顺着街道往前走,地上的雨水映着过往的车灯,空气里一股清爽味道。
“为什么男孩约女孩出来,也不先想想去哪儿呀!”她举着伞赶上来,撅嘴嘟囔。
“第一,我很久以前就不是‘男孩’了。第二,也不算专门约出来嘛,是想大家碰巧都在这边,不如出来随便转转。”
“第三,我也是找你出来打发一下时间而已。”她笑着超过我。我被她这兜头一句搞得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只得悻悻地跟在她身后。
“第四,”她突然停住,“你姐我正好要买烟。”转身走进街边的便利店。
显然柜台里的店员也被春娇惊耸的打扮搞懵了,眼神里带着诧异。
“你好,我要……”春娇刚开口,我指着货架插嘴对店员说,“劳驾,把左边数第五包,皱纹Capri给这位小姐。”
店员忍着笑,把那包印着“吸烟可引致皮肤老化”警告的Capri香烟拿下来扫描:“谢谢你二十九块,要不要加五块钱买包薄荷糖?”
“不用。等一下……”春娇从钱包里又拿出两张二十块的纸币,“再要一包,把右边数第三包,阳痿LuckyStrike给这位先生。”
店员转身取印着“吸烟可引致阳痿”警告的绿色LuckyStrike,从后边看,他笑得肩膀颤动。春娇把烟塞到我手里,挑衅地仰头看着我,眼里却含着笑。
出了便利店,本来就不大的雨停了,尽管还是漫无目的地往前走,春娇也没有提出疑义。忽然她用手肘捅捅我,“你看……”顺着她的眼神望过去,一家关门的银行铁闸外支着个小摊档,上面摆满了贴纸、文具之类的小玩意儿,一男一女两个小贩神情漠然地守着摊档抽烟。“看什么呀?”我没明白她的意思。
“哎,你看多幸福啊他们俩,每天晚上都能一起开工、一起收工,多好呀!对吧?”
“你怎么知道人家好?”我又瞟了那两个小贩一眼。
“不好吗?又简单,又sweet呀。”她一脸的艳羡。
我不由得被她的傻样子逗笑了:“你头脑还真是简单。真是卖贴纸啊你以为他们?”
“啊?那是卖什么的啊?”
我看了眼时间,“晚上十点都不收摊,卖给什么人啊?难道是小孩这么晚才放学经过吗?还是说他们下楼买夜宵的时候顺便买贴纸啊?”
“那……你还不许那些爸爸妈妈下班经过给自己的孩子买贴纸么?”她反驳我。
“不信你过去看一眼,”我指指那个摊档,“全是灰尘啊那些贴纸上头,哪儿有人买啊?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做生意的。”
那对小贩好像听见我说话,朝我们这边望过来。我赶紧缩回指着的手,按在春娇头顶上,把这个正在傻看的女孩的头拧了个方向,
“嘘!别看了。”
“怎么啦?人家也没看你。”她在笑我。我没理会,眼睛望着别处,拽着她离贴纸档远点儿。
“干吗啊?”她踉跄着被我拽到一旁,不满地问。
“天文台啊!”我没好气地告诉她。
“什么天文台?”她一脸疑惑。
“你没听过啊?”不是我好为人师,是她不懂的太多,“天文台嘛!凡是附近有卖走私烟啊盗版光盘之类的,他们就在这儿摆个摊收风放哨,警察一有点儿什么风吹草动,就靠他们通风报信了。”
“是不是你自己瞎编的啊?”春娇不信,还笑话我,“被害妄想症吧你?成天觉得什么都有阴谋啊你?累不累啊?”
“不是我妄想,凡事都不可以光看表面。”这个道理很难被理解吗?她还是没反应。“你不信么?”
“信了信了,你全知全能,行了吗?警官,这儿整条街都是坏人啊,还不全抓回去?”
见她不服气,我也有点儿急,拉她到路边的石墩上坐下。她几乎是被我硬按在那儿的,“靠,你不信就一块儿跟这儿看一会儿。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是做生意的。”
“看就看,反正也不赶时间。”她托腮坐定,认真望着那对小贩。
说着就有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路过贴纸档,小女孩果然停下脚步看摊上的贴纸。春娇觉得她赢了,“看,有人买呀,有人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