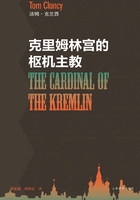宋学武
同我所从事的电影行当相比,文学在当今社会是奢侈的。我也很幸运的能在工作的筹备期奢侈了一回,读了何荷近几年的中短篇小说。
我不愿提,但不得不提:其题材之魄力,文风之凌烈令人惊讶,如我只通过之前的网络交流知晓作者是女性倒也罢了,但却还有幸曾在聚会上见过一面。而拥有如此精致的外在,散发文雅柔美气场的女性实难令人想到脑海里装的居然是前后跨越几千年,左右跨越几千里的杀戮,情欲,死亡与磨难,文字中激荡的那些鲜血和肉体的色彩总在人眼前跳跃,很容易就遮蔽了窗外的现世。而我之所以不愿意提,是因为大抵对于真正忠于文学的作者来说是不情愿被议论自己个人的,即便是称赞;而更愿意通过作品来得到读者的反馈,即便是批评。虽然这在当下中国文学界现实中显得很不现实,因为我们早已习惯先喜欢上一个名人再喜欢他的作品,而非通过作品喜欢一位作者,从而使他成为名人。这或许是文化圈被娱乐圈胁迫的结果。所以我虽然惊讶于作者外貌与内心世界的反差,但还是不愿把着眼点离开作品本身。
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第一次读女性作者写的军事题材小说,设想若我之前不知这是何人所作是否可窥探出作者的身份呢,用心的话想必不难,因其确与大部分此类题材小说极不相同。
《铁马冰河》一篇,“战争边缘”的定位确立了整篇的主题。以边缘的形式迂回的,多层面的推进描述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这在手法上是很现代的,令文章显得丰富且带入感强。最难得的是当我们随着一个与战争本来无关的剃头匠一步一步走近这位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众所周知的名将其实也是一个“人”。按我们惯常的思维,历史人物都必须被描述为“历史形象”,这在当下大量的影视剧及官方文字中随处可见,而非一个活在当时的“人”,只不过因为那个“当时”离我们有些年头,我们就以为那些都是“形象”,而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所以当被时间书写,揣测,曲解,议论,评定了无数次的张自忠突然作为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一种感动油然而生。而当他死的时候,平淡的意外,侧面的语态,冷静的质感,让切肤之痛变得幽远而难以摆脱。若说遗憾之处,依我偏颇之见,或在于整体的结构上尚需精细打理,主体人物的布局安排或可明确,我们到底是体验剃头匠的心境,抑或剃头匠和其他人只是我们了解张自忠的一个桥梁,通过人物眼睛的观察和作者本身的立足点之间的协调或许也还有考虑空间。
而说到结构,《透明蝎子》倒着实充分展现了形式之美,其结构令人印象深刻。让我脑海里恍惚浮现了《喧哗与躁动》的“错乱文学时间性”,又时不时闪现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式的空间转换。作者从文章一开始就把很多看似不合逻辑的人物关系及对话直接呈现,这“奇怪”的“平淡事实”足以勾起读者的好奇心。随后闪回式的叙述张弛有度,入世出世的语法控制力也很好,令一个单线条单向发展的故事变得立体,同时也令一个暴力冷血的故事有了交相映衬的温情。美中不足或许是说明性文字的存在有的不必,因为我们阅读时毕竟还是期待通过描述的内容来感同身受,这样会比作者直接告诉我它到底是什么显得更有温度。
何荷自然非俄国人,能写一个俄罗斯军队的故事要有必要的自信。而我能感到其对俄国历史、军事的足够了解能给予其自信。文中虽然对“俄国生活”的描述缺少了一些味道,例如俄国人特有的话语表述方式,冬日俄罗斯街边咖啡馆里的气氛,家庭生活里的细节,及街道上独有的魅力(莫斯科的雄壮与躁动,圣彼得堡的文艺与颓废,及文中“故乡”的那种惬意与冷清),但说实话,对于我这样一个在俄国生活了六年的“老炮儿”来说,这个恰恰是不重要的,因为它并不属于“文学性”,无关作品的创作精神。而此文令我的欣喜之处是全新的态度。因历史关系,我们跟俄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俄罗斯从沙俄到苏联甚至到现在都要被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来描述,我们离它虽然很近,虽然发生很多事,但从“人对人”的角度看其实一直遥远而陌生,以至我们对苏联,或者俄国的文字描述中充斥了太多的概念性臆想,造成此苏俄一直是我们幻想的苏俄,而这基调大抵是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形象所积淀下来的,或说这是当时那一代作者基于自身看到俄国的文学影视作品后产生的本土反应。但这篇文章中终于有了一双抛开了政治的人看人的平视视角来关怀人物的眼睛,这让文中人物离我们的距离近了,近到就像邻居家发生的事,只不过这个邻居有着蓝灰色的眼睛而已。
与《透明蝎子》的紧张、惊恐相对应的是《曼陀》,这个作品的文风优雅洒脱,有几分沉思与放松并存的魅力。描述干练,推进速度快,同时又不失细腻精确的雕琢。到位的细节和通过人物眼睛来描述的世界真实感强。个人觉得,若能在故事上再大胆些,再多些“病态美”,把故事推向极端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毕竟这是一篇关于“艺术创作”本身的作品。而艺术创作在受众看来是优雅而高贵的,殊不知对于创作者本身来说却是煎熬与折磨,甚至带有自我毁灭的殉道意味,而其动力的源头或许只是一种“病”。从《霸王别姬》到《黑天鹅》,无论中外,无论年代,其实都道出了艺术创作者的宿命——不疯魔不成活。文中亦有此元素,且还多了几分“鬼魅”。
作者的“大胆”我看最多的体现到了《囚龙》一文中,不仅从一个“私”的切入点讲述公共历史人物,更在对立人物身份中植入了莫名的肉感与暧昧。自然,文中有些方法不敢苟同,例如背景的铺陈虽然周密,但显得过于臃长复杂,太过独立,而有些地方似乎更细化展开会好些。但此文依然是我读过的最“性感”的军事题材小说。
此外,还读到了两篇古希腊题材的作品《掷铁饼者》及《温泉关》。客观说,我个人对此类题材并不偏爱。但除却其主观叙述(甚至是死人的回忆)及文学时间所带来的诗意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仿佛看到了儿时对一个遥远未知世界的幻想,那幻想真实而令人兴奋,让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再害怕。而通过这两篇其实更可以对作者所遥想的内心世界做一番窥探:那世界宏大,自由,却充满诸多灰色的忧愁与斩杀出的红色鲜血,可以说极不完美,但世界本身却能给作者无限乐趣。这一点其实令我羡慕。
我依然惊讶于貌似文弱的优雅躯体里所蕴含的庞大力量,这力量因其胚胎的不同极大的区别于男性的生猛,它既不是一种可以举起重物的力量,也不是一种可以把铁棍折断的力量。这力量带我们从远古的希腊战场飞奔至民国的医院病房,似乎溅到铠甲上的血还没干,就又闻到了解放军战士残破肌肉上流淌的汗味儿。作者是否有着强烈的“古希腊之爱”情结,“训练养成”情结,“善战将领”情结,我想我们无需多问,而文章所体现出的视觉化形态,私人化角度是否足够现代,我们也无需多想。因为首先,这些故事本身就已经为同类型题材增添了重要的一笔颜色。
电影《老哨卡》导演
杜 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