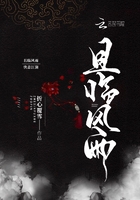初春的西雅图,天空湛蓝清澈,别墅后院的草地已经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蔡光庭坐在那棵银杏树下,抚摸着因换季而更为鲜活的树干,忽然间老泪纵横。
生命是那么脆弱,又是那么坚强。他努力要留下的人终究还是留不住,而曾经下过狠手欲要除去的人,却又在受尽摧折后顽强地留存于世。
命运在他最为得意之时,夺走了他唯一的女儿,却又在他心坚如铁的时候,无情推翻他自认为合理的心狠手辣,更在他暮年之际,让他再次认错、再次妥协。
他开始因为曹劲的那句话而审视自己,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如曹劲口中一般,狠绝地令周遭所有人与幸福失之交臂。
秦文渊拿着薄毯搭在他肩头,口吻如同经年未见的好友:“一晃二十年了,我们眼见着这棵银杏从树苗长得这般粗壮,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渐渐成长。如今,他们都如这树一般挺拔,我们却老了,也该放手了。以前的事已经无法转圜,可我们还能用余下的时间尽量弥补。”
蔡光庭颌首,问道:“连书那孩子怎么样了?”
秦文渊叹了口气:“子弹没有打中要害,生命算是无虞。只是那孩子的断腿总是她心里的结,这结或许只有季家少爷去解了。”
蔡光庭点点头,说道:“当年之事错在我,即便我从未想过取走那孩子的性命和腿,却也真的耽误了那孩子的一生。现在想要弥补,却发现,自己除了钱财,一无所有。”
秦文渊道:“需要我去跟连书解释当年车祸始终吗?”
蔡光庭摇摇头:“不必了,手下的人只是照章学样,或许我的指示本来就说得太含糊,才让他们失了分寸下了重手。结果已经这样了,就算是季礼和连书怨恨我,我也没有资格推脱。与其这样,不如尽快安排纽约的复健师去宁城。还有,把连书的合同销毁,该给的补偿再增加一倍,全数打入她的账户。至于答应季家的合作计划,继续进行,季礼是个好孩子,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秦文渊嗯了一嗯,又问道:“那孟智山那边……”
“这小子还是有些傲骨的,作为孙女婿的条件依旧不够格,但他对经年的感情我也全数看在眼里了。再说,我也欠他一份恩情。蔡家从来不缺大富大贵的继承人,却难得在如此家产面前求得一个真心爱经年的普通男人。”蔡光庭笑了起来,他拍了拍秦文渊,说道:“去把律师先生叫来吧,我的遗嘱需要另外追加一些了。智山那些他自己凭本事拿到手的股份既然转给了经年,那么,就作为他娶经年的礼金吧。还有……若我记得不错,他在国内还有家小公司,是不是?”
秦文渊点头。
“很好。那么拿出我私人账户的五分之一,找个生面孔出面,作为天使投资人身份去投资他的小公司吧。若是这小子能在三年内让这个小公司上市,经年和华兴都交给他,我也就放心了。”
秦文渊惊诧地望着蔡光庭,一时语塞。
蔡光庭却笑了:“总不能让外头的人说我的孙女婿是个空手套白狼的孬种吧。再说,你就不想看看秦珂在孟智山身边这么多年,究竟有没有点实打实的能力吗?”
秦文渊也笑起来:“我并不是担心那两个孩子的能力,而是三年时间太长,只怕是您的曾孙等不了那么久。”
“嗯?”蔡光庭扭头看着秦文渊,十分疑惑。
秦文渊笑容不减,继续说道:“虽然秦珂帮着智山打掩护,但我身为他老子又怎么会被他轻易骗过?蔡小姐怀孕了,智山住了一周医院就急不可耐地买了回美国的机票,这次怕是要直奔别墅找您提亲了。”
蔡光庭狠狠道:“这小子疯了不成?竟然敢让经年未婚先孕!等他回来再打他一顿让他好好长长记性!”
秦文渊憋着笑,问道:“真的打?智山这孩子身体可还没养好呢,不怕蔡小姐挺着肚子护在他跟前?”
半晌,蔡光庭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道:“女子外向啊!我也老了,打不动了!随他们去吧,我这老头子就老老实实等着抱曾孙算喽。”
秦文渊一愣,继而笑出了声。
蔡光庭也笑了起来,他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深深呼吸着带着植物清新香味的空气,犹如脱去了周身枷锁一般,自在无比。
天空飞过几只小鸟,银杏树也应景的抽出几片还不明显的嫩绿,生命以它特有的方式往来反复。
蔡光庭靠坐在银杏树下,和秦文渊云淡风轻的聊着从前,聊着未来。
一片随风而来的蒲公英种子从树上落下,从蔡光庭眼前旋转而下。他心底一软,下意识摊开苍老的手掌接住这不知从何而来的种子,又温柔地将它放到树边的土壤之中。
若是有缘,明年的这个时候,种子就会长成一朵朵蓬松的蒲公英。而他或许能抱着蔡小牧与孟智山的孩子,一起吹动这些毛茸茸的种子,让它们随风而去,落地生根。
想到这里,蔡光庭笑了起来,他起身拍了拍银杏树,缓缓向屋内走去。
风轻轻吹落年华,蔡光庭回头望去,那树下似乎是蔡珩面带笑意的身影,轻轻地向他挥手道别。
是啊,逝去的人早该离去,活着的人永不会重复那并不遥远的悲剧。有了孟智山的呵护,蔡经年一定会幸福下去。
蔡光庭如此坚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