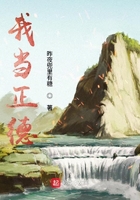“我去帮你拿回属于你的东西。”
远空传来苏紫的声音,心情阴郁的白伢子突然哑然失笑:“又没丢,拿什么拿…”
苏紫的这句话,让白伢子心情好转了不少,便离了海边。
……
白伢子进了一座县城,听闻最近茶楼来了一个说书人,江湖事从他口中说出来如同亲见一般。刚坐下,还没等来说书先生,便听到一些短襟武者或普通百姓在高谈阔论。
“凉州那个新兴的山门入道者亲自授徒,你说我等去了可有机会拜在入道者门下?”
“什么新兴的山门,那可是当世剑尊,从玄天教打出来的绝世强者自立的山门,你要是都能有机会,那葬剑锋不得成为天下第一大教了?”
“要我说呀,玄天教也好,当世剑尊也罢,都理咱普通人太远,这次苏大帅出兵石国才是大事,听说已经三战三捷了。”
“你是普通人我可不是,咱可是正儿八经的修士。”
“屁的修士。”
“凡境二品的修士?哈哈哈。”
白伢子听着这些传闻思量着,当初岳断为什么就罢手了?池秋白设计围剿石国尊者于大夏有益,可岳磊何辜?
“庞先生来了。”有人起身,兴奋的高呼。
或许于这些普通的凡境武者而言,生计比江湖更重要,可又向往江湖,虽不能亲身体会,但听他人说一说江湖事也是好的。
一名手持白纸扇的中年书生来到一张木桌前,轻轻拿起醒木往桌上‘啪’的一声,开口道。
“各位看客且留心,学生今日要讲一件真事儿,还请静静听来。”
有人起哄道:“庞先生哪日所讲不是说真事?”
“哈哈,这回要说的人,想必很多在座的都没听过。”对于看客的起哄庞先生也不恼,笑道。
“无名之辈讲来何用?老子要听剑尊杀出玄天教的故事。”有一粗壮汉子不喜道。
庞先生捻着短须道:“今日所讲的人可不是无名之辈,只是尔等不识罢了,话说六百年前儒门中有一位吕先生,带着坐下两名弟子纵横双剑叛出了儒门。”
“六百年前的事说来作甚?”那粗壮汉子依旧不喜。
庞先生轻笑:“呵呵,这吕先生众位不识,可这两名弟子其中之一可是大大的有名,便是如今龙州山河堂首座项彦直。”
有人又插嘴道:“项尊者的事早听了八百回了。”
庞先生捻开纸扇道:“这项尊者众位是听过的,可今日要说的是项彦直的师兄娄彦恒。”
“哦?既然是项尊者的师兄,那为何名声不显?”
庞先生一拍醒木“啪”,正襟危坐:“这便要从吕先生一脉的传承说起,话说这一脉自儒门诞生之时起便有了,只是规矩古怪,一代人之收两名弟子,一纵一横,以剑相传,当纵横双剑学成之后便会独自闯荡江湖,再次相遇时,既分胜负也决生死,然后由胜出的人再收徒延续传承。”
“项尊者自百年前于龙州斩叛逆名传天下,莫非项尊者是胜者?”又有人插话了。
庞先生好似习惯了,接着说道:“还未分出胜负,因为二人还没到比试的时候,不过今天要说的便是娄彦恒此人,在未分胜负的情况下居然收徒了。”
白伢子暗觉好笑,一个修士收徒而已,还有对那古怪的规矩也是不屑一顾。
只听庞先生接着说道:“收的是谁呢?便是我们上回说的葬剑锋剑尊之子。”
“剑尊的亲儿子需要拜别人为师?胡吹呢吧?”有同样慕名而来的新看客质疑道。
庞先生摇着纸扇:“个中原委还请听我细细道来。这剑尊之子也是旷世之才不弱乃父,于三十七岁便结魁成就大能。”
“三十七岁才结魁也叫旷世之才?”有人不屑的笑道。
“咻…”一粒豌豆突然飞来,崩碎了插话这人身前的茶碗,
白伢子轻撇了一眼,朝庞先生颔首示意继续,那插话的人惊恐的站起身抓过桌上的钱袋便匆匆跑了。
庞先生微笑继续讲着,一众看客或怕无意间惹恼了白伢子离去,另一部分则对庞先生所讲好奇,紧闭口舌,不再接话,静静听着。
随着庞先生将娄彦恒的生平大致讲完,再讲到收徒岳磊之事,白伢子也明白了岳断当日为何没有与池秋白清算。
原来娄彦恒此人,当年也曾心印破碎,后来于南海苦坐三十年,再证心印。当日渊城一战之时,苏玉和项彦直联同作保,请娄彦恒出山教授岳磊,岳断才暂且罢手,没有为难池秋白。
白伢子如今也踏上了心路,深知前路茫然,即便有娄彦恒成功的经历,可岳磊成功的希望依然渺茫。
庞先生讲完,缓步来到白伢子桌前坐下,身躯半躬:“学生此处有一壶好酒,先生可愿与学生共饮?”
白伢子抬起头,怔怔的看了庞先生很久,庞先生也不着急,等着白伢子开口。可白伢子再三打量,也不见庞先生有一丝修为,只觉此人额前明亮,满面春光,分明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
“我很好奇,什么样的普通人才能对娄彦恒这等隐世不出的修士秘闻也能了若指掌?”白伢子终于开口了。
“呵呵,学生不过喜好打听奇闻轶事罢了。”庞先生笑着坐下。
白伢子呲道:“葬剑锋远在数千里外,娄彦恒收徒不过近日才发生的事,连寻常修士都不得而知,庞先生却知之甚详,怕不只是喜好打听而已吧。”
庞先生带着歉意的笑道:“学生对学问一知半解,读书也不甚专心,却偏偏喜好看一些杂书,此前便从一些杂文记事中知晓娄彦恒此人生平,今日来茶馆之时,偶然听到有人提到葬剑锋天骄拜师娄彦恒一事,便拿来做了说辞,混一口饭吃罢了。”
说着,茶楼伙计好似配合庞先生一般,将一串铜钱送了过来,说是今日的说书钱。
“呵呵,让先生见笑了,学生不过为了三餐罢了。”庞先生说道。
白伢子轻抬眉眼:“无故请我喝酒,又是为的哪般?”
庞先生拱手道:“学生见先生方才出手,便斗胆猜测先生不似普通武者,而是那高来高去的修士。”
见白伢子不语,庞先生将一个黄皮酒葫芦放在桌上,又接着说道:“学生自酿的高粱酒,想换先生的过往江湖事。不知可否?”
白伢子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拿起酒葫芦细细端详,自语道:“真像啊。”
曾经在白伢子生命中很重要的那个瘸子也是用这么一个黄皮葫芦装酒,连干瘪的模样都仿佛一样。拔下葫芦塞,往口中倒了一口酒,那劣质酒水泛酸的味道都仿佛一模一样。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前尘往事。
“伢子,你狗日的少拿点,让赵大爷看出酒菜被人动过了可不得了。”
“伢子,你小子今个咋没拿酒回来?”
“伢子,看见老子劈柴的斧子没?”
徐瘸子往昔的景象在白伢子眼前一一浮现而过,不由得脸上露出笑容,好像又回到了过去,隐匿在体内强横的魂元气息也如一汪多年未曾有人淘过的井水,波澜不惊。
庞先生轻摇着纸扇笑道:“睡吧,睡吧,睡着了便没了人世间的疾苦和烦扰。”
“啪。”白伢子的脸贴在木桌上,沉沉睡去。
庞先生一挥袖,茶楼中哪里还有看客和听书的。
白伢子在梦里,梦到了和徐瘸子趁厨娘李婶不注意,往怀里偷揣给赵家大爷准备酒菜。
“你傻呀,鸡屁股就一个,你拿了怕赵大爷不知道是咋的。”徐瘸子一巴掌拍在白伢子的手背上。
此时的白伢子年仅十岁,哪里想的了这么细,不忿道:“他又不吃,每次都倒了,多浪费啊。”
“他不吃是他的事,这块好,这块肉多。”
徐瘸子拿了几块鸡身子肉,然后再摆弄了一番,拉着白伢子偷摸着溜出了厨房。
一晃时光如逝,白伢子年满十五了,在徐瘸子的帮助下,凑够了给白姐儿赎身的钱。
白姐儿接过刘大脑袋手中的卖身契,在白伢子的搀扶下微微颤颤的走出了妓寨,望着外面的天地白姐儿顿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此后的日子里,白姐儿在城东寻了个给人洗衣服的活计,加上白伢子在赵府的例钱,辛辛苦苦一年之后,终于存下了一两银子,找城中做冰保媒的王婆给说了一门婚事。窑姐儿要嫁人,可从来都不是男方下聘的,除了少数被客人赎身带回家的,那也不算下聘,只能算买了回去。
白伢子终于如愿的看着白姐儿出嫁了,嫁了一个穷苦的庄稼汉,庄稼汉见白伢子在赵府做活,每月的例钱还可以,便也没有将白伢子赶出家门。
次年,白姐儿有了身孕,头上包着快青布还忙活在澡堂前。
又一年,白姐儿的孩子出生了,庄稼汉难得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白伢子也告了假,看着新生的婴孩,脸上留下了泪水。
“哥哥…这是啥?”小童长大了,接过白伢子手中递过来的糖块。
白伢子心疼,小童长这么大都没吃过甜的东西。
“好吃,哥哥你也吃。”小童咬掉一块,将另一半沾着口水的糖块递给白伢子。
白伢子也不嫌弃,张嘴含住了小童手上的糖块。
“哥哥,二毛子打我。呜呜呜….”
已经长到白伢子胸口高的少年哭着鼻子回来了,白伢子抄起锄头就出了门。
……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白伢子躺在土炕上,弟媳和弟弟围在一旁,还有几个小辈眼中含着泪水。
“大爷爷…”
白伢子含笑的点了点头,眼皮变的沉重,身躯已经干涸无力,但仍然极力的扭过头,看向窗外院落中的石刻墓碑,那是白姐儿和庄稼汉的坟。
白伢子这一生未娶,年轻的时候替这个弟弟攒够了娶亲的银钱,又在白姐儿故去的时候,白伢子又将白姐儿存下来给他娶亲的钱拿去置了这块石刻的墓碑,后来渐渐的年岁大了,弟弟也有了子嗣,便没了娶亲的念头。
“我这一生,无声无息的来,无声无息的走。”
白伢子笑着闭上了眼睛,身子保持着扭动的姿势,脸依然对着白姐儿的墓碑。
酒馆中
庞先生背负着双手,看向窗外,悠悠然道:“这梦中红尘,可如你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