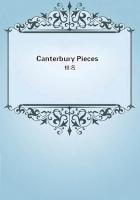“毕竟是年少,于晟清的感情上难免意气用事,只能事叹一句年少无知,也是不能全赖上他了!”叶芷薪应着陆母的话,嘴角一抹笑意淡到隐约难辨了。
“当初应了冉长允的婚约是有些同阿清赌气的意气在里头,后来在外头设计阿清可就不是了!”陆母说着,话里头有一抹辨不清的冷意在里头,“我是这两天托了人才问到的,也难怪阿清三年前不愿意为着木木同她屈就,如今更是不愿意了!”
能是托了谁才问到这些子私隐的事了,怕只有当事人能清楚吧,不过若是傅潋芸做下的局,那她自是不会同陆母说白了的,可陆晟清应该也是不会同陆母细说起这些的了,陆母能是托了谁才问得到呢?
“伯母,潋芸无论是做下如何的算计,她只是心里头想着晟清而已,为着心头所念即便是花些小心思,也是情有所原了!”叶芷薪淡淡地应着,心底里她是想知道些陆晟清同傅潋芸的过往,可又怕是知道了反而徒增难堪和牵念,是以话语才是淡了,想将话题隐过去。
哪知陆母是存了念要让叶芷薪知道,未随着叶芷薪一句场面话转了话题,“我是不了解你们年轻人对情缘之事如何看了,只是想着即便是心之所念,也该有个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度吧,可是不能仗着喜欢的名头,就为所欲为,全然不顾及对方的意愿了!”
“潋芸同晟清打小就是一块儿的,那么些年的情意是外人所不能比拟的,再是如何胡闹,也是不会惘顾晟清的意愿的吧!”叶芷薪到底是经不住心底的好奇,起了些探究的意思了。
陆母淡淡地笑开了,嘴角一抹苦涩的无奈,“这孩子我是越大越瞧不明白了,瞧着是个温婉端庄的,怎是有时候做事却是狠辣不羁了。大概四年前阿清出去谈生意,去了希檠他们那个城市,想是念着旧友,就去寻着他们聚聚,潋芸知晓了阿清留了你在身边,她同阿清闹,还明里暗里算计着希檠和长允陪着她闹,希檠同长允本是念着亏欠她一分,自然是纵着她了!”陆母说着又是一声叹息。
“我是知晓些的,那个时候他们在外头遇着,念及往日,一时情念又起,才是情不自禁,做下了那等错处!”叶芷薪轻声说着,“其实那个时候若是将错就错,晟清同我说开,我们早些分了,又哪里来如今这些纠缠,只是那样的话就没了同木木这么些年岁的相处了!”说着叶芷薪又是不舍得轻轻抚着木木的脸蛋。
“你这一番话也是未将阿清的心思算在里头了,他们虽是长在一块儿,可阿清对潋芸到底不是那方面的心思,他是只对着长允起过些亲近之意,后来他也是想明白了,只是长允性子活络,心思单纯,阿清瞧着是同别个朋友有些不一样,才起了异样的亲近,并不是恋慕同性的感情了!”陆母说着,轻叹了口气。
“潋芸那个时候就是怂恿着长允给阿清使了绊子,在给阿清的酒里头动了手脚,她本是想着如此一来,阿清又是看在往日的情份上,定会离开你,选了她,哪里知道阿清事后只恼着潋芸的一番算计,半点旧情也未提及,潋芸那个时候心性自负又傲气着,也未同阿清磨着,更是未在你跟前搬弄是非,还想着是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哪里知道却是有了木木了啊!”陆母说着抬眸瞧着床上的木木,眉眼里头一丝温婉的慈爱之意。
“潋芸就未在木木出世之前同晟清提木木的事吗?”叶芷薪低声问着,心头也是一阵好奇,木木抱回来之前,陆晟清可是未在她面前提及分毫,甚至是清冷疏离的神态都是如了往常一贯,她也未瞧出任何先兆了。
陆母轻轻摇了摇头,“阿清未同我细说,不过依着我想,潋芸定是同阿清提过的,只是阿清恼着潋芸一番算计,言语上自是不会同潋芸软着来了,再说那个时候你在阿清身边,他也顾着你的!”
叶芷薪倒是未觉出那么早以前陆晟清行为处事就会顾念自己了,那个时候他可是对着自己依旧态度冷淡疏离着呢,同他处着,自己也得小心谨慎,时时估摸着他的心思了,“潋芸竟是未同晟清好好商量着就将木木生下来了吗,她家里头也未来同你们提及这些,就算是瞒着长辈,可潋芸的大哥同冉长允该是知晓的吧!”
“唉,他们自然是知道的,潋芸的母亲性格强硬着呢,逼着潋芸不让她将孩子生下来,哪里会来同我们说这事,潋芸呢性子也犟,非要将木木留下,同她母亲闹开了,就寻了处地方安静地养着!”陆母眉眼里头无奈的神色重了些,“潋芸呀是瞧着温婉端庄,可这性子却是随了她母亲几分了,那段时间我想着潋芸这孩子定然是不好过的,也是怜惜她,所以现下能纵着她的地方,我就不苛责了,薪薪,也望你能体谅我了啊!”
“潋芸那个时候怎就未找上你同伯父替她做主了,她毕竟怀着的是晟清的骨血啊!”叶芷薪问着,眼眸里头一片平静中携着丝悲悯的同情之意。
“她呀是性子里头有些矛盾之处了,当初一门心思算计阿清不过是为着同阿清在一块儿,手头有了胁迫的筹码了吧,她倒是念起阿清的心思不在她那儿了,又没了同阿清纠缠的勇气了!”
“她哥哥同冉长允就没想着替她出面同晟清商议吗?”叶芷薪既是存了心思深究,如今陆母在跟前说开了,那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个明白吧,往后虽是没机会再遇着,但到底是梗在自个儿心头多年的事了!
“阿清没提过,我也问过阿清,他是不怎么愿意提当年的事了!”陆母说着,“我是想着既是过去的事,阿清不愿提及我也不能生将这些往事掀起来了!”
“嗯!”叶芷薪轻轻点了点头,“那伯母你同伯父是何时才知晓木木的?”
“唉,我同你伯父退下来后就不大理事,阿清呢是忙着公司里头的事,饮食起居又有你帮忙操持,我就闲下心思陪着你伯父了,对阿清的是甚少过问,潋芸那头未同我们通消息,阿清又闷在心头不说破,我们哪里能知道这些了,那个时候还想着将你同阿清早些完婚,我同你伯父也好早些得个乖巧的孙儿在一旁!”陆母说着,“我们也是在木木生下来后才知道的。”
“木木才是生下没多久了,潋芸怎是舍得把孩子给你们抱回国了?”
陆母眼眸里一丝复杂之意流过,“潋芸那个时候为着生木木本就是憋着股委屈,孩子生下来才同阿清提,哪知阿清却是恼潋芸擅做主张,再见着潋芸对她一句温言软语都没有,却是对木木舍不下!”
“也是了,生下孩子本就没得着家里头长辈的半分怜惜与理解,还要见嫌于晟清,自然是心里头的委屈更重了吧!”叶芷薪淡淡地说着,眼眸掠过陆母,瞧着屋里头一处角落,眼神却是有些散开,眸子里头没了焦距,思绪是琢磨着傅潋芸的委屈去了。
陆母淡淡地笑开了,“你这孩子心善,到如今地步了,你竟还能体谅潋芸一番苦楚,只是这心里头的苦楚啊,是得别人主动触碰才可得一分怜惜,若是硬将苦楚摊开在别人跟前,逼着人怜惜上一分,反倒是惹了厌烦了,潋芸那个时候就是揣着心头慢慢的委屈,又同阿清犟着,阿清虽是心疼孩子,可对潋芸是真真无半丝容忍的耐心了!”
叶芷薪淡淡地点了点头,“是这个理,只是潋芸怎会不明白这些了,若是真想同晟清处着,即便是有木木这个筹码,也是该服个软啊,毕竟是她有错在先了!”
陆母听着脸上神色有一瞬讶异,而后又融了丝暗淡的无奈之气,“薪薪,你对阿清一番心意是都过去了吗?也罢,也该让阿清受些教训,往后才能觉出情意难求,在男女之情上也就能开个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