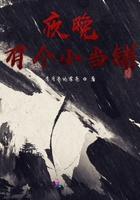临行前我打算追忆过去,以此为出发前的仪式,也能让日后在路上时,不会觉得一切开始得莫名其妙,就跟我的人生为何如此这般一样无凭无据。
要说天生兴趣,除了食色性也,也就写作时自己的记录表达欲了。
努力追溯下记忆,模糊想起这欲望的萌芽期大概在三四年级。
那时候还没学会阅读,也不存在出于模仿崇拜什么而写,单纯就觉得在当时所有只能填横线填空格的作业里,写作文是最自由开心的事。
或许其它作业空洞无趣没意思,但只要其中布置了一篇作文,那我就有动力用光的速度做完作业去写作文。
这也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后——初高中时候作文相比其它科作业对我要更显得沉重。
小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光觉得校园生活已经够无聊的了,课堂时间有老师控制,课余时间有老师布置的作业控制,唯有作文是我可以自由发挥的地方。
那时候大概是一周布置一篇作文,其他同学每次周五语文老师宣布布置作文时候都会全班起哄叫苦连天,我就恨不得每天布置一篇,要是能把其它作业去掉多布置几篇我也愿意,而其他同学铁定难受得要命,我就舒服得不行,此消彼长之下,我在班级里的名次就上去了。
每次布置作文就等于憋一周的欲望得到解放,好像那时候姑妈家里被关了一天在吃饭前打开铁笼一溜烟撒欢跑向狗盆的那只老狗,我觉得我的心情和它是一样的。
憋太久的欲望释放过后自然都会瘫软无力,有过几次写完作文就不想写剩余作业,而到周一时因此被请家长,而后又经历被家长“请”回家的经历以后,我只好不得不再次推迟释放的时间,规定自己作文要在完成所有作业以后才能写。
当时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痛不欲生,总是痛恨自己太过于懂事聪明,那么为老师家长着想,生怕他们因为打骂自己而感到疲劳。
权衡利弊之下作出了决定,所以我在作业出现在我生命中之初便解决了自己拖欠作业的情况——在我还未对写作文失去兴趣以前。
在兴趣当中最欣喜的便是老师最初布置作文的几次中,没有任何要求,字数不限,题材不限,诗歌随意。总之只要别在作文本上画鬼脸,写什么都行。而我一开始写的是一首诗,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啊
天上飘着一朵一朵的屁
地上蹲着一个一个的人
地上一个一个的人放屁
飘到天上变成一朵一朵云
天上一朵一朵的云下雨
被地上一个一个的人喝掉
酝酿成了屁
又一朵一朵飘到天上
变化成了云
题目叫《人云屁云》。
本来第六句就结束了,但后来无意间在一本书上看到“酝酿”二字,觉得这词深奥且难写无比,为了给老师一个惊讶,让她知道我懂如此生僻的词语,才特地又酝酿许久编出末尾三句给“酝酿”生搬硬凑进去。
写罢后一读,惊讶地发现这诗竟有一种翻来覆去,可以无穷尽编下去的势头。
这一发现愈发使我坚定必须要给语文老师看的势头,在我的料想之中,这篇诗歌若是上交,必然是惊艳之作,万万不可让其胎死腹中。
秉着这一理念,我满心欢喜,迫不及待要上交作业,半路却杀出个姑妈说要检查作业,我亦满心欢喜,迫不及待地交给她检阅,等待着被夸赞称惊艳。
不料却被严厉批评一通,然后要求此篇作废再写一篇。
原因有两个,一是内容太过粗俗,小孩子不该满脑子这些东西,二是作文不能写诗歌。
我说,语文老师说诗歌不限制。
姑妈说,不限制也不能写。
我说,为什么。
姑妈说,因为我要求你写五百字。
我说,那我就继续写,写够五百字,这诗我能一直写下去。
姑妈说,也不可以。
我说,为什么。
姑妈说,诗歌不能写五百字。
然后我就想不通了。
后来我当着姑妈的面重新写了篇五百字的,然后背地里又偷偷把之前被没收的那篇诗歌默写出来,周一满心欢喜,迫不及待上交语文老师。
第三节课后,我出现在语文老师办公室里,旁边还站着同在学校教书的姑妈。
这次我无心争辩,听完两人的教导后,我拿着那本作文本走出办公室,把它撕碎后扔进学校厕所的化粪池里。
从这间事里,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是有边缘存在的,而划分边缘的往往是年龄。
不是因为年幼者有多愚笨,这事关乎于年长者有多少自认聪明的成分。
当作文纸还未被厕所里的蛆爬满时,我就先它一步接受了这个世界的划分。
第二次,我便把和同学一起在橡树林里用橡树叶互相追逐打闹在作文里写成一场武林高手比武大会,把当时所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专业名词“轻功水上漂”,写成一种所有人都会的武林秘籍,并且我以这种秘籍打败了所有人,最后所有人都对我抱拳大呼大侠好身手。
不出所料,这篇作文被语文老师也就是当时的班主任亲口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诵了一遍。
尽管平日里班主任对我特别严厉,就因为上课我跟女同桌说几句话把她逗笑,班主任下课就到办公室给姑妈告状,让我挨了顿骂。
并且从那天后,我成为我们班里第一也是唯一一个人坐一张桌子的同学。
在我九年义务受教育的经历中,这种情况断断续续持续到高中毕业。
另外,那是我从上一个学校转过去读二年级的第一天,我和我的那位女同桌只坐了一节语文课,我还来不及问她的名字。
换座位后,当天晚上我就梦到新座位上坐我前面的另一个女同学。
尽管这样,当她在全班同学面前读完我的作文后,我觉得她是一位有品味的老师,作为同样有品味的我,自然就不计较之前的种种。
有个性的人值得被原谅。
这是我在就读过的第二所小学里遇到的人生里第一位真正赞扬我作文的教师,此后在转学前的日子里,每次写作文她都会给我程度不一的表扬。
唯一提过一次要求,那次我赶着去姑妈玩具店里玩四驱车草草结了一个自以为新颖的尾,她在讲台上读完作文对我说,你还没写完,怎么就结尾了呢?继续写吧,我们还想听,希望下次你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故事。
她的名字我却是已经忘却了,或许便从未记得过。只知道她住在镇里,每天由她丈夫骑摩托送到学校里来。有次她摔断了腿,也是被她丈夫背到教室里。我们看着她腿上白白的膏药和被雨水淋湿正往地上滴水的头发,全都停止了晨读,她打发走她丈夫后对我们说,我没事,继续读。
我好似记起来了,她姓赵,因为姑妈只告诉了我她的姓,而我先前总是将其与她一身黑的服饰联系在一起仇恨她,那个下雨的早晨她便是穿着这一身衣服。
不论我记得对与否,这位让我继续写,继续读的教师,已被冠予语文老师的称号储存于我的记忆之中。在那之后,我所遇到的众多班主任老师都曾赐予过我作文的表扬以及一人一桌的坐位,而她,都是第一个。
这是我接受社会的开始。
四年级升五年级的时候,我由老家,也就是父亲那边,去到了母亲那边。父亲把我交到母亲手里时,我好奇地看了半天,原来她已经长这个样了。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完全就是两个地方,无知的我甚至根本比较不出两者的区别。
唯一隐约觉得我大概是从乡下去到了城里。
原本我无知得连区别都不会发现,只觉得坐了一趟车,下车以后见到的东西和原来那个地方有些不一样。
直到去新学校入学考试的时候发现试卷上的题目从来没有见过,连作文题目都读不懂。
竟然还有一题让我写出两句带桃花的诗,我想得差点吞铅笔自尽,最后只好瞎编两句带桃花,字数相同的句子填进去,好像是“春天桃花开,冬天桃花关”之类的。
奇异的是,后来试卷发下来,那两句上面竟然打着两个大钩,一分未扣。
不由感慨如此荒唐都能对,真不知道那些不算很荒唐的错误是如何评判的。
老天马上满足我的猜测,翻到后面作文里我不小心把“地”写成“的”,竟被画个大圈,并在旁边扣了五分。
那时候我才发觉,我已经离原来那个地方很远了。
后来我还是成功入学,遇到了第二位语文老师,她姓苏,也是一位女老师,她还曾安慰过我,告诉我刚来几天上课听不懂没关系,好在我基础好,不用着急。
这是入学第一天我第一次见到她后听她说的第一句话。
不知她是从“春日桃花开,冬天桃花关”里看出我的基础,还是对每个新同学都这么说,总之在这样的批改制度里,我实在不敢妄称基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