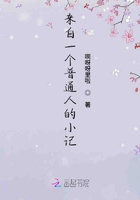虽然离开了大宅门,搬到了简陋的小院,但生活中充满了亲情,日子变得更快乐。让我父亲最高兴的事就是表姐刘惠华的到来,表姐总是像股新鲜空气似的使小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我奶奶的姐姐杨木槿和姐夫刘德绪倒很少过来,据惠华讲她父母和哥哥每天都在外头忙,除了救济难民还办了两家孤儿学校,为此已经又卖了两所房子。
惠华说:“军阀横行,我父母行善。政府里有人在卖国。我父亲卖房子救国。说实话,太讽刺了。”
我奶奶表示:“惠华,你父母都是佛门大居士,你应当学他们也信佛吧。”
惠华笑笑:“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最让我奶奶意外的事不是当时惠华没跟着父母信佛,而是有一天她竟然带了一个男同学来到新街口北大街这个小院。也是这个年的初春,柳树刚刚发芽的时候,还是个礼拜日,我奶奶和我父亲那天都在家。当时,我奶奶在院子西头的小厨房里洗菜,我父亲坐在自己屋里做作业,他隔窗抬眼便看见院门开了,接着就瞧见表姐那小蓝袄、黑色学生裙的熟悉身影。
我父亲欢快地叫了声“惠华表姐”马上飞快地穿过堂屋去迎接她,可来到屋门时却猛然地停住了脚。他看见一个人随惠华进了院门,而且是个男青年。他二十左右,留短发,穿深灰色长衫,脖子上围一条特别醒目的红色毛线围巾。
惠华看见表弟发愣,先嬉笑着问:“安表弟,不欢迎啊?也不叫人儿?”
我父亲叫声:“表姐。”
目光却把疑问投向了那个男青年。
同时,我奶奶已闻声从小厨房出来,热情地:“惠华来啦。这位是--”
惠华介绍:“他叫张中华。安表弟,叫张大哥吧。”
我父亲礼貌地:“张大哥好。”
惠华一指我奶奶,对张中华说:“你,快叫二姨呀!”
张中华大声地:“二姨!给您老请安。”
我奶奶笑了,夸了一句:“真懂礼儿啊!在旗的吧?”
张中华便答:“是。我老家在吉林那边。”
我奶奶便客气地:“那算一家子啦。哎,快进屋,别站院里呀。安儿,给你张大哥泡茶!”
惠华说:“还是我来吧。”
我奶奶新家的正屋也并不大,摆了张方桌,四个方凳,平常就是饭桌,来人也在这儿待客。左边那间是我奶奶住,右边就是我父亲的卧室兼书房了。正屋虽然小,靠右壁放着小平柜、茶具等杂物,而挨着我奶奶住房那边则是供着观音菩萨的佛台了。
进屋后,我奶奶招呼客人坐在方桌旁,惠华忙着在平柜前沏茶倒水,我父亲就凑到表姐耳边小声问了一句:“你们怎么认识的?是同学吧?”
惠华却故意大声回答:“我可不配跟他同学。人家张中华是谁呀?北大的!知道吧,北京大学。”
这让张中华有点不好意思,又站起来:“惠华,我一旁听的穷学生有什么显摆的?”
惠华端着茶杯走过来,放在张中华面前:“大少爷,请喝茶。”
张中华就朝我奶奶解释:“二姨,您瞧,她老是这么挖苦我。”
我奶奶咯咯笑着,指着他俩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哪,真不像我们当年哟!”
惠华却撅着嘴,故作生气状:“哼,二姨,您当我是夸他哪?才不是呢!人家张大少爷,小小年纪在吉林老家都定下媳妇儿啦!还带着我们反封建呢,今儿个在二姨家我可得揭你老底啦!”
张中华顿时脸都红了,忙辩解:“不是那么回事儿!二姨,那不作数。我是逃婚才到北京上学的,惠华编派我!”
惠华转脸问我父亲:“安表弟,你信吗?替我审审他!”
在表姐鼓励下,我父亲就开心地:“小小子儿,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张大哥,对吗?”
张中华笑了:“对对对!这成了吧?可我知道媳妇儿是谁呀?”
我父亲一指她表姐:“刘惠华呀!”
惠华伸手轻轻打了一下表弟:“你人来疯啦?”
我奶奶被逗得开心地大笑:“哈哈哈!惠华呀,他张大哥第一次到咱家,你可有点儿不像话喽!”
惠华仍不依不饶地数落道:“二姨,您可不知道,人家张中华在我们同学里头搞宣传,什么德先生、赛先生的一套一套的,可他那家呀封建透顶!”
张中华反问:“那怨我呀?我是彻底革命派。”
我奶奶听糊涂了,便问:“德先生?还有赛先生,都是你们老师?”
我父亲抢先回答:“妈,别出笑话了。那是英文,民主和科学的意思。”
我奶奶站起身,想往外走时说:“得了,你们年轻人聊吧。他张大哥,今儿别走哇,二姨给你们做饭去。”
没想到张中华伸手一挡,说:“二姨,今天您歇着,我来做饭。”
转身翻开他带的书包,“您瞧,这是惠华让买的五花肉,我做个红烧肉给您尝尝吧。”
我奶奶有点不相信:“大小伙子的,会做饭?”
惠华嬉笑着说:“让他露一手嘛!二姨,他做的呀不比同和居的差!”
我奶奶瞧瞧惠华,又看一下张中华,这才说:“你们俩呀,在涮二姨我吧?”
惠华说:“哪儿敢呢?走,中华,做饭去!”
两人出正屋就往小厨房走。我父亲就说:“我也去。”
我奶奶拉住他说:“回来。没你事儿,回屋写功课去吧。”
这次愉快的团聚后,有一个多月时间再没见刘惠华和张中华的面。我父亲准备要考中学了,而且决心报考辅仁,所以功课挺紧也没多说什么。
倒是有一天晚上我奶奶提到惠华时,对我父亲说:“我看,惠华和你张大哥那孩子还挺般配,我是不是应该跟你大姨提一下这个事呢?”
我父亲马上反对:“妈,您很少看书看报可能不知道,那北京大学提倡的就是思想自由哇。惠华表姐和张大哥应该是自由派,一定反对父母干涉他们的事。
您还是别管了,成吗?”
我奶奶倍感欣慰地说:“安儿,你真是长大了。”
在晚清实施的所谓“新政”中,有一项是成功的,并且影响深远,那就是废除了“科举制度”。至民国初年,中国高等教育处于高速发展期,大批爱国学人投身于教育事业,更使高等学府成为中国进步新思潮的领军之地。特别是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引进了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一大批有影响有学识而且思想激进的文人学者到北大任教,这就使北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思想与精神的中心。我父亲的表姐刘惠华没有读北大,可她与北大有较密切的联系,因为与她在学生运动中相识,而后又相处关系最好的那位名叫张中华的男同学(姑且用现代语叫男朋友吧)就读于北大。她读到的每一本《新青年》,都是男朋友传给她的。
就在那年四月底,惠华拿着一本最新出版的《新青年》,跑到姨妈家找到小表弟就说:“安表弟,列强的凶残、中华的未来,写的非常清楚。你也看看吧,咱们不能总待在书斋里呀!”
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岁,最信赖大表姐,捧着杂志就跑到里屋读起来,表姐就和我奶奶聊家常话儿。
只隔了十多分钟,我父亲就重又跑出来,指着那本杂志问表姐:“这里边说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到底是什么内容?那个胶济铁路对咱们中国特别重要吗?”
刘惠华一拍手,笑着说:“安表弟你真棒!不用我说,你已经找到重点了。这叫国耻,懂吗?”
我奶奶接过书,翻了两下递给刘惠华,郑重地嘱咐道:“惠华,这类书哇以后别给安儿看了,他还小呢。”刘惠华笑着回道:“二姨,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啊!我还有事儿,我走啦!”说罢,她嘴里哼着什么新调儿,跳跳蹦蹦地离开了那个小院。
这年五月初的某日,北京街头还飘扬着柳絮,卖早杏儿的刚乘鲜上市时,我奶奶正看着我父亲在南屋背书,就听得小院外大街上传来一片人群吼声,响动越来越大,以致声震长空。这是前所未有的异相,我奶奶有些诧异,就带着我父亲走出了小院门儿,来到了新街口。
娘儿俩只见从西直门内大街由西往东走来了一长串学生模样的队伍,大批年轻人都是满脸的激愤,成百上千的市民跟着学生们怒吼: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抵制日货,反对卖国!”
“宁为玉碎,勿为瓦全!”
在一片吼声中,整条大街都沸腾了,路边小贩不单是跟着喊,有的人还给学生们送烧饼送油条呢。我父亲站在路旁,不断高举起小拳头,激动地跟着游行学生队伍呼喊口号。
我奶奶抚着我父亲的肩膀呆呆地看着,半晌才喃喃地自语:“咱们这个国家呀,要变了,也应当变变啦。”
这一天,是1919年5月4日。
当日傍晚时分,表姐刘惠华和她的男朋友张中华突然来到了我奶奶家小院,说是太累了,歇口气儿喝水。
表姐进屋还没坐定,就兴奋地说:“二姨,中国人终于觉醒了!今天学生们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看谁还敢卖国?”
我奶奶关切地问:“那些大兵没打你们没抓你们?”
表姐那位男朋友张中华回答:“中国军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卖国求荣的败类是少数。我就在天安门,我亲耳听见步兵统领李长泰说了,你们学生有爱国心,难道我们不爱国?我们就愿意把中国的地方让给别人?”
我奶奶忙问:“这位步兵统领是旗人吗?”
表姐大笑:“二姨,都什么年代啦。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看谁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公元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学生运动很快波及全国,至6月初全国各大城市全都宣布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6月11日总统徐世昌请辞未准,迫于全国压力于6月23日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从缓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6月28日是与会各国正式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当年秋季,我父亲就读辅仁中学。
开学那天,我奶奶送他来到学校门口,只说了一句话:“安儿,读好书就是你一辈子的前程。”
十一、
秋天到了,我奶奶家租住的新街口北大街那个小院里洒满落叶,院里的一棵槐树和一棵枣树很快将是一树枯枝了。这天傍晚,饭后我奶奶正在小厨房里洗碗,我父亲坐在灯下看书,忽然小院门被人“通通通”地敲响了。
我奶奶从厨房走到院门口,问一声:“谁呀?”外头是刘惠华焦急的声音:“二姨,快开门!”
我奶奶刚拉开门栓,惠华和她的朋友张中华便急着推门进院,并且马上回身看看才关门上栓。惠华神色有些紧张地问:“家里没别人吧?”
我父亲闻声早已站在堂屋门口应道:“有。有我呀!”
张中华叫了声:“安表弟。”
往日特别喜欢表弟的惠华竟然没搭理他,拉着张中华就往屋里走:“快进屋!别在院里说了。”
都进了堂屋,我奶奶就问:“怎么啦?惠华。”
我父亲也开玩笑地说:“表姐,看你这样儿,像是遇见劫道的了。”
要是在往日,惠华肯定跟表弟不依不饶地斗嘴,可是今天她可跟没听见一样,径直冲我奶奶说:“二姨,让中华在你们家住两天,成吧?”
张中华也跟着说:“麻烦二姨了。”
我奶奶这才感到事不一般,接着问:“出什么事儿了吧?”
我父亲却挺高兴:“没事儿,让张大哥跟我住呗。”
张中华却惭愧地道:“唉,都怪我呀。”
惠华气恼地:“怪你什么?怪你那反动封建家庭!”
我奶奶弄不清此中缘由,便说:“惠华你别跟人家急,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说说。来,他张大哥,坐下坐下。”
几个人围着方桌坐下来时,惠华仍带火气地说:“你们家也是邪了门儿啊!逼婚能派当兵的来北京抓人?干脆把你那定亲的媳妇送北京来不就得了嘛。”
我奶奶又劝道:“惠华,别这么说话!”
我父亲也说:“表姐,人家张大哥的心里想着谁,你不明白呀?”
张中华低头不语,只是叹气。惠华忍不住了,便对我奶奶说出了事由:“二姨,他吉林老家有个什么堂叔,在东北军里当点儿官。而他爸又是老家张家屯子的族长,奉系军阀又是张作霖,就这么着好像拉上关系了。他在老家定过亲,可那是封建包办,是不能作数的。您想得出来么?他那堂叔奉他爸的指示,今天到北京抓人来了,还说张中华是叛逆,非带回老家不可!”
我父亲听了也气愤地说:“这光天化日之下,也太霸道了!”
我奶奶就问:“那学校不管管?”
惠华回答:“现在的东北军,段祺瑞都得让他们三分。再说中华他和同学住在学校外面,他堂叔带的兵不单知道他住哪儿,连他在北大听课教室都找到了。”我父亲便问张中华:“张大哥,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一直没吭气的张中华这时才抬起头,沮丧地回答:“今天正好没课,惠华送我回宿舍,一眼瞧见门口站着两当兵的,我们就赶紧躲了。后来是溜出来的同学告诉我,是我堂叔带人来抓我了。”
惠华气愤地:“你生在个什么家庭?还不如我爸妈信佛呢。”
我奶奶马上问:“惠华,告诉你爸妈了么?”
惠华顿时有些气馁:“我,我敢么?他们要是见了中华,以为我……”
我父亲马上接着说:“私定终身。”
我奶奶制止:“别闹了。他张大哥,我一直没敢问,你老家那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张中华深喘口气:“我也不怕丢人了。二姨,我跟您说说吧。”
惠华也催促:“你彻底说吧,连我都不知道你是逃婚到北京的。逃什么婚呢?”
张中华面色凝重,讲述的第一句是:“我只想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现在我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民主和自由了。在我心里头我的父母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我们家有一点特殊吧。在吉林张家屯子,我们算旗人里的望族,算是家族掌门的一系……”
刘惠华,我奶奶和我父亲眼前是一段发生在遥远东北农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