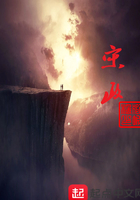将作监,案牍坊。
最后一个被约谈问话的工匠已经起身离去,坊丞游景云扭头对郭虔瓘说:“郭队正,案牍坊所有的官吏和工匠都询问完了,您看有什么需要卑职配合的?”
别看郭虔瓘只是一个翊府队正,可也有正七品上的官阶,比游景云这个正八品下的坊丞大好几级呢,尽管文官一向看不起武官,但官阶品级摆在这里,大唐又不比宋明清几朝重文轻武,游景云还不得不在郭虔瓘面前低声下气。
整个案牍坊有大小官吏十三人,另外还有工匠一百五十多人,郭虔瓘用了一天一夜才全部询问完毕,这中间除了如厕和进食饮水,根本就没有休息过。
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查出在这案牍坊内到底是谁把空白过所私自带走并卖给了吐蕃细作。
郭虔瓘思索一下,问道:“游坊丞,这案牍坊之内,如果有谁私自把空白过所带出去,如何能查出来?”
游景云笑道:“郭坊正,您来之时也看到了,大门处守卫林立,官吏及工匠进出都要被搜身,没有人能私自把空白过所和其他相关案牍带出去,包括卑职在内都要接受检查!”
郭虔瓘点了点头,起身道:“行,郭某没有其他问题了,游坊丞去忙自己的事吧,郭某在坊内随便走走,不会打扰你们坊的正常生产!”
“那······卑职的确还有事情要办,就不陪郭队正了!”
郭虔瓘走出游景云的办公房,他带着几个兵士来到了生产制作案牍的作坊随意参观。
过所也是案牍的一种,大唐朝廷各个官衙以及全境所有州县官署所用的案牍都是从这座案牍坊生产并运送出去的,但这座官办案牍坊并不生产制作案牍所需要的纸张、包装。
制作其他用来书写公文的案牍的纸张并不困难,把这些纸张装订制作成案牍也不复杂,可以说比较简单,但制作过所却又不同,毕竟一张小小的过所承载的是一个人的身份信息,容不得马虎。
因此,制作过所的纸张是官办造纸坊采用特殊工艺专门制作而成,当这类纸张运到案牍坊之后,这案牍坊的工匠们在官吏的指导之下用特殊的药水浸泡、晾干、再进行裁剪、装订,最后在关键位置印制图案和文字,生产制造出来的空白过所有几道可以进行防伪的隐藏标记,不熟悉这些生产制作工艺流程的人绝对伪造不出来,就算熟悉这些工艺流程,也没有纸张的生产配方,造出来的纸张很容易就露馅。
在另一边,坊丞叫来一个书吏暗中吩咐:“你去盯着郭虔瓘一伙人,看看他们都在作甚、说甚么,别让他们把咱们制造案牍的生产工序偷学了出去!”
“卑职明白!”书吏领命而去。
这书吏刚到生产作坊就看见郭虔瓘正拉着一个工匠询问,他连忙悄悄走过去躲在一根木柱后偷听。
郭虔瓘问这工匠:“你觉得这案牍坊内有没有人可以案牍私自带出去?”
“不会吧?私自把案牍带出去,特别是过所这东西,一旦被查出来可是重罪啊!再说进出都要进行搜身,谁有本事带出去?不过······”
“不过什么?”
这工匠犹豫了一下才说:“不少时候,坊正出去是没有经过搜身的,他是坊正,那些守卫都是他的人,都听他的,谁吃饱了撑的敢去搜他的身?如果不是他自己要求,守卫们还真没有谁去自讨没趣!”
“哦?”郭虔瓘一愣,他这时才意识到游景云从始至终都表现得太过热情和配合了,让他从头到尾都情不自禁的没有怀疑到此人身上。
他这时把这一天一夜的经过仔细回忆了一遍,这个游景云的确有些不太正常。
躲在木柱后的书吏听完立即退走,很快回到游景云的办公房向他禀报方才所见所闻。
游景云心中有些慌乱、忐忑,他知道郭虔瓘很可能已经开始怀疑他,但他也不是很害怕,毕竟捉贼要拿脏,没有证据肯定不能给一个官员定罪。
其实游景云也很后悔私自把空白过所带出去卖给特定的人群,但架不住这玩意在黑市上有价无市,而且一年比一年的价钱高,一张空白过所在黑市上可以卖出三十贯的天价。
其实游景云并不是很缺钱,他孤家寡人一个,父母早逝,妻儿也在一场瘟疫之中全部死去,如今已过去六年,他也一直没有再娶妻,但谁会嫌钱多?而且当钱多到一定的程度时可以吞噬很多人的意志和灵魂,游景云显然也不是极有原则的人。
游景云打发走书吏,正打算回家休息,他已经被郭虔瓘这活人折腾了一天一夜没睡了,趁着今天不用去见上司,坊内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生产任务,他打算回去好好睡一觉。
这时郭虔瓘走了进来,“游坊正,郭某是来跟你告辞的,此间调查已经告一段落,郭某要回去向上官复命,不过此案还没有结案,可能后续还有一些事情需要麻烦游坊正的!”
游景云笑道:“好说、好说,郭队正随时来,卑职随时接待,有任何需要配合的,郭队正只管吩咐,正巧卑职也要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哦?游坊正家住何处啊?要不要郭某送你一程?”
游景云连忙拱手:“不必、不必,卑职住在升平坊,与郭队正不顺路!”
“那行,我等就先告辞了!”
“慢走!”
从案牍坊出来之后,一个兵士问郭虔瓘:“队正,我们现在去哪儿?”
“先去找一个摊子吃一顿早饭,然后回营中好好睡上一觉,睡好了再去向使君禀报游景云的事情,我们再请求使君让我们调查游景云!”
布政坊北街。
一辆华丽的骡车在车夫的驾驭下向右金吾卫衙门方向行驶而去,这时一个小巷子内蹿出来一个油头粉面、长相颇有西域风情的年轻男子拦在了骡车前面。
“律——”车夫急忙拉住缰绳停下骡车。
车厢内传出一个女声:“十八,发生了何事?”
车夫连忙回话:“回禀娘子,有一年轻小郎君拦住了去路!”
车夫说完立即凶神恶煞的看着年轻男子喝道:“小子,你找死不成?竟敢拦截我右卫郎将的家眷车驾!”
这年轻男子却对车厢拱手说:“敢问车内娘子,可是去往右金吾卫狱探监?”
车厢内沉默了一下,一根葱白羊脂玉一般的手指挑开车帘子一角,一双眼睛盯着俊秀年轻男子看了看,“是又如何?小郎君是何人?何故拦住奴家车驾?”
年轻男子急忙拱手作揖:“小子梁玉郎,家人因犯夜被抓进右金吾狱,小子前往探监,但狱丞和守卫禁兵见小子人微言轻,不肯让小子进去,小子无奈,只得返回,不想却看见娘子车驾,心知娘子必定是贵人,若是娘子能带小子一同进狱中探望家人,小子感激不尽,必定衔草结环以报娘子大恩!”
车内女子见这拦车的梁玉郎身形高挑,不仅长得秀气,还有着一副西域人的面孔,那眼神简直要人老命,她忍不住心中起了一阵涟漪,当下忍不住就答应了:“看在你一片赤诚的份上,上来吧,奴带你进金吾狱!”
“多谢娘子、多谢娘子!”
梁玉郎连声道谢作揖,然后走到骡车旁边撩起长袍下摆就上了骡车钻进车厢。
车夫十八扭头看见这梁玉郎竟然真的钻进了自家娘子的车厢,张了张嘴,却是无奈暗中叹息一声,驱赶骡子向右金吾卫衙门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