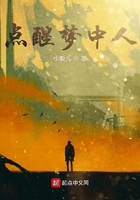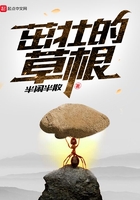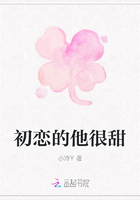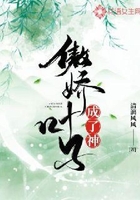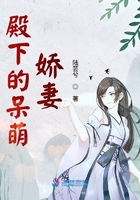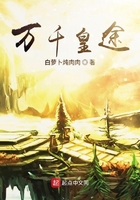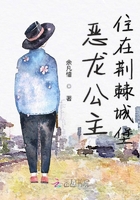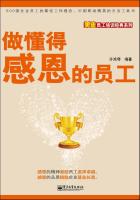接下来几日赵婷雯没再闹着要出去玩,整日里幽怨着,徐倾阳难得几日清静,想趁这几日赶紧把作业做完。
平静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被打破,而这几日来赵婷雯压抑着的情绪也终于找到了个爆发口——徐倾阳把一锅粥煮糊了。
或许是少添了一瓢水、多抓了一把米,或许是灶下多填了几把麦秸秆,总之这锅米粥就是煮糊了。其实也不算严重,只是略有糊味,再徐倾阳看来这点味道完全可以接受,但赵婷雯却执意要倒掉重做,又给出什么致癌、对身体有害的理由。
几番争论后徐倾阳做出让步,这锅粥自己和太爷爷喝,另给赵婷雯热一盒牛奶。
吃饭时赵婷雯还在说这事,她喝着自己的罐装牛奶,还认真的数落着徐倾阳:“你这就是穷人思维,分不清轻重,如果因为这一锅粥吃坏了身体,要花更多的钱去医院治病,那更是一种浪费。”
徐倾阳觉着委屈:“可是课本里教育我们要节约粮食,这么一锅粥难道要扔掉?再说了,这糊的不严重,又不是不能喝,人身体哪有那么脆弱。”
“学校虽然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可是并没有让我们去拿自己的健康做代价。你这不叫节俭,叫愚蠢,一锅粥而已,又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小姑娘伶牙俐齿,论讲道理徐倾阳自然说不过她。
可一旁吃饭的太爷爷却不知怎地,似乎耳朵突然灵光了,听清了赵婷雯这番话,他停下筷子,眼皮微微下垂,神情有几分落寞,叹了一声。
“要是当初你奶奶有这么一锅稀饭,也不至于活活饿死了。”
赵婷雯下意识的想要反驳,时代不同境遇不同,现在早已不是那个课本里描绘过的穷苦年代了。可不知怎的却突然想起了前些天自己绝食了两顿,便觉得饥饿难耐,活活饿死又是怎样的一种感受?赵婷雯想象不出来。
徐倾阳对那个时代的认知也很模糊,他知道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很艰难,却对后面几十年的事情不甚明白,他看着太爷爷大声问道:“人为什么会饿死啊?”
太爷爷沉默好一会儿,才决定给孩子们讲一讲那个残酷的年代,他咳嗽几声,徐徐讲道:“那个时候的人,白天要下地干活挣工分,晚上妇女还要去生产队纺棉花织布,又常常吃不上饭,有的人就饿死了。”
赵婷雯疑惑:“可是白天去田里干活,那田里收获的粮食呢?”
太爷爷眼中闪过一丝怒意,说道:“那时候农村生产队天高皇帝远,为了比拼政绩都可了天的往上报收成,一亩地打二百斤粮食说能打八百斤,打的粮食还不够交公粮,还要去其他生产队借粮食交公粮,自己生产队里一袋粮食都不剩下。人饿得受不了了,有的去城里卖小孩换一袋米,有的扒树皮吃,村里的树皮都被扒干净了,还有的人趁夜里去偷着刨红薯,可偷也不行,让生产队逮着了有处分。”
太爷爷越说越激动,他平复了下心情继续说道:“你奶奶那时候不敢跟着别人去偷红薯,都是别人偷着给她送点,你爸年纪小还不懂事,饿了就哭就闹,你奶奶心疼孩子,有点吃的就都给你爸吃了,自己身体却是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呢?”徐倾阳问。
“后来啊,”太爷爷浑浊的眼睛盈盈闪着光,“后来生产队发现有人偷红薯,就组织个巡逻队天天巡逻,我连续三天都没瞅着机会。”
赵婷雯沉默了,原来那个给自己奶奶送红薯的贼就是眼前这位老人。
“雯雯的奶奶就是那几天死了,阳阳本该有个大伯,也是那时候没的。”太爷爷语气越发悲伤。
徐倾阳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过一个大伯,旋即又问道:“那后来生活又是怎么变好的呢?”
太爷爷搓了搓脸上的皱纹,说道:“国家一直在努力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地方上做的不对,国家就派人来教育,来管理。老百姓穷,国家就想尽办法让老百姓富起来。你看现在好了,家家户户有房子有地,吃不愁穿不愁,还有电视机摩托车,还有电话,要搁几十年前说俩人隔着几千里地能说上话,那谁敢想呢?”
太爷爷继续感慨着时代的日新月异,赵婷雯能听懂的不多,还在回味着这个老人先前的话,原来自己父亲幼年时有过这般经历,怪不得即便现在生活好了,他还是保持着节俭的习惯。在上海家里,每顿饭总会剩下一些菜饭,这些剩饭连保姆都不大情愿吃,父亲却能吃的津津有味。
赵立伟是做服装厂发家的,可自己在穿衣服上却相当节俭,一身衣服在洗衣机里洗了又洗,都不肯添置一身新的。再说另一个品质,能吃苦,就说前些日子赵立伟送女儿到徐岗村时,从上海过来驱车将近一千公里,硬是连个司机都没带,赵立伟一个人开车十几小时,到当地县城招待所稍作休息后就送女儿来到乡下。
赵婷雯不再坚持向徐倾阳推荐自己那套“健康饮食”的理论,却也不大可能因为老太爷的一番话就敢尝一尝糊了的米粥,只是默不作声的啃着习惯吸着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