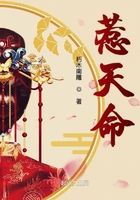饶顺雨此生并无什么成就,唯独生了个儿子,三岁就能如五岁孩童那般说话,正当收拾着东西,班碲夫问道,“母亲,为何父亲纳了个娘母便把蔓越山的主宫隔开?”
她随口骂道,“小孩子懂什么,是怕那个女人伤害你”
“可她为何要伤害我?她也会伤害海棠姐姐吗?”
“你关心小海棠做什么?”
小孩子的心思总是单纯,他便说道,“姐姐是我唯一的朋友”
乳娘惊叹一声,这个年纪别人家的孩子才刚支支吾吾会说点话,怎么班碲夫就能如此?
饶顺雨回道,“她不会伤害小海棠,她是小海棠的妈,你是我儿子,她只会......”,再编下去,她居然有些于心不忍,那日确实看到了青棠瘦骨嶙峋的病态,都是做人母亲的,心想着若是自己的儿子也惨死,自己该如何活下去,便道,“她也不会伤害你,她只会抢走你父亲”
他又要问些什么,饶顺雨不耐烦地指着门口道,“行了,出去!再问今日便没有牛乳喝”
尽管她极度讨厌这个儿子,但总归是做母亲的人。老夫人知道她对待儿子十分刻薄,甚至还会打骂,心情不好时更是变本加厉,多次要接去带一带,饶顺雨又死活不肯
班碲夫在外头独自玩着台阶上的泥巴,抬头见母亲口中说的那个父亲新纳的妾室向自己走来,便问道,“娘母好,娘母就是海棠姐姐的母亲吗?”
“你好,我是二夫人,你是谁?”青棠半蹲在地上
“我是世子班碲夫”
她错愕,“你是碲夫?”
“娘母第一次到朝班府吗?我母亲是大夫人,护国府大将军之女”
确实,这种随时将自己身份挂在嘴边的做法也只有饶顺雨干得出来了,她又问道,“怎么是你一个人在外头?你母亲呢?”
“母亲不喜欢碲夫随时叨扰,海棠姐姐又整日都在先生那里,碲夫只有自己玩”
她向碲夫伸过手去,“走吧,娘母带你进去找你母亲”
推门进去,饶顺雨破天荒地关心道,“瘦得犹如皮包骨头,还回来做什么”
青棠抚摸着班碲夫的脸颊道,“大可放心,不与你抢你家大人”
“此话当真?!”
“你看就是了”
饶顺雨见她看班碲夫的眼神,是那种母亲对儿子的慈爱,若当初不是自己替班苏瞒着,也许青棠的孩子也不必死。心里虽是同情,但口中那句对不起也没能说得出口,“不跟我抢?那你回来做什么?”
“不必管我,做好你的诰命夫人,但你告诉我,杜滨发生了什么事?”
班碲夫十分懂事,坐在旁边半句话都不说,自顾自玩着,待饶顺雨不出声了,他才敢说道,“母亲,碲夫想吃这个点心”
“对一个下人操什么心”,饶顺雨不耐烦地从桌上拿走那盘糕点放在地上,班碲夫伸手去够的那一瞬间,手挽上露出一个个淤青,青棠立即将他袖子掀起来
“这!怎么回事?”
“小孩子磕磕碰碰的”,饶顺雨丝毫不担心,“在所难免”
“他可是你儿子!”
饶顺雨抱起班碲夫指着青棠道,“碲夫,母亲跟你说,你的第一口母乳都是你娘母味的,你以后便是她的儿子,她带着你,如此一来你便可以日日跟着小海棠去见先生了”,说罢便将孩子推给青棠,“你关心,你带去养着,我是养不动了的”
“你!”
她突然哭起来,“你可知你走后,班铭从未来看过我们母子,碲夫学步快于常人,我教他如何去班铭面前讨巧,如何去表现,班铭也从来都只顾着让小海棠去见先生,对碲夫连一句问候都没有,老夫人要从我手中抢走碲夫,我怎么可能把我儿子的未来葬在她们手里!”
“这就是你如此对待碲夫的万般借口?”
“青棠,你把碲夫接过去吧,他聪明,在你身边,班铭无论如何都会看他一眼的”
班碲夫从青棠手上接下绢帕给饶顺雨擦泪,“母亲不哭,碲夫跟着娘母去”
青棠带着碲夫转身那瞬间,饶顺雨大吼,“你说的不与我争,别忘了!”
“说到做到”
“杜宾的事,别问了,如今府上没有你半分地位,与他保持距离。也别想着其他的事情,不然,你会再死一次的”
她这句话说得如此中肯,青棠却越发担心,身边值得信任的人一次又一次败在班苏手上,她回头看了一眼又念叨着:“你是不知,班铭如此对你并非是因有我存在,我自诩是他心尖上的人,他却连我都护不了”
班碲夫抬头问青棠,“娘母以后会欺负我母亲吗?她很可怜的”
青棠蹲下来对他道,“我怎么会欺负你母亲?”
“母亲说娘母抢了父亲”
“所以不管你父亲喜不喜欢你,你都要长大,保护了自己才能保护你母亲”
“碲夫记住了”
......
将近夜时,班铭喝了酒进到青棠的寝殿中迷迷糊糊倒在桌子边睡觉,青棠惊醒,见班铭犹如死人满身酒气不忍侧目
她穿了衣服出去,杜滨从今早就一直坐在湖中庭发呆
主宫隔了的好,里头一应侍女侍卫全是穿庭府的人,且一众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都还都是陪着青棠长大的,自然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你那个膝盖吹不得冷风,为何一直在湖中坐着?”
杜滨拄拐下跪道,“夫人,大人他......”,他朝大殿看着
“喝醉了,我让侍卫送他回房”
杜滨起身告别道,“请夫人原谅,杜宾不敢再与您交谈过多,以免您又蒙受不白之冤”
“清者自清,只是我从未想过,你有功夫在身,在朝班府当牛做马那么多年,最后却无故被人利用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他叹息,“无论如何,自我离了老爷身边,是朝班府养着我,再受太多的委屈也罢,这里头上上下下总还是有人叫我一声侍卫长,也知足了”,又半跪道别
“你可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杜滨,当然记得”
青棠走到他近旁道,“你自一生下来就被我父亲带回南方府中抚养,青家于你有恩,只是后来你愿意自谋生路时却误打误撞进了朝班府”,她看着自己慢慢恢复血色的手心肉,“你知道班苏为何要将你名字改成杜滨?”
他笑道,“杜詺,与主子名字重了”
“海外有一种狗,名叫杜宾犬,你生是堂堂正正之人,凭什么让他如此糟贱?”
杜滨低头良久
青棠起身掐下身旁花上的一朱花蕊,“青棠有一件事情没弄明白”
“夫人请讲”
“祖太金娘娘下令剿灭乱党后第二年,世子班铭回府,不见自己母亲的身影,户长史大人只道是乱党误杀后便对此避而不提,虽在祠堂中供奉,世族园林中却不见母亲墓碑,知晓此事的侍女侍卫一夜之间消失无踪,这其中,只有户长史大人身边的小侍卫不曾参与,也从中幸免于难”
杜滨连呼吸声都开始加剧,“小姐......老夫人是被户长史所杀!”
“大人喝醉了,你去照顾一下”,青棠头也不回地往自己寝殿中走
......
班铭被扶回自己寝殿中睡着,自青棠回府后,不管他装醉或是真醉,总不愿与他同房
侍女喂他喝下醒酒汤,伴随着剧烈的头痛,他不自觉叫了一声,“青棠......”
“大人,是我,杜滨”
他睁眼一看,揉着鼻梁睡眼惺忪地问道,“夫人呢?”
“方才大人跑到夫人房中的桌子上趴着睡了,夫人怕您着凉,便让下人将您扶回来”
他嗤笑道,“她果然还是不愿接受我,怕我着凉,为何不让我在她房中睡下?”
杜滨道,“夫人的身体还未调养回来,近几日也都在照顾世子,无暇顾及其他了。快到老夫人的祭日了,大人何时去祠堂将老夫人的信物拿出来做个祭典才好”
这一题勾起了班铭的心事,他心头惶惶不安,“对啊,竟忘了,只是宗长下令不能碰母亲的遗物,如何是好”
杜滨装作唐突道,“大人,遗物......”,而后又没了声气
“什么?”
“......”
“说啊!”
“大人,杜滨在第三狱中原以为自己要死了,只想见大人一面,将十多年前老夫人的死因道出”,杜滨看着班铭的眼睛,里头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今日便都要说出来,“二夫人是被宗长所害,同样‘莫须有’的手法,也用在了老夫人身上!牌位下信物盒子里根本没有老夫人的遗物!”
班铭突然站起来拔剑抵在杜滨脖子上,“你可知你说的若有半句假话,犹如欺君之罪!”
“尸体埋在宗长寝殿门口的鱼塘下面,而鱼塘底则是重达万斤的铜币所制,意在镇住下头的亡灵!”
......
班苏从门口侍卫杂乱的脚步声中惊醒,池塘最上方用大理石雕刻的雕像轰然倒下,人群中班铭满身酒气地举着火把,池塘中的水早已抽空大半,留下能没过膝盖的泥沙
“逆子!你做什么!”
班铭回头看了一眼,凶恶的眼神伴着火光燎燎更加让人感到背脊发凉,“把宗长和老夫人请到近前!看看这池塘地下埋着谁的至亲挚爱!”
“你敢!!!”
“我为何不敢!”
半柱香时间,朝班府各处宫院的户史点着火把走来。侍女站在池中掏着泥沙,侍卫用榔头铁杵不断敲击着那层铜币制成的隔层,一块块破碎的铜板被撬开
“慢死了!”班铭抢走侍卫的铁杵跑到中间挖掘下层泥土
临近清晨,众人的火把已经熄灭,伴随着昨夜的雾气散开,班苏大喊道,“尽管挖!挖不出什么便把朝班府的地也挖通!”
他终于跌坐在泥沙里一言不发
“怎么?不挖了?那就散了!”
人人皆慢慢退避,他盯着裂缝的雕像不说话,京州城钟楼的声音响起
“慢着!”
他举起斧头一步一步向石像走去,重重一击朝裂缝劈去,雕像骤然裂开
侍卫蹲下检查道,“是铜!大人,是铜!”
一锤又一锤,铜铸的内里裂开,里头散发着尸体腐烂发臭只剩骸骨的气味,手骨上挂着许多手环,从尸水中捞起一个不起眼的流苏结
他立马大喊,“拿妩仪剑!”
随着尸臭蔓延到众人的鼻腔中,各个捂住口鼻不忍直视,班铭跪在骸骨旁边,那流苏结竟然与妩仪剑上的一模一样,班苏吓瘫在轮椅上
“母亲,儿子来晚了,儿子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