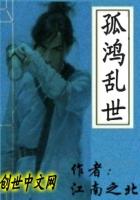岗从太平观里出来,并没往植英斋去,他气冲冲转过几条街巷,来到一家油坊前,一脚踹开大门闯了进去。油坊里的伙计见他进来个个惊慌,也没人敢拦他,就眼睁睁看着他穿过前店、磨坊,掀开后屋房门,气呼呼一屁股坐在了屋里的案桌上。
屋里的人都惴惴不安地看着他,也不敢说话,只窃窃私语着:“阿丘呢?”“在后厨忙着呢。”“快叫他过来。”
不一会儿,只见那常与岗碰头的布衣,也就是众人口中的“阿丘”腆着笑脸迎了过来:“大哥这两天哪儿去了?叫兄弟们好找啊。”岗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反手一嘴巴把阿丘抽翻在地,还不解气,一边疯狂踩着一边骂道:“好找!好找!好找还找不到!”直踩得阿丘连连求饶,他这才解了气,长舒一口令道:“起来。”阿丘慌慌张张从地上爬起,嘴角挂着红,腿肚子直发抖。
“这两天有什么事没?”岗问道。阿丘连忙抹了嘴角的血迹,回道:“除了马良回宜城途中在岘山留了一宿就没别的什么事了。”岗将信将疑看向他:“真没别的事了?”“哦!”阿丘猛然想起,又说道:“昨日黄承彦的下人路过襄阳,我们在他行囊里发现一封信,就抄誊了一遍,信是给江夏黄氏的,说的是要设宴庆贺他女婿入仕的事。”
“信呢?”“在这儿。”阿丘在衣襟里翻出一张折成四叠的纸递了过去,岗展开读完,扬手做了一个要抽人的动作:“这还叫没事儿?”阿丘唬得慌忙抱头,连声认错。
岗并没有抽下去,将信收回了自己的怀中,又问道:“让你找的‘寅组’的人找了没?”“找了,找了。人就在后厨绑着呢,什么‘罪证’都有,就算张释之活过来都挑不出半点毛病。”被问到了自我感觉办得周全的事上,阿丘马上接上了一副谄媚的笑脸。“把人带过来我瞧瞧。”“是!”
须臾,阿丘与几个伙计拖着一个鼻青脸肿的男子扔到了岗的面前,这男子一见到岗,就抱着他的脚连声呼道:“冤枉啊!我真的没杀你们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城里还有‘丑组’的人!大首领,一定相信我啊!”他那张被打得面部全非的脸上,原本该长着眼睛的位置被几坨乌紫乌紫的肉包挤得只剩下两个小孔,不住的眼泪从这两个小孔里流出,倒是洗刷了一些脸上的血迹。
“嗯,嗯,都是同门,我相信你。”岗敷衍两声,把那只被他抱住的脚抽了出来,看着足袋上血印不禁皱了皱眉:“不过,我的人也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你,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我需要跟你们首领聊几句,把误会化解开,你告诉我上哪儿找你们首领?”看着男子犹豫,岗又补充道:“放心好了,同门不相残,误会化开了就放你回去;化不开也没事,已经搭了一条人命,都是隐门同袍,再搭一条,我于心不忍啊,事情都过去了,人死也不能复生,我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便是。”
男子闻言给岗“砰砰砰”的直砸头,口里不停叫道:“谢谢大首领,谢谢大首领,首领真是大善人。”瞧着脚下这位对着自己感恩戴德的男子,岗嫌弃得直咧嘴:“行了,行了,别磕了,告诉我怎么找你们首领吧。”那男子停了磕头,老老实实地回道:“就在北大街西二巷子里的‘喜昌客栈’。”
“客栈?怎么知道谁是你们首领?有暗号吗?”
“客栈是个幌子,其实就是我们‘寅组’的据点,里面除了我们的人没有别的人。最近天冷,首领一般都在,不怎么出去。”
“行,我给你们首领写封信约一下,免得唐突赶去显得不尊重。”说完便吩咐旁边伙计去取来纸笔,提起笔又问道:“你们首领叫什么?”“弥崎,弥补的弥,崎岖的崎。”“一个代名取什么两个字,这么多笔画,真麻烦。”岗嘀咕着,在纸上书写起来。片刻功夫写完了信,唤来阿丘,递与他说道:“给弥……弥……”“弥崎。”阿丘提醒道。“对,弥崎首领送过去,他什么时候约见我,我什么时候给他送人过去。”阿丘领信离去,岗又对周围伙计叫道:“一个个傻愣着,弄点吃的去啊!饿死老子了!”那些个伙计争先恐后地望着后厨跑去。
差不多一个时辰左右,阿丘回来了,一进屋就大声嚷道:“大哥,弥崎约大哥客栈一聚。”岗瞥了眼那“寅组”的男子,他那两个小孔里射出来的光连周围一圈暗紫色的肉包都没法遮挡。岗“啧啧”了两下,抬头与阿丘问道:“小点声,大嚷大叫的干嘛?那个弥……弥……”“弥崎。”“对,弥崎,说了什么时候了吗?”
“说了,今日午后便可。”
“怎么比我还着急?罢了。你见到他了,他长什么模样?”
“挺高大,虎背熊腰的,看上去很是威猛。”
“很是威猛啊……”岗嘴里碎碎念叨着,又向那“寅组”男子问道:“你们首领会武功吗?”“会呀,我们弥崎首领武艺高强,气大无穷。”男子那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脸上竟让人轻易就能看到上面洋溢着自豪。岗是没工夫管他自豪与否的,他此时也不知在琢磨着什么,坐在案桌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直挠头发。挠了半天,估计也是心里愁的事没想到法子,便伸手从旁边把方才没吃完的羊腿抓了过来,拿着小刀割起肉来。
割着割着,看着手里的小刀突然眼里一亮,嘴角忍不住得上扬起来。只见他将羊腿一扔,拿脚碰着趴在地上的“寅组”男子说道:“起来,起来,我带你去见弥……你们首领。”“真的?”那男子滋溜一下爬了起来,欣喜的语气配着他的肿眼泡腮在岗眼里简直就是惨不忍睹的滑稽。“嗯,真的,你闭上眼。”岗紧锁着眉头,强忍着笑意说道。男子不明就里:“闭眼干嘛?”“让你闭你就闭,哪儿那么多废话?想不想回去了?”见岗有些不耐烦,男子不敢违逆,马上乖乖闭上了眼睛。“这才像话嘛。”岗嘴角一扬,突然,猛一挥手中小刀,那男子脖子那里当下喷起了一道血柱,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
冷不丁地就杀了人,屋里屋外的手下都惊呆了,一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措。看着这些手下个个跟雕塑似的立在那里,岗烦躁地叫道:“都傻愣着干嘛啊?把脑袋切下来啊!去找个好看的木匣子,装了给‘寅组’送大礼啊!”手下们这才回过神来,几个上来砍那男子的头,几个去寻盒子,还有几个懂事的直觉上来清洗屋子。
看着手下们的忙活,岗总算是满意了,又与众人说道:“你们一会儿吃饱肚子,带上刀剑,随我一同去喜昌客栈!”众人齐声应是的声音洪亮震耳,竟使岗嘴角的那抹奸笑看上去有了些踌躇满志的味道。他从案桌上跳了下来,走到阿丘旁边,侧身对他,看也不看就翻掌伸了过去。阿丘不知他要干嘛,又不敢多问,直愣愣看着伸在自己眼前的手掌,哆哆嗦嗦,竟拿自己的手放了上去……岗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向阿丘,占满眼帘的是阿丘那张傻笑着的大脸。岗甩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又将阿丘抽翻在地,上去“砰砰”往他身上直跺脚,口里气冲冲地骂道:“老子是来搀你的吗?拿剑啊!叫你把老子的剑拿来啊!”
屋子里,砍头的砍头,洗地的洗地,打人的打人,热闹非凡,其乐融融……
北街以西,在襄阳城中算不上什么繁华的位置,西二巷子更是萧条,但偏偏有人不顾这份萧条的和谐,非要在一片低矮瓦砾当中突兀地耸起一座三层的客栈,这便是“喜昌客栈”了。说也奇怪,明明没有多少过客往来,这家客栈门头的灯笼却长年不亮,永远都是客满的状态,也是叫城中其他的客栈掌柜嫉妒不已。
此刻客栈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从一层一直沿着楼梯挤到了二层,足有百人。一层正当中到客栈的大门,拥挤的人群让出了一个长方形的空白,里面摆着一张桌案,后面坐着一个黑壮的汉子。这汉子胡子拉碴,身形魁梧,大冷的天只在裋褐外面套了一件羊皮坎肩。他粗犷的模样与正襟危坐的姿势总让人觉得不太和谐,就如西二巷子一片矮屋当中的“喜昌客栈”一般,这汉子便是“寅组”的首领——弥崎。
听得几声叩门声,门口的人打开客栈大门,岗终于舍弃了那身红曲裾,以一个清秀美少年的模样出现在了门口。他领着手抱乌木大匣子的阿丘刚踏进门,门口的两个人,一个上来要卸他的剑,另一个就要夺阿丘手里的匣子。岗甩手摆开卸他剑的人,又把夺匣子的人推开,大声叫道:“我是隐门‘丑组’首领——岗!本门规矩,首领之剑,唯有掌门可卸!”他这底气十足的一嗓子确实有用,屋里的人一个个都被他震住了,不敢妄动。
“你说你是‘丑组’首领,有首领印吗?”坐在案桌后的弥崎却是不吃他这套,他嗓音深沉而浑厚,仿佛山中猛虎扑食之前喉咙里的低吟。
“我支老首领遇害,首领印随她一起沉到河底了。”
“那我如何信你?”
“首领印没有,家主印不知大首领认不认?”岗从怀中掏出一块小东西向他抛了过去,弥崎接住一看,竟是一块刻有蔡琰名字的金印,这可算是蔡家品级最高的信物了。弥崎拿住金印,反复查看,辨明了真伪后大为意外:“‘丑组’也是效力蔡家?”
“若非如此,我怎会专程造访?”
“你怎会知道我‘寅组’效忠蔡家?又是怎么知道这间‘喜昌客栈’的?”
“自然是主公告知。”
“为何告知与你?”
“大首领的人让我们之间闹了点误会,都是一家人,主公自然是希望误会化开的。”
“你来信说要把人还我,人呢?”
“正在植英斋好吃好喝着呢。主公说,在下与大首领之间的误会化开了再把人送回来才不会结下梁子。都是为蔡家效忠的,主公可不希望今后你我之间有什么不对付。”
“既是主公之意,信上为何不说?”
“信上若是说了,大首领接见在下,是诚意还是被迫?若是被迫,这事了结以后,你我的误会化了还是没化?信上不说,正是主公忧心啊。”
“既然如此,主公为何单与你交代,不曾知会我一声?”
“一件小事,让主公劳了心,在下与大首领的颜面本就不好看,还要主公两边周旋,你我该当何罪?趁着在下去的时候私下交代,让在下与大首领自行解决,这是主公在给你我台阶啊。”
岗有蔡家的上等信物,话里也挑不出毛病,按说也是可信了,不过弥崎就是看着他那张漂亮脸蛋上谦逊到做作的微笑感到阴森,让自己不寒而栗。弥崎盯着岗上下打量着,目光落到了阿丘手中的乌木匣子上,问道:“那里面是什么?”
“初次造访,自然是给大首领备的大礼。”岗拍了拍匣子笑道。
“让客人抱着这么大的匣子可是失礼了,还是交给旁边我们的人代劳吧。”
“当前不可,在下还需与大首领闲聊几句,若是聊得愉快,这份大礼自然奉上;若是聊得闹心,这匣子在下还得还回植英斋。”
谎称是受了蔡琰的密令,岗打的算盘一来是让他不要为难自己,二来才是更主要的,这匣子万万不能让他强开。弥崎眼睛直勾勾盯着那匣子良久,缓缓说出了一句:“既然如此,就委屈岗首领受累了。”弥崎改口称了“首领”,岗的算盘算是打着了。
随即,弥崎吩咐门口的人让了岗进来,又说道:“既然都是自家人,岗首领可不必卸剑,以‘不攻’拿剑即可。”
剑,通常佩以左腰,右手拔出使之。而“不攻”这种携剑的手法,是以右手反握剑鞘,这样就去除了右手使剑的可能,就算运气不好,遇着了那万分之一的惯使左手的剑客,这样的姿势会也让拔剑困难许多。弥崎倒是不怀疑岗是受了蔡琰的密令而来,他只是不太放心岗这个人,可他偏又是个讲规矩的人,按隐门规矩他也确实没有卸岗剑的资格,故而只得提出这等小小要求,只要岗是带着诚意的,那便不会抵触。
果然,岗大方以“不攻”握了剑,步入屋中,恭敬与弥崎拜过礼后问道:“大首领这里有无僻静处?在下想与大首领借一步说话。”岗已显了诚意,弥崎自然也就不再为难与他:“随我到上面来,匣子就请岗首领受累自己抱着。”“这个自然。”岗从阿丘手里接过匣子抱在怀中,又叫他先回,弥崎没有说话,屋里人也不阻拦,放了阿丘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