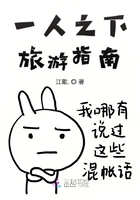清脆的铃声在教室外响个不停,像个摇着铃铛的唠叨嬷嬷,站在课桌边,催促你放下疾书的笔。
她告诉你,你长大了,该离开了,学会飞翔吧,她也老啦。
这个盛夏,在教会学校成长的孩子,将在她的祝福中飞向远方。
张谷神是第一个走出教室的,他走下楼道,与逐渐离开教室学生们一起,来到教学楼外。
他看到了珊妮女士,孩子们依恋的修女交叉着双手,站在枫树下翘首等待。
修女已经很久没再教他文学课,但她还是孩子们的班主任,她没有子嗣,也没有伴侣,在这十几年里,她一直陪伴在孩子们身边。
珊妮女士看着他们长大,她付出了许多心血,只因她已将他们看做自己的孩子。
张谷神没有见过母亲,张牧之没有续弦,也不常提起他的生母,少年只在只言片语中知道自己的相貌与母亲相似,尤其是如瀑如织,乌黑柔顺的黑发。
所以张牧之一直让长子留长发。
他对母亲这个概念缺乏认知,在国公府时,世子心中母亲的形象是第一位照顾他的奶娘,来到教会学校后,这个形象渐渐被珊妮女士代替。
那时的珊妮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喜欢唱歌,喜欢看散文诗,经常用歌曲的调子哼唱诗集,虽然大部分孩子还是更喜欢她讲的故事。
她本有她的青春,但被她全灌注在教会学校的孩子身上。她会学着唐娜女士,为孩子们做饼干,她会学着卡萝女士唱歌,在睡前为孩子们唱安眠曲,她会在深夜悄悄走进寝室,温柔地为孩子们掖好被子,她会在孩子们生病时,急得掉下泪来。
张谷神和孩子们一样,把珊妮女士视作母亲,他曾见过塔露拉的看向修女的眼神,想必女孩也是一样的。
于是他走上前去,与珊妮女士道别。
“珊妮女士,您好。”
他的心里还在惧怕,并没有说出那个亲切的昵称。
“啊,谷神。感觉考得怎么样?”见到孩子,珊妮女士欣喜地走到张谷神身边。
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比她高出许多,而她的面庞也不再光滑,眼角延伸出一缕时间淌过的痕迹,连笑容也不如以前有活力,只泛着满满的母性。
他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那天,艾普丽女士拉着他的手,站在教室门外,怕生的他第一次见到她。
“正常发挥,应该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太好了!你的成绩一直是最好的,我对你有信心。”
张谷神沉默下来,他还有许多想说的话,此刻却哽在喉中,不知从何说起。
他不擅言辞。
“我要离开了……请您保重。”
那就道别吧。
修女的笑容也渐渐消失,她叹了口气,拉起张谷神的右手,用双手握着孩子的手。
孩子的手已经很大了,明明以前一只手就能握住。
“谷神,你是个很受欢迎的孩子,要多交些朋友。”
“……我会,试着去做。”
“今天是个值得高兴的日子,别这样。我会通知你成绩的。”珊妮女士又笑起来,噗嗤地驱散了伤感。
“我会回来探望您。”他也笑了。
教学楼外的学生越来越多,此时已经有同学来与珊妮女士打招呼。
他们也是她的孩子。
“愿神保佑你,孩子。”
张开双翼,努力飞吧。
“也愿神保佑您。”
他并不信神,在祈祷时只会做个样子,平时也不喜欢神学课,但至少现在的他是虔诚的。
修女放开他的手。
离开修女后,张谷神又在校园里转了转,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学生的身份来这了。
教会学校承载了太多的回忆,走在校园里,那些碎片会像泡沫一般浮起来。
曾经有人与他牵着手,并肩走在这个广场上,后来变成三个人,坐在这张长椅上,现在又变成他自己。
教会学校扩建了新的校区,孩子们都搬到新的宿舍里,还有更大的操场供他们活动玩耍,这个小广场少有人来,它旁边的旧宿舍也被闲置了。
就像那间老屋,成为被遗忘的一部分。
他常会来这散步,绕着广场走两圈,然后坐在这张长椅上,静静地想自己的事。
在这里,张谷神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也有很多不好的回忆,但这就是人生,他总得学着去接受,一直逃避是无用的,是很累的。
而且他是个念旧的人。
塔露拉离开后,张谷神没有再去交新的朋友,他与谁都能说上两句话,但也仅限两句,很多时候都不予回应,就连他都认为自己很孤僻。
珊妮女士说他很受欢迎,张谷神一笑了之。
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手插在兜里,慢悠悠地往校门口走去。
现在已经过了学生最多的时候,校园里的行人稀稀落落,像深秋的树木,叶子大都脱落了,只剩个光秃秃的枝杈,不禁地让张谷神想,这个学校是否到了暮年?
他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现在是盛夏,是万类最繁茂的季节,离秋季还有两个月,那时校园里的枫叶会变得一片金黄,黄灿灿红彤彤的叶冠聚在一起,放眼一望,是起伏的织锦蝶翼似的波澜。
若是说暮年,则要到再之后的冬季,萧瑟的寒风会吹走残余的枯叶,校园里的草木会像睡去一般枯萎,然后披上银装素裹的被子,留下一片沉沉的白地。
但春季也不远了,积雪终会融化,老树会抽出新芽,沉眠在冬季的草木都会苏醒,就像学校里的孩子们,永远保持着青春活力,永远都没有暮年。
四季变换对孩子和草木来说,不过一次小憩。
像是一场一场梦轮回。
他怔怔地看着眼前人,也成了被惊醒的人。
少女就站在他几步外,撑着腰喘着粗气,脸上是即将滴落的汗珠和泛起的红晕,蓝色发丝粘在额头和脸蛋上,两只常在他梦中出现的龙角摆脱了稚气,更加粗壮嶙峋。
她看着他,眼中是不服输的倔强。
她从梦里走出来了。
“小洁。”
今天是龙门所有学校的修业考试日,她的学校在上城区,离教会学校很远,现在距考试结束不过几十分钟。
张谷神不敢想象陈是怎么来的,他走上前去,想搀扶她又退缩了,压在心里的许多话也说不出口,只是叫出她的名字。
他开始痛恨自己不善言辞。
“我有话想对你说。”少女殷红的眼眸盯着他,咬着牙,还在急促地呼吸。
“你现在要休息,我带你去个安静的地方。”
他再次鼓起勇气,拉住少女的手,往校园里走去。
她挣扎了一下,但他抓得很紧,没能挣脱。
时隔多年,他又牵起了她的手。
陈的手是炽热的,也许是刚运动的缘故,在他的手心里冒着热气,甚至有点烫。
张谷神在路上买了一瓶水,一包纸巾,然后带着陈来到小广场,坐到那张长椅上。
刚开始陈有些躁动,但看到这个小广场后就安静下来,低着头,任他拉着自己。
他取出一张纸巾,示意她擦汗,接着拧开瓶盖,把纯净水递给她。
“塔露拉呢?”等陈小口喝完水,他终于问出藏在心里的问题。
他太想知道关于那个温柔恬静的女孩的消息了。
那对殷红瑰丽的眸子望着他,里面酝酿着他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两姐妹的瞳色很漂亮,像琥珀,像宝石,但也很能掩藏情绪,以前的塔露拉或陈和他闹脾气时,他常要去揣摩她们的心思。
“你就想问这个?”陈轻轻说。
他顿在那里,一时语塞。
“我不知道她在哪。”陈看了他一会儿,又说。
不知道?
张谷神深吸一口气,像一壶冰冷的水开始沸腾。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尽量保持平静。“塔露拉不是被家人带走吗?”
“谁说的?”
“艾普丽女士。”
“她……”陈一怔。
“她去世了。”
就在塔露拉离开后的一周。
张谷神仍记得珊妮女士宣布这个消息时,悲痛的模样。
艾普丽女士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林风眠也来了。
那些人肃穆而沉痛,穿着样式不一的黑衣,拿着一只白色菊花,把教会学校围成一片黑色的海洋。
安静而压抑,似乎能隐约听到哀声萦绕。
“她被带走了,我不知道那些人是谁。”
他想起与塔露拉离别时的样子,心中开始抽搐。
如果……
陈猛地抓住他的手臂。
“我要找到她。”她又恢复了那倔强而严厉的眼神,坚定而无畏,谁也拦不住她。
“你能帮我吗?”
去帮助陈?
不。
是他没保护好她。
他要履行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