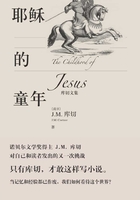色当大败的消息刚传来,共和国政府就宣布成立了。混乱直到巴黎公社后才结束。开始的时候,整个法国都在杀来杀去。
小商人成了上校,指挥着熙熙攘攘的志愿兵;和平人士在大肚子上系着红腰带,插满了手枪和匕首。
这些只拿过秤杆子的人手里有了武器,高兴得发狂。为了证明自己会杀人,他们常常杀死无辜的人。在没有遭到普鲁士人践踏的乡村里到处转悠,开枪打死游荡的狗、反刍的牛和在草场上放牧的病马。
人人都认为自己注定是这场战争中的重要角色。连最小的村里的咖啡馆都挤满了穿军装的商人,看着像兵营或军医院。
小镇加纳还不知道军队和首都那些疯狂的消息。由于敌对的派别已经交锋,近一个月小镇极端动荡。
镇长华塔纳子爵,是个上了年纪的消瘦老人。原本是正统派,前不久出于野心归顺了帝国。但是子爵突然多出了一个死敌-马沙利医生,一个红脸胖子。他是这个区域的共和派首领、农业协会会长、共济会镇分会头目、救火会董事长,还是农民保乡团的组织者。
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居然发动了六十三个有妻儿的谨慎农民和镇上的商人出来保卫家乡。他每天都在广场上训练他们。
镇长偶尔到镇政府的时候,马沙利就会腰挎手枪,手持军刀,骄傲地走过队伍前面,让那些人高呼:“祖国万岁!”有人发现,这呼喊让小个子的子爵很不安,他把这看作一种示威,一种挑战,也是对大革命时代的可怕回忆。
9月5日早晨,马沙利医生穿着军服,手枪放在桌上,正在为一对乡下老夫妇看病。男人得静脉曲张已经七年了,一直到妻子也得了这种病才一起来看医生。
这时,邮差送报来了。他打开一看,脸庞激动得抽搐。他突然站起来,举起双手,放开嗓门叫道:
“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随后,他一屁股坐进靠背椅里,激动得快要晕倒了。乡下人继续说:
“开始时,像一些蚂蚁沿着我的腿爬……”他叫道:“让我静会儿,我没时间管这些事。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皇帝被俘,法兰西得救了。共和国万岁!”他跑到门口,大声吆喝:“玛丽,快,玛丽!”吃惊的女仆跑来了,他说得太快而口齿不清:“快,把我的靴子,我的军刀,我的子弹袋,还有我的西班牙匕首,都拿过来,快!”那个来看病的乡下人趁医生住口时继续说:“……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个鼓包,我走路时很疼。”医生被惹火了,吼道:“见鬼去吧,让我安静一会儿,如果常洗脚的话,就不会得这种病。”然后抓住他的领口,冲着他大声叫道:“你不知道我们变成共和国了吗?你这个大傻瓜!”不一会儿,他安静下来。他把这对夫妇送出去,不停地说:“你们先回去吧,明天再来,我明天给你们看。朋友,今天我真的没时间了!”他紧张地将自己装束起来,同时又给他的女仆下了新命令:
“快到中尉里彼特和少尉梅森家去,让他们快来。告诉他们,我在这儿等着呢。并叫里德斯把鼓带来!快!快!”
玛丽出去之后,他开始聚精会神地计划如何应付目前的形势。那三个人穿着工作服来了。以为他们会穿军装的司令官吃了一惊。“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上帝!皇帝被俘了,共和国宣布成立了,是该行动的时候了。我的地位微妙,甚至是十分危险的。”几个下属十分惊愕。他思索了几秒钟说:“我们应该行动了,现在不能犹豫,关键时刻的几分钟能顶几小时,所有的决定都取决于迅猛果断。里彼特去找神父,让他召集群众,我要对他们讲话。里德斯到村子里敲鼓集合队伍,吉利赛和萨马尔那些小村子也要去,让民兵到广场上去。梅森赶快穿上你的军服,只要军衣军帽就行了。我们去占领镇政府,命令华塔纳先生向我们交权,明白了吗?”
“明白。”他们齐齐地回答。
“立即执行。梅森,我陪你去你家,我们一起行动。”五分钟后,这位司令官和他的下属全副武装来到广场上。这时,华塔纳子爵从另一条路走过来,像要去打猎似的绑着绑腿,扛着猎枪。后面跟着三个穿绿衣服的猎场保卫,挎着刀,背着枪。
医生停下来愣神的时候,四个人已经进了镇政府,关上了大门。医生支支吾吾:“我们被人抢先了,现在得等支援。暂时什么也干不了。”
中尉里彼特出现了,他说:“神父拒绝服从,他和教堂执事、侍卫把大门关上了。”
广场另一边,对着关门的镇政府就是静悄悄的黑色教堂,包着铁皮的大门格外显眼。这时,好奇的居民们躲在窗户后面或站到门口看着。突然,马沙利敲着集合鼓点迈着正步穿过广场,很快消失在田间小路上。司令官挥舞着军刀独自走到敌人占据的两幢房子的中间,吼叫着说:
“共和国万岁!叛逆者必死!”然后,他开始往回走。
放心不下的肉店老板、面包店老板和药店老板都关上了门。只有小杂货店还开着。
民兵们陆续到了。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头上都戴着有红边的黑军帽。军帽成了全团统一的标志。他们拿着三十年来一直挂在厨房壁炉上的生锈老枪。看起来像一队乡下的护林人。
司令身边聚集了三十多人,他用几句话交代了情况,而后回头对他的参谋部说:“现在行动。”
居民们聚集起来,一边看一边议论。医生很快确定了他的作战计划:“里彼特中尉,你到镇政府的窗户下面,以共和国的名义要求华塔纳先生将镇政府交给我。”这位原是泥水匠的中尉不遵从,他说:“司令,您是个大滑头,要我去挨一枪。里边那些人枪法都特别好,这个您最清楚。您自己去完成命令吧。”
司令官怒气冲冲地说:“我以司令的名义命令你去。”中尉反抗:“我可不会糊里糊涂去送命。”围在一旁的好些人都窃笑起来,其中一个人嚷道:“你说得对,里彼特,还没到时候!”医生骂道:“一群胆小鬼!”
于是,他把军刀和手枪交给一个士兵,决定亲自上阵。他慢慢往前走,眼睛盯着窗户,提防有枪瞄准他。走到房子附近的时候,旁边学校的大门打开了,一群男孩和女孩涌上广场嬉笑打闹,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围在医生周围。
等孩子散开后,这位司令官终于鼓足了劲喊道:“华塔纳先生?”二楼的一扇窗开了,华塔纳先生出现了。司令官开口说:“先生,最近发生了政府变革体制的大事,您代表的政府已经覆灭了,我所代表的政府已经掌权。在这决定性的艰难时刻,我以新共和国的名义要求您,请交出国家授予您的职权,由我接管。”
华塔纳先生回答:“医生先生,我是正式任命的加纳镇的镇长,接到上级的撤职命令前,我仍然是加纳镇的镇长。作为镇长,我应该待在镇政府里,我将继续待下去。要不您就试试赶我走吧。”
说完,他关上了窗户。司令官回到了他的队伍里。说明情况之前,先打量了里彼特一番,说:“你真有勇气,真勇敢,简直是我们全军的耻辱,我要降你的级。”中尉回答:“我不在乎。”于是,他自觉扎进了交头接耳的老百姓里。这时,医生拿不定主意了。怎么办呢?发动进攻吗?可是这些人愿意吗?还有,他有这个权力吗?他想出了一个对策,跑到镇政府对面的电报局发了三份电报。一份致在巴黎的共和国政府成员;一份致在鲁昂的下塞纳州的共和国新任州长;一份致共和国新设的迪耶普专区区长。他说明了形势,当前这个镇的贵族镇长掌握实权,还说他愿意忠诚地服务,请求给予授权,并且在签名后加上了自己的头衔。此后,他回到了队伍里,从口袋里掏出十个法郎,说:“拿去吧,去吃点东西并喝上一杯。只要留下十个人的一小队,防止任何人从镇政府出来。”
和钟表商聊天的前中尉里彼特嘲笑他:“他们出来就是进去的好机会。如果不那样,我看你没机会进去!”
医生没有回应,自己去吃饭了。下午,他在镇子周围布下岗哨,以防镇子遭到意外的偷袭。有几次,他大着胆子走到镇政府和教堂的门前,没发现丝毫可疑的现象,两幢房子几乎像没有人。肉店、面包店和药店又重新开了门。
群众都在家里议论纷纷。如果皇帝成了阶下囚,那就是下面的人发动了政变。谁也说不准究竟哪个共和国回来了。
天色渐渐暗了。九点钟的时候,医生独自悄悄走到镇政府门口,他认为对手已经去睡觉了。他准备用十字镐砸开门,立刻,有一个像是卫兵的声音问道:“谁在那儿?”
马沙利先生撒开腿就大步往回跑。天亮了,局势没有丝毫变化。
武装民兵占据了广场,老百姓都围在旁边想探个究竟,邻村人也跑来参观。
医生决心采取措施,他明白他正在用荣誉做赌注。正当他要采取强硬措施时,电报局的门开了,局长的女佣走出来,手里拿着两张纸。
她走到这位司令官跟前,递给他一张电报,之后,她穿过那空荡荡的广场中心,走到关着的镇政府门口,轻轻地敲门,似乎不知道里面藏着一支军队似的。门开了一点小缝,伸出一只手接住了那张电报。那个女子被全镇子的人盯着而满脸通红,回来时,她几乎都要吓哭了。
医生嗓门有些发颤,他要求大家道:“都安静点,请你们都安静点。”于是,所有的群众都静下来,他扬扬得意地说:“这是我从政府接到的通知。”说着举起了手中的电报,读道:
解除旧镇长职务。优先考虑最紧急的待办事宜,后续接班人即到。
专区区长参议员萨班代签
胜利了,他高兴得双手发抖。可他的旧下属在一群人中叫道:“如果那些人不出来,这张纸只是空欢喜一场!”
马沙利的脸色霎时变了。的确,如果那些人不出来,他就该进攻。这不仅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
他急切地看着镇政府的门,期盼它会打开,他的对手能自动出来。可那扇门仍然紧闭着。怎么办?
人群越聚越多,团团围住民兵。有一种顾虑最让医生为难。如果进攻,他就得起到表率作用,走在队伍前面。华塔纳先生和三个卫兵一定会瞄准他。他们枪法很准。里彼特刚才还提起过。如果他死了,所有的较量就失败了。忽然,他灵机一动,转过身对梅森说:“快去找药房老板,跟他借一块白餐巾,一根棍子。”
少尉立即跑过去。他计划做一面谈判用的白旗帜,看到白旗也许会让那位有正统派心理的旧镇长觉得好一点。
梅森带回一块白餐巾和一根扫帚柄,用绳子绑成一面旗子。马沙利先生双手持着旗子,走到门前,他叫着:“华塔纳先生!”那扇门忽然打开了,华塔纳先生和三个卫兵出现在门口。
医生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彬彬有礼地向对手敬了一个礼。他的声音有些激动:“先生,我来向您传达我接到的指示。”
这位绅士没有还礼,说:“先生,我暂时先退了。你知道我不是害怕,也不是为了遵从篡权的这个丑恶政府。”他一字一顿地说:“我不愿让人以为我是为共和国服务的,即使一天也不愿意。这就是我最初的动机。”
吃惊的马沙利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华塔纳先生已经疾步走开了,他的随从一直跟着他。消失在广场的那个角落后。
医生得意地朝人群走过去,一走到可以让大家听见他声音的地方,就大声地叫道:“万岁!万岁!共和国全线胜利了!”
可是没有任何人应和他。接着这位医生叫道:“人民自由了,我们独立了,快挺起胸膛来吧!”镇上人的眼睛像一潭死水,都麻木地望着他不说话。他愤慨了,对他们的麻木不仁感到惊讶,他开始搜索一些他能说的,可以起到刺激作用的话,完成他启蒙者的工作。突然,他有了一个灵感,转身对部下梅森说:“少尉,把参议会会议厅的皇帝半身像搬来,顺便把椅子拿来。”很快,部下扛来了那个石膏的拿破仑像,左手提着一张椅子。马沙利先生走到他前面,把椅子放到地上,又把皇帝像放在椅子上。
然后,他退回几步用响亮的声音吆喝:“暴君,你终于倒台了,倒在臭泥巴里,倒在烂泥浆里。法国曾在你的枪炮下喘息,今天,复仇的命运之神把你打倒了。失败和耻辱都是属于你的,普鲁士人的俘虏,你战败了,在你那崩溃的帝国废墟上,年轻光辉的共和国站起来了……”他静静地等待着喝彩声,可是没有一点回音和掌声。那些木然的乡下人一语不发。那座胡须翘得超过了两鬓、头发像理发店广告一样纹丝不乱的半身像,好像凝视着马沙利先生,脸上的微笑隐含着嘲讽。
他和石像一动不动地对视着。他努力思考该怎么办?如何才能煽动这些人,夺得这场公众舆论的胜利?
他的手搁在肚皮上,无意碰到了红腰带上的手枪枪柄。心中的愤怒无处发泄,他拔出了武器,跨前两步向旧君主开了一枪。
子弹在石膏像的脑袋上留下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黑洞,没有任何解气的效果。于是,马沙利先生又朝它开了一枪,石膏像上只是多了一个洞。接着是第三枪,第四枪,连续地射出了余下的三颗子弹。拿破仑像的前额稀烂,可是眼睛、鼻子和胡子的两个尖角仍然完整无损,没有任何变化。
医生气急败坏地一拳打翻了椅子,脚踩到摔在地上的半身像上,以胜利者的姿态转过身向吓傻了的群众嚷道:“让所有的卖国贼都这样毁灭!”
观众被他的行为吓呆了,没有一个人响应他,这位司令官只好对他们喊道:“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说完,自己逃跑似的往家的方向走去。
他刚到家,女仆告诉他,病人已经等他三个多小时了。原来就是那两位既耐心又执着的乡下夫妇。
那老人又开始对他絮叨:“开始时,就像有一些蚂蚁沿着我的腿在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