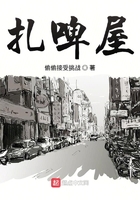1
我十五年没去过韦尔洛涅了。直到今年秋天去朋友塞尔瓦家打猎,才又一次到了那里。当时,他已经把被普鲁士人破坏的城堡修好了。
我非常喜欢那里,世上有许多美丽的风景,给我们的眼睛带来肉感美。有时,我们的思绪会飘到某处森林,某段河流或某个百花盛开的庭院。虽然只在某个好日子里偶尔见一回,它却像春日清晨在街上遇到的那些穿着浅色透明衫的女子的身影一样,在我们的灵魂和肉体内种下难以磨灭和忘怀的欲望,那是一种由失之交臂引起的伤感和幸福。
我爱韦尔洛涅的整个田野:小树林遍布田野,溪流在田间流淌,溪里可以捕到虾、白鲈鱼和鳗鱼,幸福得宛如身在天堂一般。有些地方还可以游个泳。溪流两岸长着茂密的青草,草丛中经常可以看见沙锥鸟的身影。
当天,我带着我的两条猎狗,敏捷得像只山羊一样朝前走着。塞尔瓦正在我右手边的一块苜蓿地里搜寻猎物。我绕过索德尔家森林边上的灌木丛,看到了一座被烧毁的茅屋。突然,我想起1869年最后一次看到它的情景。那时这茅屋还整整齐齐的,旁边架着葡萄棚,门前有许多鸡。现在只剩下没倒塌的破烂骨架,还有什么比这断壁残垣更凄凉的景象呢?我记得有一次累得筋疲力尽时,住在房里的一位老太太请我喝了一杯葡萄酒。当时塞尔瓦给我讲述了她一家人的情况。她的丈夫经常违规打猎,后来被森林警察打死了。她的儿子,我从前也见过,个子瘦高,还没有成家,据说也是个残忍虐杀鸟兽的人。大家把他们一家叫作“蛮子”。这究竟是一个姓呢,还是一个绰号?想起这些事,我就远远地叫了塞尔瓦一声。他迈着大步走过来。我问他:“喂,那所房子里的人现在都怎么样了?”于是,我的好朋友向我说了这个故事。
2
小蛮子三十三岁时,普法战争开始了。他参了军,留下母亲一人。他一点不用为母亲担忧,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有钱。
她单独住在树林边上和村子相隔很远的房子里。她并不害怕。此外,她和那父子俩脾气一样,严肃耿直,长得又高又瘦,没人敢找老人的麻烦。
农家妇人们向来不大让人看到笑容。在乡下,笑是男人们的专属权利!生活的沉重压力,使她们晦暗没有光彩,所以她们心境狭窄。男人们在小酒店里,总算学会了一点热闹的快活劲儿,但他们家里的伙伴却自始至终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她们脸上的肌肉似乎已经忘记了笑的动作。
蛮子大妈在她的茅顶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生活。不久,冬天到了,雪盖满了茅顶。每周她去村子里一次,买点面包和牛肉。
当时大家都说外面有狼,所以她每次出来总背着儿子那支锈了的、枪托也被磨坏的枪。这个高个儿的蛮子大妈看起来不合群:她微微地偻着背,头上戴着黑帽子,在雪里跨着大步慢慢地走,围巾紧紧包住一头谁都没见过的白头发,枪杆子却举得比帽子高。
一天,普鲁士的队伍到了,依据各家的贫富,分派到当地居民家吃住。大家都知道蛮子大妈很有钱,所以她家被派了四个。
那是四个少年,金黄的头发和胡子,蓝眼珠。虽然他们经历了许多辛苦,却依旧长得胖胖的,他们到了这个被占领的国家,却没有盛气凌人。他们住在老太太家里,对她表示感谢,想方设法替她省钱,让她省力。
早上,有人看见四人穿着衬衣围着井洗脸,他们用冰冷刺骨的井水洗着北欧汉子特有的白里透红的肌肉。蛮子大妈正忙着为他们准备菜羹。
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厨房、擦玻璃、劈木柴、削土豆、洗衣裳、料理家务,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自己的妈妈。但是,蛮子大妈忘不了自己的亲生孩子-那个瘦高的、弯钩鼻子、棕色眼睛的、嘴上盖着两撇浓厚髭须的儿子。
每天,她必定向住在家里的普鲁士士兵问:
“你们知道法国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开到哪儿去了吗?我儿子在那个团里呢。”
他们用带德国口音的法语含混不清地回答:“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后来,他们知道了她的忧愁和牵挂。他们家里也有等待他们回家的母亲,于是更加照顾蛮子大妈。她也很疼爱这四个“敌人”。其实,农民都没什么仇恨,这种仇恨仅仅属于上层统治阶级。
至于底层的人们,贫穷已经压得他们透不过气,各种负担都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付出的代价最高。因为人数最多,他们成群地被屠杀;因为最弱小,他们是战争最终的受害者。他们无法了解种种好战的狂热,不了解那种令人振奋的光荣,以及那些鼓动人心的空洞的宣传口号。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无论谁胜谁败,交战国双方同样变得精疲力竭。
当时,人们谈到蛮子大妈家里的四个德国兵,总说:“那四个算找到安身之所了。”一天早上,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人在家,远远地望见乡村邮差向她家走来。走近了,他拿出一封折好的信,她颤颤巍巍地从自己的眼镜盒里取出老花眼镜,读下去:
蛮子太太,非常遗憾这封信将带给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儿子维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差不多被分成了两段。我那时就在旁边,我们在连队里是紧挨在一起的。他从前对我谈到您,说如果他遇到了什么不幸,要我当天就通知您。
我从他的衣袋里取出了他的那只表,预备将来打完仗的时候带给您。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夫齐
这封信是三周前写的。她受了巨大打击,但她并没有哭,木木的呆在那里纹丝不动,似乎连感觉都没有了,一时还没有感到伤心。她暗自对自己说:“现在,维克多被人打死了。”
片刻之后,她的眼泪慢慢涌到眼眶里,悲伤在她心里蔓延。各种难堪的、痛苦的心事,一件件闪现到她头脑里。她以后看不到他了,她的孩子,她那高个儿的儿子,永远看不到了!
丈夫被森林警察打死了,儿子又被普鲁士人打死了,他被炮弹打成了两段!那情景仿佛在她眼前,令人战栗:儿子的脑袋是垂下的,眼睛是张开的,咬着自己两大撇髭须的尖儿,和他从前生气的时候一样……出事以后,他的尸体怎样了?她丈夫的尸首连额头当中那粒枪子被人送回来。她儿子呢,会有人这么做吗?
这时候,一阵嘈杂的说话声传入她的耳朵。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走回来,她赶忙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仔仔细细擦干了泪水,用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的平和态度接待他们。
他们带回一只肥兔子,四个人全笑呵呵的,毫无疑问这是偷来的。他们对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今天可以大饱口福了。
她立刻动手预备午饭,但要宰兔子的时候,她却下不了手-虽然她并不是第一次宰兔子。其中一个兵在兔子耳后来了一拳,兔子就死了。兔子死了,她从它的皮里切下带血的肉。她看见糊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慢慢冷却又渐渐凝固的黏黏的血,她竟从头到脚都在发抖。之后她仿佛看见她那个被打成两段的高个儿儿子,也是浑身鲜红,同那只微微抽搐的兔子一样。吃饭时,她一口也吃不下,四人只顾狼吞虎咽,并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凝视着他们,脑中闪现了一个主意,她脸上保持波澜不惊的神情,他们没有丝毫察觉。
忽然,她问:“你们来了已经一个月了,我连你们的姓名都不知道。”他们懂了她的意思,于是四个人说了自己的姓名。她还叫他们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最后,她把眼镜架在自己的大鼻梁上面,仔细瞧着那些她并不认得的字,然后把纸折好揣在自己的衣袋里,和儿子报丧的信放在一起。
饭吃完了,她对那些兵说:“我来帮你们整理床铺。”于是,她在他们睡的阁楼上搁了许多干草。四人看见她这样反常,不免有些奇怪。她说这样会觉得更暖和,他们就不多想了,也帮着她搬。他们把那些成束的干草堆到碰到了屋顶,他们的寝室四面都被干草围着,又暖又香,睡起来肯定很舒服。
吃晚饭时,有个士兵发现蛮子大妈一点也不吃,问她怎么了。她假装说自己的胃有些痛。随后,她燃起一炉火烘着寒冷的屋子。四个士兵踏上那条每晚使用的梯子,到卧室里准备入睡。
那块当作门的木板关好后,她抽去了上楼的梯子,悄悄打开通到外面的房门,把好些麦秸搬进了厨房。做这一切的时候,她赤着脚在雪里来回走,轻巧得别人什么也听不见。她不时仔细听听那四个睡熟了的士兵响亮而长短不齐的鼾声。
等她确定各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取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燃着之后取出来分开放在另外的麦秸上。随后她走到门外瞧着。不一会儿,熊熊的火光照亮了那所房子的一切。随后整座房子变成一团怕人的炭火,仿佛一座烧得绯红的巨大焖炉。
随后,一阵阵发狂的声音从屋里传来,杂乱的叫嚷,令人心碎的刺耳呼号。随后,做楼门的木板一塌,一阵旋风样的火焰快速冲上阁楼,烧穿了茅顶,如同一个巨大的火把升到了空中。整栋房子成了一片火海。房子里面,除了火花噼啪声,墙壁崩裂和房梁的坠落声,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屋顶轰然下陷,房子被烧成通红的空架子,一阵黑烟升起,大簇火星射向空中。
远处开始敲响一阵钟声。蛮子大妈在烧毁的房子前镇定地一动不动,手里紧紧地握着儿子的那杆枪,防备四个兵有人逃出来。等她确定士兵再也出不来的时候,就把枪扔进了火里,枪声突然响了一下。
这时候,许多人赶来了,有些是农民,有些是普鲁士军人。他们看见蛮子大妈坐在一段树桩上,平静并且微微笑着。一个满口流利法语的普鲁士军官问她:“您家里那些士兵到哪儿去了?”她抬起皮包骨的胳膊指着正在熄灭的红灰,高声回答:“在那里!”
大家聚过来围住她。那个普鲁士人问:“这场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她回答:“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她的话,觉得这场大火使她变得神志不清了。她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讲给围观的人听,从收到那封信,一直到听见那些和房子一起被烧的人最后的叫喊。
说完后,她从衣袋里取了两张纸。戴起眼镜,对着燃烧的余光分辨这两张纸,随后她拿起一张,说道:“这张是给维克多报丧的。”接着,她又拿起另外一张,斜着脑袋向那堆残火一指:“这张,是他们的姓名,可以写信通知他们的家里。”她不紧不慢把这张白纸交给那军官。他此时正抓住她的双肩,防止她逃跑,她接着说:“您要写清这件事的始末,告诉他们的父母这是我干的。我在娘家的姓名是默里多娃·西蒙,到了夫家人们叫我蛮子大妈。请您不要忘了。”
军官用德国话下了命令。士兵们抓住她,推搡到那堵依然燃烧的墙边。随后,十二个兵迅速地在她对面排好队,距离大概二十米。她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她很清楚,她在专心等待。
一道口令过后,一长串枪声骤然响起。响完之后,又接了几声迟放的单响。
蛮子大妈并没有完全贴在地上。她跪在地上,上身却依然直立着,像双腿被人砍了。
军官走到她跟前,看到她几乎被打成了两段,在她几近僵硬的手里,依然握着那页满是血迹的报丧信。
我的朋友塞尔瓦接着说:“后来,普鲁士人为了报复就毁了我的古堡。”我默默无语,想着那烧死在火里的四个孩子的母亲们。接着,又想到那个靠着墙被人枪毙的蛮子大妈残忍而又有些悲壮的行为。最后,我弯腰拾了一片小石头,上面还有那场大火留下的烟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