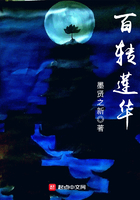却说霍雨儿负着晕迷的霍风乘夜沿着小路奔行,其实这道路就从莽山穿过,通往不知名的海边。
这段目前仍是在莽山剑派的势力范围之内,寻常盗贼倒也不敢在这里撒野,而大型猛兽则早已被历代历练的莽山剑派弟子杀了个净尽,换成了派中的贡献点,所以霍雨儿这阵子跑得是相当地安全。
等天快蒙蒙亮时,她已近于跑了一夜,自己也不知跑了多远。
霍风还在沉睡,只是鼾声轻了一些。远处路的尽头好像是地势突然有些拔高,因没到近前,瞧得不甚清楚,倒也不像死路的样子。
时间稍倒回一个时辰前,却说这被霍雨儿送到鬼门关前又放回来的秦德利,终是昏迷大半夜后醒转了来。醒来后他浑身无处不痛,而且一阵脑袋发炸。回想起霍雨儿那冷得似没有感情的双眼,心中还是一阵后怕,惊恐不已。
身体动不了,秦德利也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处境。再换各个角度试了试,却是发现了霍雨儿绳结的弱点。她这貌似绑了里三层外三层,但关键口儿的打结法却不是很老练。秦德利三转五绕,用了小半刻,竟将身体由绳子中间脱了出来。这场景如果叫老秋之类老水手见了,可能能把霍雨儿骂到跳海。
闲话不多说,秦德利脱身后,既庆幸对方毕竟心还不够黑,下手也不够狠,但这到手的富贵就这么飞了,心里也着实失落不甘。
“还有没有办法?”他心下嘀咕,如此就不由得估量些个路途状况、时辰方位,这么一寻思,倒是有了那么一点儿的预计,再看向里院,秦德利这脑里还真是突然间跳出了个主意,一个比迷药更残忍的主意。他也不犹豫,飞身进了后院,里面向右一转是个栅栏,内中有几个动物,见秦德利过来,都兴奋地奔了来。
秦德利作为正牌杂役弟子,喂狗也是一项基本功课。而这里的狗又有些与众不同,它们乃是门派有专人秘法培养的独有品种。这种狗据说有某种异兽的血统,比常狗快上十倍,凶上百倍!且长于韧性,据说跑上一天追击猎物都可做到。一旦培养好后,又异常听主人的话,而对主人以外的其他动物,包括人,都极端残忍。
这种狗有两个用途,一个是给门内中级弟子作陪练,也做一个考试的科目,既锻炼弟子的武功能力,又锻炼血性和胆量。另一个用途是追猎山中的一种异鹿。这种鹿的茸角和血是门派中一种秘制丹药的最重要基材,另外浑身上下另有多处部位都有很好的药用。而要捕猎到这种鹿,只有用这种狗才能跟得上它们的速度和耐力。
话不多说,秦德利挑了五条最壮硕的狗,准确说,应该叫獒兽,随着他来到了院里,又进了原来霍风睡的房间。地上还留着霍风呕吐的大滩污物。秦德利喝令几只獒兽去嗅了嗅这污物气味,然后一个喝叱,其中四条就犹如闪电一般倏忽冲出了山门,转眼间就跑得没有影儿了。这污物气味甚重,于这些獒兽来说几乎不用在识别气味上多用一丁点儿的时间,一路只循着霍雨儿夜晚跑过的路狂奔而去……
如果能从天上看,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的距离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拉近,又拉近……秦德利则索性关了山门,在后面跟着最后一只獒兽,不紧不慢地向这个方向从容而来。
起初,霍雨儿丝毫未察觉身后有追兵的迹象,倒是前方的路拦住了她。仔细看了这路,她吸了口凉气,因为实在是太奇特了。只见前方是一处向左右绵延甚长的绝壑,对面很高,而且边沿向自己这边斜斜地伸来,顶上的最前端几乎已伸到了自己这一面沟壑边缘的正上方。而自己走的路,离前面尽头已是只有十丈许。路正中由对面上方垂了一条铁索下来,如攀了这根铁索,向上爬,则爬过约莫五丈高之后,就可以达到对面。而看清了这怪路之后,霍雨儿便也听到了后方的异动!
是风声,是猛兽迅疾奔跑所带出的特有的呼哨声!因为这种声音她以前听过!那还是在她小时,有一次父亲和几个水手出去打猎,她死缠着跟了去。而就是这次,一头剑齿巨豹将这支队伍几乎屠杀净尽,最后只有父亲、她和一名老水手逃得了性命。而这种野兽狂奔的风声,就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一般,跟随着当时的这支如被诅咒的队伍。现在,这个噩梦又来了!而且,这次,这样的猛兽,是四只!快如闪电,高如牛犊,模样奇丑,嘴裂到张开可以装下一个成人的头!
霍雨儿瞥眼看见它们的瞬间,浑身的寒毛都炸了!“——决不可力敌!”她于急忙之中暗道,确是一下子就判断出了实力的对比。
不知哪来的气力,霍雨儿爆发出几乎原有的二倍的速度向前方的铁索狂窜!可獒兽更快!看不清动作的一个起落,最先一只的前爪就快够到霍风的背后了。也许是被后方巨大的危机所震动,霍风就在这时,醒了。
霍雨儿不再看身后,因为她深知,看不但没有用,反而会延缓自己的动作,这时只有爆发出最快的速度,才可能在这与死神的比赛中胜出!她脚尖一个对地狠踏!力道大得几乎将那小块的地面都踩得裂了!背负着刚醒来的霍风向前上方蹿起,左手单手前够!已是牢牢地抓住了铁索。右手则仍是抓着交叉在自己喉间的弟弟的两只小臂。
而就在霍雨儿以为马上就能将腿盘上铁链时,突然感觉后背如有一块两三百斤的大石压将下来!却是那条最快的獒兽一个蹿身跃起来,双爪搭上了霍风的双肩,爪上尖刺突出,插在了他肩上的肌肉之中!侧头一口就将上、下两排有力的尖齿结结实实地咬在了他的脖颈!一股冲鼻的犬臭味从脑后方直传过来,加之獒兽喉间的呜呼喘气声也在后脑处响起,霍雨儿浑身汗毛又炸!
霍风颈间鲜血也瞬间爆出,部分流进獒兽喉间,在这新鲜热血的刺激下,獒兽更加狂暴,眼睛已是刹时瞪得血红!另一些血则喷溅到了霍雨儿的脖颈上,而这时两人一兽的重量则把霍雨儿本是紧抓铁链的手,硬是猛拽得向下沉了一尺!
手上传来火辣辣的痛,想是表皮已被磨破。两人一兽的身躯太重,直拉着铁链向前猛然荡过。第二只獒兽此时也几乎是要腾空跃起,参加这场空中的杀戮盛宴!
还没来得及感受颈间弟弟流出的热血和在下坠中找到出路的霍雨儿知道,今天,是逃不出去了,死在恶狗口中已成宿命,心中一股巨大的悲哀好像要撑破肚腹身躯……
可就在这当儿,霍雨儿的右手背上又传来了钻心的痛!痛得她本能地甩手,随之手上的痛就立刻轻了,但,脖子上也松了,好像一块原本压迫自己的大石瞬间脱开了,那压得她几乎抓不住铁链的二、三百斤的重量,忽然离开了她的身体,但同时,也好像是什么重要已极的东西随着刚刚骤然减轻的重量一同离去了……
霍雨儿的背上一凉,清凉的初冬的风扫过她早已被汗水浸透的背衣,后背一片冰凉。霍雨儿突然间得到了一刻难以想象的轻松,她下意识地双手一搭铁链,虽铁链在摆荡之中,但她身轻力健,就是顺着斜的铁链,也是合身向上一蹿,已是到了离地二丈多高,只要再向上攀几下,几乎已可够到上面地面的边沿。
这獒兽再猛,也是跳不到这么地高。
还不等欢喜,霍雨儿才发现脚下正下方,几只獒兽在欢吠中呜咽,这是口含血肉的欢快的哼叫,这是獒兽们幸福的高峰时刻。这些獒兽的呜咽声霍雨儿清楚地记得,便是在那莽山剑派外门的院子里听过,当时她和它们只隔了一堵墙。这些狗是哪里来的已经是昭然若揭。
突有一声尖嚎透出,直向上方激荡而来:“走啊!姐!——”还没喊完整,就蓦地被一阵犬牙嚼碎骨骼的声音彻底地截断了……
霍雨儿终于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残酷的现实重重地一击,击得她双眼发黑,几乎松脱了铁链!而心底里逐渐升腾起一阵很大很大的悔恨和悲伤,混着滔天的怒意,升上了脸面,这股倔强的愤怒又使得她的手扣住铁链扣得更紧,以至于指关节处已经白得快要透明!
一股咸腥味从喉间涌上来,如洪水般的眼泪冲出了眼眶,冲出鼻腔,嗬嗬地,她只呼出不似人声的声响。
下方群狗在撕咬吞咽的,是她曾在娘的肚里面贴面在一起几个月的一胎的亲兄弟。而这个局面又是自己的错误一手造成,当初就应该杀了那个恶魔,而她却没有下去手,如今,他那边放出的恶狗在啃吃她的至亲弟弟,而她却挂在这半空,什么也做不了……
下去与他同死?
除了让狗吃得更饱些以外毫无意义。命运以这种方式夺走了自己最后一个亲人,这种方式怎可接受?而刚才明明是弟弟咬开了自己的手,放开了自己的一条生路,去用自己的肉、骨、血和内脏,去向恶犬赎买姐姐生还的希望……
“霍雨儿,你还有资格下去死吗?”她想道,一字一血。
巨大的悲愤堵得霍雨儿几近窒息,她头在嗡鸣,什么也不能再想,泪也似乎是断了来源的泉,慢慢地干了。心的一部分好像也空了,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好像也死了。霍雨儿仍吊在空中,微微摆荡,如同挂在初冬藤上等待风干的葫芦,不可能重新生长,也倔强地不会掉落……
下面猛犬的欢宴似乎要进入尾声,但它们对霍风尸体的兴趣,仍然比对活着的挂在半空铁链上的霍雨儿的更大。霍雨儿无声地哭泣,如同在哭出的是血,汩汩地,她已看不清东西,眼中除了灰色的混沌外,再无他物。
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半个时辰,霍雨儿似乎一部机械般地,开始蠕动了,向上一寸一寸地往上拽自己的身体,好像婴儿通过产道般费力,一下一下,终于,右手勾上了地面,然后是左手,之后是双手用力,右肘上翻,随即左肘,然后胸部压上了地面。
喘了会儿气,她的右腿跨上,腿臂又双双用力,便将左腿和全身都拉上了地面。霍雨儿面无表情,如泥塑般又回转身体,仍是跪趴在地上,似乎调动起全身残余的气力,一只手抓着铁链,向上拉,很重,继续,另一只手又过来拉……这样,一下,一下,铁链越来越多地拉上了这边地面。又是一会儿,已经全部拉上来了。
霍雨儿吐出口中最后感觉的一点气息之后,就昏死了过去。
……
不知何时,一大片细密的凉意固执地敲打着昏沉中的她,好一阵子,她才意识到,是天下雨了,初冬日子里的雨。
雨势不小,可是霍雨儿只感到周身剧痛,所有关节仿佛突然间都塞进了火炭,动一下任何部位都像是要被烧红的烙铁烙一下一般。脑中混酱,口中是咸的苦的,仿佛喝过海水。身体内感觉到处是炭,但偏又是一股由内而外彻骨的寒!如此的矛盾,但偏又如此和谐地混在一起,使得霍雨儿像一块在火上烤着的冰块。
好在下到身上的雨,似带着一点点凉,也有一丝丝的暖,冲起了地上的土味,让人不由想起春天在还没有冒出草的土地上奔跑时闻到的气息。
……
“弟弟死了。”霍雨儿艰难地想起来了可以翻找到的第一条回忆。
“死在狗群。”
“定是那个秦德利放的狗。”
“那恶人当是醒了,却不知怎么把狗放了出来……”
“都是因为我的一时心软、仁慈,没杀了他。要是杀了他,就没有这个结果了……”
“是我的错误,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可我犯的错,害的却是弟弟你的命!我为什么这么蠢、这么笨?为什么这么无能的我不去死?却让从没做过坏事,只会对我好的你去死?……”
“秦德利明明提醒过我,他们有狗,还能吃人,为什么不给这个恶魔一刀?这一刀没给他,其实就是给了弟弟!我怎么这么蠢啊?我想过不能心软,可到时却下不了手,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想着想着,哇地一声,霍雨儿还是哭出来了。
她渐渐从俯卧的位置,用肘撑起胸口、脖子,逐渐抬起了头,在密集的大滴的雨中,她一点点跪坐起来,雨势又大了些,还开始扫过满是寒意的风,脸旁仿佛有些冰粒做的鞭子,在细细地抽打。
无边的悔恨炙烤得她几欲疯狂,霍雨儿蓦地仰头向天,口大大张开,发出一声声不似人声的嘶吼:“天,你惩罚我,我有罪,你拿走我的妈妈,拿走我的爸爸,你拿走我的家人,又拿走我的弟弟。你看还有什么可以拿,你拿吧,你拿啊!你拿啊!”
头似再无力向天,便是垂了下来,仍哭道:
“这人,活着就这么难的吗?”
“我和弟弟只是想活下去,活下去。我们不配吗?”
她的头又是昂起,向天嘶吼:
“你回答我,你说啊!嗬嗬”
……
然后,好像用光了力气,霍雨儿无力地向斜前歪着软倒了下来,侧身跪趴在了泥地上。
泥上满是水洼。
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倔强狠劲,霍雨儿还是动了,仆了身体开始一下一下地往前爬,像一只垂死的蟾蜍,无目标,也无速度地向前爬,她唯一的意识是,“我可能就要死了,但就算是死,也不能像一只猫那样蜷着死去,要像蛇那样坚持爬行,血不流尽,不可低头,只要一口气还在,就不能停止,我除仇恨,再无所有,要除掉仇恨,只有向前走,不能停……“
可是浑身的冰冷感更甚,她强烈地开始抖起来,额头实已比火还烫,她终于冷得哆嗦成一团,一个小姑娘,只能缩成小小的一团,在大雨中侧着身,蜷着。她好像母体里的婴儿一样蜷着。她也好像终要陷进一个梦,一个没有痛苦,没有仇恨,没有失去,没有挣扎的梦中,只有这一刻,她才有了一点如释重负的解脱、幸福和欣慰感。
“我要死了吗?……”这是霍雨儿再次昏过去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她终是昏死在这雨中的地上,如一条被剥去了鳞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