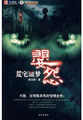阿茫对陈可镜的决定不支持也不反对,万事开头难,他的最大担心是凭陈可镜一家人的力量,能否在那种相当艰苦、近乎蛮荒的地方生存下来。
老实说,这时的陈可镜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乐坏了,他不可能去想那些将要面临的困难,更何况,任何的困难对陈可镜来说实在不算什么,陈可镜穷苦出身,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什么苦没有受过?还在国内时,有一年,他去给村里的一个大东家割稻子,一个人一天割两亩,从天才刚刚亮开始,一直割到太阳落下山,月亮升起来,一整天时间,连腰都不直一下。在他们村子里,还从来没有一个人一天可以放倒两亩稻子的人。因此,陈可镜在村里还落了一个绰号,叫陈二亩。当然,就陈可镜本身来讲,到两亩地的稻子割完,那个累呀,感觉差不多腰都已经断了。
陈可镜是下定决心想要开发那片富庶的土地了。这天到了下半夜,陈可镜还依然睡不着,他兴奋极了,他已经在心里为将来描绘了一幅幅美丽的蓝图,在那幅蓝图里,有蓝天,有白云,有奔跑的牛羊马群,有一望无际、随风起舞的稻浪,还有成片成片的橡胶树,油棕和胡椒。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向李清华讲述着描绘着那一幅幅蓝图。他告诉李清华,二叔在信里告诉他的金矿他是找不到了,其实也一点不符合现实,因为,从本质上说,他和李清华都还是农民,作为一个农民,他们必须现实点,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换上什么衣服,他们仍然得记住自己还是一个农民,这一点是永远无法改变,也不能够忘记的。既然是农民,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土地,一个农民要是没有了自己的土地,那还叫什么农民?而现在,土地就在眼前了,只要你肯付出劳动,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那是在自己的国家连做梦都不可能得到的,有这么好的机会,他们为什么不去努力呢?他没完没了说着,越说越激动,就像是那一切都已经变成现实了似的。
李清华呢,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顺从就是美德。作为妻子的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男人的性格。当自己的男人一旦下定决心,想要成就某件事时,你就是九头牛也休想把他给拉回来了。眼下,她只是瞅着自己的男人笑着,笑得非常开心,非常灿烂,这是他们夫妻俩来南洋后,她第一次心情这么的好。男人的心情好,她的心情也跟着好了。不过,开心过后,她仍然怀有一丝隐隐的担忧,她想不明白那样肥沃的土地为什么会没人要,她不停地问着丈夫南洋政府是不是真的鼓励大家去那里开发,要是花力气开发了,政府又给收回去那该怎么办?那不是白白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了?
陈可镜这时心情极好,所以他有足够的耐心慢慢地向妻子作解释,他让李清华不要有过多的担心,他说,政府鼓励到沙捞越州自己开发那片荒地是天下皆知的事,只是刚刚到南洋的中国人不知道罢了,政府现在担心的是没有人去那里开发,作为他们来说,说干就干好了,完全没必要怕这怕那,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
两天后,陈可镜便携妻小去了诗巫开发土地。其实,坦白地说,到那片荒地上开发的陈可镜并不是第一家,在他们之前,整个拉让江流域,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中国人拖儿带女先行到达那里,盖上草房,挖出水井,在那茫茫无际的荒地上安家了。就在陈可镜一家人到达荒地的那天,便有一群中国人也赶到那里,加入了开发土地的行列。陈可镜看得出来,那都是一些农民,他们骨骼粗壮,皮肤黝黑,衣衫缀满了补丁,甚至有点破烂。他们的所有家当就是在肩上挑着的那些东西:锄头,镰刀,箩筐,水桶和一床被子。他们的到来,让陈可镜除了感到亲切外,还让他吃了一惊,心里想,他们比自己还精呀!他们究竟从哪得到的消息呢?便想还好自己果断,要是犹豫不决,就耽误大事了。
随后,陈可镜和李清华,夫妻俩带着山子,在那片大草地上找了一个干燥、向阳、背风的地方,用荒野上现成的灌木和苇草盖起了一座草房。草房盖好后,陈可镜站在门前欣赏着,越看越满意,心里想,到哪里去找这样美妙的地方呢?看看吧,屋子后头有树,屋子前头就是拉让江,就是沙捞越最大的河流,清澈透明的江水从屋子前滚滚流过。江两岸,是极目千里的肥沃的土地。也就是说,那里是他的庄园,现在,他已经是这片庄园的主人了。
夜里,躺在自己新盖起的草房里,到处闻得到苇草散发出的阵阵芳香,听着拉让江的江水哗啦啦地响,陈可镜陶醉其中,觉得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这里有的是地,你可以栽种芭蕉,菜蔬,水稻,你爱种什么就种什么。只要你耕耘了,你就会有收获。如果你想尝尝鱼腥,随时都可以下江里捕捞去,江里有的是鱼虾。想到这,陈可镜微微笑了。到南洋几年了,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过。这时,他忽然看见李清华在默默垂泪。窗外,旷野上清冷的月光泻进来,照得她的泪水在闪闪发光。陈可镜并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哭起来,女人真让人搞不懂,他以为妻子在后悔跟他来这里过苦的日子。
而事实上,陈可镜完全想错了,李清华是一个非常顺从的女人,嫁鸡随鸡的思想早已在她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想铲除也铲除不掉。自己的丈夫既然选择了这里,她和孩子不可能不跟着来。她之所以掉眼泪,完全是为自己到南洋两年多来,终于第一次住上了自己的房子高兴的。尽管,这个房子是如此的简陋,或者说简直不能叫房子,但它毕竟是属于自己的,是自己和自己的男人一根木头,一把草,辛辛苦苦盖起来的。睡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心里踏实,自在,没有那种寄人篱下的困窘和不安。于是一种幸福感从她的心底弥漫开来,充斥着她的整个身心。她激动得掉泪了,她把自己的男人揽在了身边,动情地说,多好的一个地方呀!其实咱们早就该来了,咱们为什么到了现在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呢?以后,我们什么地方也不要去了,永远就在这安家。
陈可镜说,你不后悔跟我来这里了?
李清华说,后悔什么呀!你看那么多的中国人都来了,他们还不都是冲着这片好土地来的?
陈可镜说,咱老家那些没地种的穷苦乡亲要是知道有这么一大片土地荒着,恐怕半夜都得扛起背包往南洋跑了。
李清华说,他们在家里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会愿意来的;就算愿意来,他们出得起到南洋的盘缠吗?你这一说我倒想起黄泽如和香香他们,要是他们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开发就好了。
其实,李清华的这些话是在替陈可镜说的,李清华说出了陈可镜心里想要说的话。陈可镜平日最讲义气,为了朋友,他可以为之肝脑涂地,两肋插刀。更何况,黄泽如这个朋友对他来说还不单单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朋友,他们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结成的生死情谊,简直比亲兄弟还要亲,不管到什么时候,他也不可能把他给忘了。现在,听李清华这样说,心里就越发想着他们。但是,李清华才说过,就又开始在心里担心了,她知道,黄泽如毕竟和陈可镜不一样,黄泽如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读书人,而开荒垦殖完全是农民们干的事,他吃得了这个苦吗?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给了陈可镜,陈可镜却认为她过于担心了,在他看来,进士也好,举人也好,哪怕你在中国是一个皇帝,也只能说那是在中国的事。到了南洋,到了人家的国家,你就只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侨民,是沦落天涯海角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的身份已经不再高贵了。陈可镜说,这一点,黄泽如非常有自知之明,早就已经做到了,不管是来南洋的路上,还是中间两人所共同经历的种种磨难,他觉得他已经找不出黄泽如身上哪怕一丁点举人的影子了。环境能够改变人,在那样的环境中,你黄泽如去向那些海盗说自己在中国是一个举人,岂不是笑话?
陈可镜他们这边还在想着要不要叫黄泽如他们一起来垦荒,黄泽如却已经带着一家子人直奔诗巫来了。那是一年后的一天正午,那时,陈可镜夫妇已经在荒地上开出了十几亩的水田和旱地,种上的稻子和芭蕉,大获丰收。陈可镜忽听有人在不远的地方喊自己的名字,心里想,在这样的一个鬼地方还会有谁能够认识自己呢?抬头一看,只见门口不远处大大小小站着几个人,除了小孩外,两个大人背上都扛着大包小包的。看得出他们是从远道来的。陈可镜看着看着,不禁激动地大声喊起来,黄泽如!我还没去找你呢,你小子倒自己找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