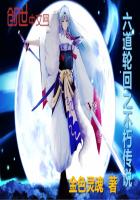秋水夜露,一大清早,宣仪殿水榭前的菊花都开了,浅浅的鹅黄色还带着露水。
内侍主管张平苦着脸站在水榭前,对面前的男子十分为难。
“实在不行啊丞相大人,君上命奴才守门,除了君上之外谁都不准进,就算您有君上口谕也不行。”
面前的男子正值壮年,身穿鹊灰色绣银丝的官袍,国字脸显得格外忠厚老实,此时说话也是温温吞吞的。
这人正是燕国丞相宋自衡。
“君上在朝前和岳大人说话,本相先行来一步而已。”
他见张平着实为难的样子,了然点头,颇为好说话。
“无碍,那本相在这里等着君上便是。”
像张平这类从底下一步一步爬上总管位置的,对朝前的事不懂不论,但时常接触这些大臣,对这种毫无官威不摆架子的人格外有好感。平日里见面也是客气的很。
“怠慢丞相大人了。”说着,张平让人端了个椅子,又亲手奉了茶来。
“多谢多谢。”宋自衡客气道,坐下之后品了茶,像是随意与他言。
“近日君上好像心神不宁的,听说总爱往御花园跑?”
张平也是个人精,听到这话微微一顿,立刻谄媚的笑了笑。
“嗐,君上的行程哪是我们能知道的。”
“不过……”他话锋一转,“近日魏明容不再入宣仪殿,君上好像也不怎么去暮日斋了。”
宋自衡一挑眉,魏明容要失宠了?
“不过谁知道呢,君上的心在哪,奴才们可不敢乱猜。”
“我等做臣下的,也不敢乱猜。”宋自衡也笑了笑,端着茶缓缓喝了一口。
约摸着大半个时辰后,李弘承才从朝前款款而来,和宋自衡入了宣仪殿。
而与此同时,御花园中。
菊花也是一朵朵,如少女一般含羞待放,在暖阳的照耀下格外好看。
碧水扶着魏秋月的手臂,缓步走在石子小路上。
“果然还是御花园的空气好,近日主子身子倦怠,就该出来走动走动。”
魏秋月抚了抚袖口,春蓝色的衣裙在这百花之中,有着清雅淡薄的姿态,令人眼前一亮。
抱着画箱的李逸之便是这样认为。
哪怕驻足远远的地方,也无法忽视这个女子举手投足间的美丽动人。
“主子,是梁王殿下。”碧水低声道。
魏秋月回眸望去,看见的便是傻傻站在远处的李逸之,她身姿一顿,微微笑了起来。
“这片瑶台玉凤长的很好,我们在这亭子里坐一会吧。”
月白色的花瓣中捧着浅黄的花蕊,如天鹅起舞的姿态,瑶台玉凤一直都是菊中的翘楚。
见她止了步子,李逸之也无法当做视而不见,低头理了理衣衫,缓缓走到了亭中。
“妾身见过梁王殿下。”
“魏明容……免礼。”李逸之低头,攥紧了袖中的手。
距离魏秋月与他初见已有月余,若不是前几日知道了她就是暮日斋的正宫明容,只怕李逸之此时已经向李弘承递折子纳她为妾了。
初识便是一见钟情,日日情深。直到前日私会时,李逸之酝酿许久才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本以为可以抱得美人归,却不想听到她温软浅声道。
“抱歉一直让殿下误会……妾其实……是魏秋月。”
燕君的魏秋月,魏明容。
李逸之一向对画画之外的人或事不感冒,只有那一日他回到府中,拿着画笔愣坐了一整日。
请安之后,两人之间便是良久的沉默。
碧水让宫人拿了些糕点放在两人面前的石桌上,魏秋月拿起一块黄蓉糕咬了一口。脸色却是突然一变,俯身将其吐了出来。
“月儿!”
李逸之下意识的唤了她的名字,才发觉自己不该再这样叫,站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要该怎么办。
也幸好此时御花园中人少,远远的有宫人在打扫,并没有发现这里的异样。
“我没事。”魏秋月起身喝了一口茶,压下腹中不适,冲他笑了笑,只是脸色苍白的很。
“是我的老毛病罢了,还请王爷不要声张。”
李逸之皱着眉看她,只是还是担心。
“我不声张,但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了。”
魏秋月看了眼碧水,后者点了点头,起身站的远了些,亭中便只剩下两人。
“我不想骗你,你也不要问我好不好。”魏秋月抬头看向他,额间的美人痣因着病色,都有些黯然。
李逸之抬了抬手想抚上去,手落半空顿了顿,又收了回来。
“好。”
他垂眸,对上魏秋月的一双含着水汽的眼睛,下一瞬她却伸手捏住了他的衣角,绣着鹤鸟纹的长衫,在白皙的手指间微微荡着。
“殿下还可以帮妾一个忙吗?”
李逸之唇角微微珉起,每一次她露出这个表情,都是求他帮忙。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每次,他都不忍拒绝。
“好。”
魏秋月冲他笑了笑,苍白的唇畔微微扬起。
这满园的瑶台玉凤,随风轻轻摇着枝叶,沙沙声远远地遮掩了亭中人的话语。
叶随风而落,抬眼便是宣仪殿。
“关于燕昌侯的事,君上打算怎么决断?”
宋自衡躬身立在殿中,颇为苦恼的样子。
燕昌侯一夜之间失去爱子,疯了一般抓住靖王不放,一口咬定就是他纵崔修元杀害自己儿子的。
但又没有证据。
李暄本来还与他辩驳两句,但见他失去理智油盐不进的样子,便直接甩袖离去,这两日都称病不上朝。
靖王府被李暄自己的家丁护的死死的,燕昌侯又无法闯进去抓崔修元入刑部大牢,这几日天天跪在朝前哭,请李弘承给他住持公道。
“李朝宗死在了靖王府边上的小巷里,孤觉得这确实不像是兄长的手笔。”
李弘承捏着茶盏若有所思。
以他对李暄的了解,若是李暄想要一人死,要么直接与他对峙,列出条条罪行直接处死。要么,就会撇清和自己的关系下手,断不会让人怀疑到他的头上。
要么兵不血刃杀人无形,要么手起刀落伏尸百万。
这是兄长的一贯作风。
“恕臣多嘴,”宋自衡俯着腰,微微抬眼看着上位年轻的君王,道。
“靖王殿下的心思,君上真的明白吗?”
他说,“若这就是殿下故意而为之呢?君上,靖王手握的户部,和燕昌侯手下的工部早就水火不容了,这是朝前百官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工部掌管建屋修渠,尤其是这几年燕宫的维护修缮,都是工部一手负责完成。工程浩大,可不得需要银两支撑。
而户部尚书则是李暄一手提上来的毛头小子,天天眯着老鼠眼,抠唆的不得了,咬着钱眼就跟自己家似的,尤其是燕昌侯要钱的折子。
据说是看一个扔一个,见人就嘀咕工部的人要债比君上还多。
日日走在路上和燕昌侯见面都恨不得互相抄家伙打一架。
“嗯……”李弘承不说话了,伸手放下的茶盏,抿唇想了又想。
宋自衡直起身笑了笑,轻声道了句。
“并非臣偏颇与谁,只是想提醒君上一句,那靖王殿下手中,可还有兵部呢。”
李弘承指尖一顿。
这个他当然知道,早在李暄封王的时候,就瞄上了兵部,在先王不在意的时候一步一步不动声色的爬上了禁军统领一职,就算是先王恍悟他的野心,将他扔到周国去,也是棋差一招。
届时李暄早已暗中掌握了兵部上下,再回燕国时,就领着兵部那点人,和燕宫整个禁军,一举推他上位。
连君仪的五万守备军都没有惊动。
李弘承即位之后,李暄将禁军全权交给了李遗和他的手里,拿捏着户部。
如此算来,李暄手里的人其实不多。
但一个兵部一个户部,兵权财政,皆是燕国命脉。
抓的死死的,让李弘承动也不敢动。
“李遗,去靖王府。”李弘承从腰间扔出一块刻着滕鸟的白玉腰牌,面无表情道。
“抓崔鹄下狱。”
“是。”李遗凌空接住了腰牌,立刻令人出宫。
直到宋自衡走出了宣仪殿,自顾理了理衣襟。殿外他的随侍一声不响的跟在他身后,低眸垂首,发丝遮住了眼底那一道狰狞的刀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