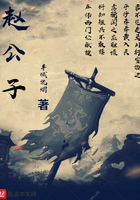我拿着珍珠给我的膏药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公子已经换过衣服,散着头发坐在床上出神。他向我伸手:“过来。”
我站在公子面前。他拿起我的手端详,“还痛吗?”
“不碰就不疼了。”
公子叹了口气,引着我到桌前坐下。桌上已经放好了纱布,他把白瓷瓶旋开,先给我上药。
药膏里大约搀着薄荷。指尖一凉,那隐隐约约的痛感也就减轻了。我盯着自己的手指,无端想起端阳节娘拿凤仙花给我染红指甲的情形来。
“院子里有凤仙花吗?”我问。
公子正拿窄窄的纱布给我裹指尖,闻言想了一想,问:“我不大记得。你喜欢凤仙花?”
“凤仙花可以染指甲。”
公子笑了一下,那笑意转瞬即逝。“明儿你瞧瞧,若没有,我叫人种。”
“那也太费事了。”我说。
“拿来染指甲,大约也不算什么名贵的花?”
我笑问:“那我若要拿牡丹花染指甲呢?”
公子道:“那就种牡丹花。”他随即带着些怀疑问我:“牡丹也能染指甲吗?”
我笑道:“诓你的,牡丹才不能呢。”
受了伤的手指被包扎起来后,我想起该说说夫人的事,可又不知道公子是否知情、告诉他夫人的心事是否妥帖。正左右为难,公子看出了我的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还是决心瞒下来,让夫人和主君同他谈。“我把事情告诉夫人知道,夫人说主君今日晚些才回来,等他们商议过再决断。明日先不去学堂。”
公子没说话。门开了,周妈妈进来道:“食盒送到了,公子先用饭罢?”她看了眼我的手,等我走过去拉我一下,说:“手不方便,就别伺候了。夫人那边赏了菜下来,吩咐不用去磕头。你先回去吃饭,今儿也累了。”
晚些时候公子说了要我睡在外间,周妈妈没说什么,只是替我铺好了被褥。厨房送来两碗安神汤,虽然不大好喝,但毕竟是夫人的好意,我还是喝完了。
周妈妈熄烛走后我就听到内室窸窸窣窣有动静。果然公子走了出来,小声说:“我有些睡不着。”
房里烧了地龙,因此并不很冷。我披了件小袄就下来,同他坐在床边的脚踏上,靠着炭盆。为了安神,今夜还特意埋了块香,闻着就让人心静。
“公子在想什么?”
公子并不答言,只是盯着炭盆里那微弱的红光。就在我抱着膝盖快要睡着的时候,他问我:“今日你怕不怕?”
我把脸倚在手臂上,迷迷糊糊道:“自然是怕的。要是阿福他们没到,咱们就要进池子了,好冷的。”
“你要是不来就没事了,后不后悔?”
我一个激灵醒过来了。想说后悔,原本十个指头就笨,现在伤了八个,又有一阵不能练针线,只怕生疏了越做越丑;但这话说了公子一定不高兴,想想还是不说的好。“我若不来,公子被他们伤了怎么办?何况公子也不能总被他们欺负呀。”
怕惊动屋外值夜的婆子,我没有点灯,因此仅凭炭火的光看不清公子神情。为了离炭盆近一些,他的肩挨着我的,我甚至能听到他浅浅的呼吸声。
“多谢你。”
我笑了一下。“你怎么同我这样客气?只可惜你那个扇套子我还没做好,这趟家去还特特地让我娘教了一种新绣法呢,过几日就要忘了。”
“无妨,你随便做做,横竖我也不去什么地方。”
“公子意思是我做的东西拿不出去吗?”
他笑了。“我可没有说。”
听到公子笑,我才觉得松了口气。他不说话,屋子里静极了;困意一阵阵袭来,我渐渐坐不稳,身子一晃就往前栽。
“当心!”公子眼疾手快拦住了我,使我免于扑入炭盆而毁容的危险。他又好气又好笑,说:“困了就说,你可把我吓一跳。去睡吧。”
“公子不是睡不着吗?”我抬头看他。
公子拉我起来,笑道:“我躺躺就睡着了。”
我躺进被窝里,公子甚至给我掖了被角——就像我们怕他着凉一样。我小小打了个哈欠,闭上了眼睛。朦胧中我听到脚步声逐渐远去,随后就是长久的满室寂然。
晨省的时候主君也在。他与夫人都面色憔悴,而夫人擦了粉,只瞧得出眼睛有些肿。
吃毕早饭,夫人就道:“你们出去罢。”顿了顿,又说,“冬香留下。”
珍珠带着丫鬟们出去,亲自掩了门守在外面。我惴惴不安地垂首,想着夫人主君还是不要说太多隐私事为好——知道主家太多秘辛可不是好事。
隔了一夜,指甲底下的瘀血早已凝固发暗,严重的几只甚至带紫;而纱布又太不便利,我洗漱时便拆去了。因此夫人叫我抬手时,我有些抗拒——太丑太触目惊心,我自己都不愿意正视。
可公子用宽慰的眼神看我,让我知道他们不会嫌恶。我伸出双手,夫人对主君道:“三郎如此可明白明珠他们昨日是何等情形?冬香这样小一个女孩儿家,也能下这样重手!怪道明珠那日病得不明不白,险些——”她不说了,拿帕子去按眼角。
我退到一边,只听主君道:“明珠,落水之事是否也是他们所为?”声音里已经隐隐含了怒气。
公子答了个“是”,夫人搂着他哭道:“都是娘的不是,才教你受这些委屈!”
主君大约是怕夫人哭,满腔不忿化为乌有,低声道:“你放心,我今日就去找他们要个说法。你别伤心,并不是你的错。明珠这个学塾不好,咱们换一个。”
公子原是默不作声被夫人搂着,但他听到这话,起身道:“换一个也未必会好。”
“我还是不去学塾了,请德高望重的先生来家里吧。父亲也不要去和他们理论。即便嘴上说管教无法对不住,心里也依旧不服。”
“将来会有他们服的一天。”
我同公子走到无人处时,终于忍不住道:“公子不去,岂不是遂了那起子小人的意!”
公子笑笑:“是我真的不想去。学生太多,先生讲课总是瞻前顾后,于我而言太慢。这不是坏事。”
可我还是意难平:“这就像吃了个哑巴亏一样。不过公子一定会金榜题名,让他们都服气!”
公子摇头笑道:“那是我为了宽慰父亲和母亲说的。倘若我为了让他们服气而考取功名,那我和看轻商户的人有什么区别?只要不自轻自贱,我像父亲一样做生意也很好。何必在意旁人想什么?”
我笑道:“公子是在参禅吗?”
公子同我开玩笑:“我明儿悟了,就去城外当道士。”
我亦笑道:“公子做道士,那我就替公子扫菩提叶、擦明镜台。”
半月后,主君请来一位老先生。公子告诉我这位老先生虽一生都在江湖中,高居庙堂之上的门生却无数;如今回到禾城是预备落叶归根颐养天年,家里有儿子的无不百般献殷勤,盼着被这位大儒指点一二。
“先生会留下来教公子吗?”我问。我们在大门口等着马车,可马车迟迟不来。
“我不知道。”公子袖下的手交握着,看起来很紧张。“传闻周老先生遴选学生只凭眼缘,没人能预判其心意。”
“公子样样都好,老先生一定会喜欢公子的。”我说着,又嘟囔起来。“不是说未时到么?这都过了一刻了......”
“老先生上了年纪,也许此刻正在休息。再等等罢。”
这一等就等到酉时,夫人和主君都有事处理先回去,只剩我和公子几个人等着。我的腿都木了,又不敢说回去,只好小范围走动着。
“你若觉得乏,就先回去罢。”公子道。
我忙道:“只是活动活动,并不累。公子还要等吗?”
“先生并没说不来。”
我叹气。公子倔起来谁都劝不动,倘若周老先生忘了,只怕就要站一夜。
好在没一会儿,就有一辆马车缓缓在门口停下。马车的车厢上不知被谁拿墨涂了,倒是云山雾罩一幅画。
公子这才走过去。腿脚有些僵硬,他走得有些慢。行至车前,他施了一礼:“可是周老先生?”
车夫不说话,里面也没动静。公子便又朗声问:“可是周老先生?”
车帘这才被掀起,露出一条小缝儿。来者细细打量了一番,这才似乎同意下车般“嗯”了一声。车夫跳下来摆好矮凳,终于搀下来一位蓝布衣的白胡老者。正是周老先生。
只是老先生下来第一句话却是:
“你这个娃儿生的好,我来吃你家的饭。嗯,门外就闻见香了!”
周老先生明明是禾城人氏,却不知操着何地口音——大约因为他在蜀地多年,学会了当地方言?他的行止也和我设想的仙风道骨的大儒大不相同,这真是奇也怪哉。
不过若周老先生的“合眼缘”就是好看的小郎君和厨子好的人家,那我倒是很有信心。
周老先生被我们引到小花厅落座,须臾就摆上宴来,夫人主君请先生上座。周老先生饮着酒,啧啧称赞:“这个酒好。来,娃儿给我倒上。”
他冲我扬了扬杯,我连忙上前斟酒。大约是喝到了好酒,周老先生看什么都美,笑道:“好,好。你们家好。”他趁着这个劲儿随口问了公子几句诗书经典,我听来都不算刁钻,公子自然应对如流,这下周老先生很笃定了。
“好,我就在这里了。娃儿来拜个师,明儿我就给你上课。”
这实在是意外之喜,在场无人能预料。夫人和主君忙施礼,道:“客房已经打扫完毕,万望先生不弃嫌鄙陋。若有不周之处,先生只管提。”
我一时看不明白这位周老先生。若说他这是思量后的选择,那关于公子学问上的考量实在太简单;若说是率性而为,那故意迟到也可说是考验公子心性。
但不管怎么说,老先生愿意留下来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