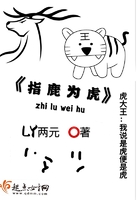傍晚时分,暮色渐浓。
云城宁府内。
宁成因念李元熹来宁府已有月余,嘱咐手下杀羊宰牛置下酒宴款待于他,并唤白狐与陈副将对席相陪。
屋里灯光辉煌,满满一桌的珍馐佳肴现下只剩下残羹盛肴,浓郁的烧酒满屋飘香。
一个白衣如雪,丰神潇洒的书生正倚着窗子,一杯一杯地饮酒,他身子摇摇晃晃,似醉非醉地曼声吟道:“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多行,他处不堪行……”书生凝视着窗外的月亮,叹息道:“只可惜路途遥远,也只能梦里多行了。”
陈副将端起满满的一碗酒,仰起脖子咕噜咕噜一口干了下去,一揩嘴角,满意地叹道:“好酒,好酒啊!”他看着书生喝道:“你这个酸狐狸!俺正喝的痛快,你倒在那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扰了俺的兴致!”
白狐闻言也不与他争辩,笑着走到桌边坐下喝酒。
陈副将又豪饮三碗,酒意上涌,他见李元熹听了白狐的话默然不语,眉间似有愁意,便好奇道:“小兄弟,你是哪里人?俺看你面容白净,倒像个书生!为何会到俺们这军营里来?”
李元熹一直低着头,凝视着杯中的酒,听到这句话才霍然抬头。
宁成见状心中一惊,连忙转头去看李元熹,见他神色无异,这才心中稍安,便在桌子下面,拧陈副将的腿,教他不要多言。
陈副将突然“哎呦”一声,转身瞪着白狐道:“你这臭狐狸,好端端地掐我作甚!”
白狐正欲反驳,却见宁成冲他挤挤眉毛,便只得摸了摸鼻子,悠然道:“我这不是看你只顾着讲话,却忘了要饮酒么!”
陈副将听了白狐的话,还想要再骂两句,就在这时,一个人从门外慢慢走了进来,青色的衣衫上一个褶皱都没有,残缺阴森的脸上带着种冷酷,坚毅的表情,眼神锐利如同刀锋。
他径直走到宁成面前,微微躬身道:“参见将军。”
李元熹惊奇地看着他,心道:这莫非就是几日前在府内杀人的青鹰?
那日青鹰杀人之时已是深夜,所以他并未看清青鹰的面貌,只知道他相貌可怖。
像是有所感知一般,他缓缓抬头,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刀锋般的目光正盯在李元熹的脸上,忽然道:“我是青鹰。”
果然是他,李元熹含笑施礼道:“久仰久仰,我是李熹。”
由于只身在外,为了以防萧氏知晓他的行踪,李元熹便自称李熹。
青鹰淡淡地点点头。
宁成道:“你深夜来此,可是京城里出了什么事?”
青鹰缓缓道:“渭城传来密报,昨日未时,有大批人马劫道,十万担粮草,被劫去了一半。”
宁成闻言骤然一惊,酒意醒了几分,问道:“可看清是何人所为?”
青鹰皱眉道:“来人皆蒙面,并未看清面貌,不过,从服饰上看,似乎不是中原人士。”
白狐奇道:“哦?那些人马可是从闽越而来?”
青鹰摇了摇头,沉吟道:“不,绝不是闽越之人,那蒙面之人皆髡发左衽,一身胡服,似乎,似乎是……”
李元熹与宁成对望了一眼,两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奇怪。
“对了!”白狐突然叫了起来,“我想起来了!”
李元熹,宁成,陈副将一齐吃惊地看向白狐。
“你想起什么了?”陈副将好奇道。
白狐眨了眨眼睛道:“是契丹人,绝不会有错!
李元熹动容道:“契丹人!”
白狐点点头,压低了声音道:“前几年,我在宫里当差,契丹使者觐见之时,我曾远远见过他们的穿着打扮,和青鹰描述的一点不差!”
青鹰接着道:“渭城密报上还说:有人在番兵远遁之时,曾见其部队回环方正,形如编剪,虽去无一支倒乱!”
李元熹闻言不禁长叹一声,道:“中国北方,素为外夷所居,历来不足为奇,只是这契丹人用法严明,乃能至此,恐怕后患无穷啊!”他心中担忧不已,这乱世之时,契丹恐怕已为外夷最强之国,假若趁势拓地,攻击中原,可是中国之祸啊!况且契丹之人一向野蛮,一旦战争打响,这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可就又要遭殃了!他身为男儿,空有一颗报国之心,却不能伐暴救民,赈济苍生,想到这,他便愁眉不展,心中连连叹息。
宁成与白狐闻言,也叹息不矣,屋内陷入了沉寂。
陈副将瞪着眼睛愣了半晌,突然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往外走。
白狐见他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奇道:“喂喂,你干甚么?”
陈副将粗声道:“干甚么?……走啊!”
白狐笑道:“走,你走哪去?”
陈副将牙齿咬得吱吱响,接道:“哼!走哪去?出了军营,俺就往西走,找到那契丹人的老窝,非给他一锅端了不可!也好教他们知道,俺们汉人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白狐闻言愈发笑得连头都抬不起来。
陈副将怒道:“白狐,你,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狐笑声渐止,斜睨他一眼,缓缓道:“没什么意思,就是笑你好说戏话!”
陈副将瞪大了眼睛,忽然跳起来道:“臭狐狸,你敢小觑俺!这是什么事?俺好说戏话!”他一边口里嚷一边手里比划道:“谁说大话谁是畜生,只教给俺一匹马,俺必定杀入贼营,把那契丹首领耶律金的头取回来!”
白狐抚掌大笑道:“哈哈!妙极妙极,你若真得耶律金的头颅,我白狐从此你做哥哥,供你驱使!你看如何?”
陈副将闻言撇撇嘴,道:“俺要做也是做你爹,哪个愿做你哥!”他转身冲宁成抱拳道:“将军下令罢,俺这就连夜追赶那贼人!”
宁成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喝道:“胡闹!这种事是闹着玩的?你好歹也是个副将,怎可总是如此鲁莽行事!”
李元熹见陈副将闻言低垂着头,怏怏不乐,便笑着对宁成道:“将军休怪!陈副将性情直爽,今日听闻契丹之事也是一时气急,才会出此狂言,想来也不是他心中所想!”
陈副将给宁成这般疾言厉色地训了一顿,面上赧然,心中虽犹有不甘,却也只得宁成的性子,当下便打定主意,趁着众人歇息之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溜出去。
李元熹盯着陈副将看了很久,见他眼珠子滴溜溜转,便已猜到他心中所想,便郑重道:“副将不知,如今这玄州梁友圭刚刚称帝,蓄势待发,想来凉州与玄州不日便要开战,这种千钧一发之时,万不可意气用事,贻误国事啊!”
陈副将怔住了,面上的不甘之色立刻脸半点也瞧不见了,心道:俺只想着如何报仇,却不成想,差点误了大事!便只得罢了。当下便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李元熹,“嘿嘿”笑道:“多亏有贤弟教导!俺这糙人!差点害了国事!”
李元熹笑了笑,道:“无事!”
宁成满面愁意,苦笑道:“虽是如此,这凭空少了十车粮食,这可如何交代啊!”
李元熹想了想,道:“敢问将军,府中还有多少余粮?”
宁成沉吟道:“现下倒不足为患,还能维持一月之久。”
李元熹微笑道:“一个月么,一个月足够了。”
宁成奇道:“这是为何?”
李元熹但笑不语,白狐却已知道他的用意,笑道:“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小兄弟说的可是这句话!”
宁成闻言也笑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哈哈哈!”
三人朗声大笑,陈副将却满脸疑惑,愕然道:“你们三人这是打什么哑谜呢!也让俺知道知道!这一个月怎么就足够了?”
白狐大笑着道:“我说陈胖子,你这还不知道!我问你,这梁友圭登帝,各州皆来祝贺,唯独我凉州不捧他的场,你说,依他梁友圭的性子,该怎么做!”
陈副将断然道:“这还用说!自然是要出兵攻打俺大凉,为他这贼子立威名啊!”
白狐接着又道:“我再来问你,这九州之中,除了玄州,最强盛的,是哪个?”
陈副将沉吟道:“这还用问!自然是我大凉!”他冷笑道:“你这狐狸,平时脑瓜挺灵光的,今日怎么竟成了木头!”
白狐也不理他,接着道:“这梁友圭登基之后,第一个要除掉的,自然就是我大凉了!”
李元熹叹息道:“不错,梁友圭平生最忌凉王,篡位后必定立即率兵数万,往攻凉州!”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兴高采烈,陈副将一时词穷,竟插不进话,听了半天也不知所云,便怒道:“哼!你,你们两个都比俺聪明!请你们两个聪明人快说说这粮草是怎么回事罢!”
李允熹笑了笑,道:“这粮草么,那时便有人来送,自然是多多益善了!”
陈副将听了恍然大悟,忍不住笑道:“正是!这可真是好事!俺正手痒痒,这就有人送死来了,哈,哈哈……”
几人便依旧入席,宴至深夜,尽醉方散。
午夜,夜色沉沉,星月低垂。
却说耶律金带领三万人马,日夕趱行,约有数日,如今已至汉城。
为首的人燕颔虎头,身材魁梧,神态甚是威严,正是契丹可汗耶律金,旁边马上的女子面容英美,一身黑衣,满头墨发随着衣袂在风中飘扬,看起来英姿飒爽,正是耶律金的妻子律氏。
耶律金朗声道:“这几日讨伐室韦,掠地渭城,众军士都辛苦了!回去之后必定好好嘉赏列位!”
众军士在旁听见,皆心中暗喜,都叫道:“是萧阿檀将军,尔朱武真汗带领咱们打的!”
耶律金闻言便大笑着拍了拍身侧的两位将领,笑道:“你们两个,可是契丹最勇猛的英雄好汉!我听说,中原有句典故:卧龙凤雏,得一可平天下!我看这两位都比不得我这两个爱将啊!哈哈哈……”
萧阿檀与尔朱武闻言,皆满心感激,一齐抱拳道:“属下不敢,全赖大汗悉心栽培,属下等才有今日之绩!承蒙大汗如此错爱,属下感激不尽!”
耶律金笑道:“你们两个自是刚勇无双,又何须本汗多加栽培!”说罢,便各个奖勉了几句,部队便继续向西前行。
又行了两日,离平州只剩下百余里,耶律金率部队行至一座高陵,部下两名哨兵忽然疾奔回来,报道:“禀大汗,前面有迭刺部拦路,人数约有五万。”
耶律金听了哨兵的言语,大吃一惊,忙问:“他们要干什么?”
哨兵犹豫道:“他们二话不说便拦住咱们的道,似乎……是要和咱们……打仗!”
耶律金沉吟片刻,向萧阿檀道:“你去问问!”
萧阿檀在马臀上刷刷两鞭,那马便纵蹄狂奔,向西驰去,不一会儿便没了踪影。
良久,耶律金见萧阿檀一去不回,略有些担忧,便按辔慢行,率领着部队徐徐前行。
突然,前面十里内尘土蔽天,号角雷动,耶律金心中一惊,凝目四望,远远地望见旗帜晃动,约有几万多骑契丹兵快马追来,不一刻就快赶上了他们。
耶律金望着远处的骑兵号角,便知是八部夷离堇所率人马,只见他们个个弯弓上弦,严阵以待,耶律金心中一紧,便知事情不妙,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炮角之声,山上山下顿时火把齐明,伏军四出。
八部夷离堇皆大声发号施令,契丹军马也一批一批地四散开来,顷刻之间已将耶律金前部兵马团团围住。
尔朱武纵一纵马,赶至队前,大喝一声道:“前方可是八部夷离堇?尔等不知死活,竟敢来拦截大汗的道路!”
八部夷离堇远远闻见,皆沉默不语,耶律金心中一凛,正欲仔细观察,旁边的尔朱武却突然凑上来低声道:“大汗,我看那队伍前面的那两个人有些眼熟,似乎,似乎是耶律刺底和耶律葛!”
耶律金闻言愕然勒马,他将信将疑的往前望去,只见前头尘土大起,八部之兵已渐渐逼近,为首的一个契丹人生的虎背熊腰,身材魁梧,正是他的二弟耶律葛,旁边的契丹人面目白净,相貌温雅,正是三弟耶律刺底,不觉暗暗吃惊,道:“这,这正是他二人!”正自寻思,忽然前面沙土飞扬,两人已率彪军疾驰而来。
尔朱武见状圆睁双眼,猛喝一声道:“耶律刺底,耶律葛!你等先前图谋作乱,大汗特开恩加以宽恕,让你们改过自新,你们为何还是这般反复多变!想要加害于大汗!”
耶律刺底闻言心中羞愧,慌不能答。耶律金向来信任他们这些弟弟,把后方都交给他们管理,想来此次他与耶律刺底谋反定是让耶律金措手不及,想到这,他便低头不语。
耶律葛起初远远地见耶律金的部队强马壮,兵甲犀利,心中颇为畏惧,此刻走进了却看见他们的兵虽强壮,却远远比不上自己与八部联合的人马之广,况且他们早已人困马乏,此刻便愈加不堪一击。颇为不屑,便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大哥,休怪弟弟们无情,只是你这大汗已做了九年之久,也该下来让弟弟们坐坐了!”
耶律金沉声道:“虽是如此,这契丹的江山几乎都是本汗一手打下,本汗居之无愧!况且本汗待彼不薄,彼为何害我!”
耶律刺底看着耶律金,讷讷道:“大,大汗不要生气,你不遵契丹旧例,我等也是奉八部之命,前来降你,你,你如今势单力薄,还是不要负隅顽抗了罢!”说到这,他满脸诚恳地看着耶律金,道:“你如果遵循旧例,举行柴册礼,即使我们兄弟之中,有人做了新可汗,也必然不会亏待你的!”
尔朱武大笑三声,厉声道:“耶律刺底,耶律葛,你们休要猖狂!我大汗此刻虽兵少,却仍视汝辈如同儿戏!况且,你们比之汉人的军队如何!他们还不是让我们大汗打的落花流水,弃甲而逃!白白的丢了这万担粮草!你们还有甚话说!”
耶律刺底被他这般呵斥心中恼怒不已,却自知理亏无话可说,只得强忍怒气,不再言语。
耶律金皱紧眉头,正欲呵斥耶律刺底与耶律葛,却突然目光一顿,只见他的亲妹妹苏葛姑正一身劲装,坐在白驹之上恨恨的瞪着他,方才失踪许久的萧阿檀也在一旁。原来,萧阿檀领命而去后,不久就碰上了驱马前来的八部夷离堇,还未等萧阿檀询问其意,就被士兵给制住送到了苏葛姑旁边,此刻正满脸怒气地瞪着苏葛姑。
他脸现怒色,喝道:“苏葛姑,你是本汗的亲妹妹,国家至亲,为何一念之间就辜负了本汗!附从于叛逆!”
苏葛姑冷笑一声,道:“大哥,你也忒没良心了!你妹夫当了三年的北府宰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罢!他萧阿檀凭什么一上来就将我丈夫踢走!”苏葛姑是家中独女,向来娇惯,就连耶律金这个大哥也一向不放在眼里,此次丈夫被降职,更是让她对耶律金忌恨不已,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八部。
耶律金闻言淡淡道:“萧连铎为人愚钝,不通事务,本汗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苏葛姑怒喝道:“呸!我看你分明是想借此机会羞辱于我!那他萧阿檀还曾被汉人俘虏,契丹因次赔了一大笔钱,你怎么不说!”
她心中气闷,猛然举起手中马鞭,朝着萧阿檀脸上狠狠甩去,打得他痛彻心扉,萧阿檀强忍痛楚,脸上登时一道殷红的血痕。
他毫不畏惧,昂首道:“要杀就杀,别婆婆妈妈的!”
苏葛姑闻言便怒气冲冲,用力拔出腰间长刀,想要杀了他解恨。
尔朱武见状心中大怒,他与萧阿檀乃是总角之交,胜似骨肉兄弟,如今见他被一妇人羞辱如何不恨,当下便弯弓搭箭,“飕”的一声,往苏葛姑头上射去,苏葛姑吓得浑身颤抖,慌忙向一旁侧身,发箭便从她头顶蹿了过去。
尔朱武见一击不中,正欲再击时,耶律金顾念苏葛姑与他有血脉亲情,便制止道:“不可!”
尔朱武便在马上俯低身子,右足勾住马镫,嗤嗤两箭,往萧阿檀座下的名驹上射去,那马见羽箭疾驰,不待萧阿檀拉缰,往右急闪,哪知这一箭来势凶猛,“噗”的一声,正中马腹,那马痛极长嘶,发力疾驰,八部手下的士兵一时不察,让那马一下冲到耶律金的队伍里,萧阿檀身子一晃,跃身踏上马背,左脚登时用力向马腹一踢,接着用力一跃而下,奔到耶律金身边站定。众军士见萧阿檀如此神勇,皆齐声呐喊,为萧阿檀喝彩。
耶律金原本见萧阿檀在马上摇摇欲坠,心里一阵担忧,待见他平安无事,不由得大喜过望,萧阿檀是他部下中最为忠勇的将士,多年来为他赴汤蹈火,征讨外敌,立功无数,倘若这次有甚么损失,即使是用牛羊万匹都补偿不了的!
耶律金想起方才看着两个弟弟的话,便连连冷笑,厉声道:“本汗的王位乃是八部亲自选拔,名正言顺,你们还有甚么好说的!”
八部夷离堇见状皆横目斜睨,冷哼一声道:“大汗,您这可汗的位置是怎么得来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用欺骗的手段挟持我八部夷离堇选举你为可汗,本就不合契丹例法!我契丹又凭什么认你做“天皇帝”!”
耶律金闻言捻须不语,契丹乃是由八部强国组成,每部各有酋长,号为大人,可汗是从八部之中推举而成,统辖八部,三年一任,不得争夺。按理说,他应当每三年举办一次柴册礼,然而他多年来常率兵入境,掳得汉人数万为他耕地建房,汉人常言:中国君主历来世袭,未尝交替。因此他便沿制汉袭,想要废除契丹三年一任的老例,到如今,已有九年未曾举办柴册之礼。
三年前,两个弟弟贪心不足,屡屡趁着自己率兵收付夷越之时犯上作乱,他为收复民心,便秘密举办了一场柴册礼,将弓箭手埋伏在帐外,要挟八部夷离堇封自己为可汗,为保安全,他并没有邀请于越参加,虽不合契丹旧例,但他多年来九死一生,征战沙场,为契丹打下多少土地!若不是他,契丹怎会有今天牛羊千万,丰衣足食的现状!
可汗一位,他始终问心无愧,因为他为此付出过太多的心血,即位初时,契丹国力衰微,百姓贫穷,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报国救民的志向。诸弟之乱时,他带兵平反,虽大为失望却并不痛心,因为他知道,弟弟们愚笨贪婪,并不能体会到自己多年来的苦心,然而,这次他们与八部协同叛乱,自己却痛心疾首,因为他们率领的人,正是自己多年来为之苦苦谋求的百姓们!
想到这,他便有些心灰意冷,哑声道:“即使如此,我便退出选举,这可汗,不要也罢!”
八部夷离堇闻言皆心中暗喜,然而转念一想却又有些不舍,这耶律金帐下有十二部,且他兵虽不多,却个个骁勇,这一退选,自己岂不是分毫未得了?想到这,他们便连连摆手,笑道:“大汗您说哪里话!这柴册礼怎可不参加,我们只是想要维持契丹旧例,并没有不选您的意思!这柴册礼啊!您还是得参加!”
耶律金冷笑一声,正欲说话,律氏却忽然走上前凑到他耳畔,低语了几句后道:“大汗切宜缓缓而行,不可轻率!”耶律金听后沉吟良久,突然冲八部夷离堇喝道:“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得好算盘!我告诉你们,这可汗谁爱当谁当,我立汗九年,所得汉人甚多,既是如此,我便自为一部从此退居汉城,谁也别来打搅谁!”
八部夷离堇见状,只得同意,耶律金便将手中的可汗旗鼓掷了过去,转身率马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