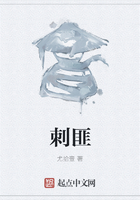有诗云:
日月生前,尘寰莽莽。有风自南,斯天苍苍。浮陈于西,翳翳成凰。茕怜其羽,擢擢其芒。昱夜为阴,昱昼为阳。阳晦于海,阴藏于冈。虚实之间,灵欲昏徨。道本为仁,奈何圣殇。
日月生后,玄冥独来。化龙于东,破天于淮。燎燎离火,震震雷霾。天不兼覆,地不周载。我道去兮,奚为人害。初本自逝,人本自衰。虚实之间,灵欲明泰。女娲补天,圣人善怀。
日月同辉,天人同光。天有天霸,人有人王。万类相竞,勿告欢狂。缗蛮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悲苦,人力终荒。时日曷丧,与汝皆亡。待到周公,复明人皇。梦泪几何,人困几方!
—————————————————————————————————————————————————
自人类有文明以来,纷争不断,战火不息。在由一场场战争组成的历史中,英雄才人辈出,前赴后继,又终成枯骨。逐鹿之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现今中华大地的民族分布形势;甘之战正式巩固了夏王朝的统治,也让王位传承制度从禅让制过渡到承袭制;鸣条之战商汤灭夏,以七十里终谋得天下,从而建立了商王朝;牧野之战武王伐纣,姬发以少胜多,推翻商,开启了属于大周王朝的时代。
大周王朝传承至今,已历五百余年,期间更是战争不断。二百多年前,犬戎攻入都城镐京,大周王朝只得迁都洛阳。自此以后,王室衰落,天下陷入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毫无疑问,每一场战争的代价都是巨大的,环顾人间,正所谓“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现状一点不差。人的铭言是:我们经历过前所未有的黑暗,但依旧不停止对于美好和光明的向往。人类的火种从微末中开始燃烧,从一点微光燃烧成熊熊烈焰,靠的是有一代又一代英雄心怀天下、薪火相传。如今的大周王朝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整个天下都在寻求着一朵烈焰、一种解放,万千黎民都在呼唤着一个人——一位英雄,能救他们于水火,走在街上甚至你都能隐约听见一个声音,在叶片最微小的震颤间,在大地最沉重的脉搏里,奏响着时代的罄音,迎接着时代的浪潮。而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浪潮的最前端,一点微光的空处,一片最深沉的平静里。
—————————————————————————————————————————————————
郑国,新郑城,整个大周王朝最繁华的城市。因为地处于中原诸国的最中心,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在列国间做生意的商人途径与此,并在城邦密集的街市间与同行花天酒地、拉帮结伙。
枫叶沙沙作响,一片红黄中还残留着几分初秋的绿意。街道两旁坐落着飞檐式的瓦屋,体现出这座城市的富足与开放。平民区的市集上热闹非凡,马车招摇过市,人群在此间川流不息,各行各业,各型各色,乐此不疲。喊声、闹声、笑声此起彼伏,繁华至极。
“走过路过,客人千万不能错过,本店新酿秫酒,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喧嚣的街市,一个小厮正在酒馆前吆喝。
“还有没有靠窗的上座了?”闻言走来两位商人,其中一位向小厮问道,一口宋国方音。
这两位商人衣着不凡,气宇轩昂,活像两位贵族。其中一位外表约莫四十来岁,灰发乌须,面目威严,可惜方脸上一只鹰钩鼻总给人一种阴翳之感;他身着紫色长袍,右衽交领,燕尾拽地;腰上系着一只朱漆兽首环佩,头戴镶金冠弁。另一位,也就是刚才问话的这一位,看着年龄不到四十,面容俊朗,棱角分明,一身淡青色深衣,须发乌黑,长发在头后盘成一个大髻,以鲡韬为蝶结。
“有的有的,两位里面请。”小厮点头哈腰,连忙答道。
小厮把两位商人引入内堂的小隔间,隔间不大,有扇对着街市的窗,地上铺着一张草席,上面有一方小食案。
紫袍商人左右打量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嗯,还算干净亮堂。”
两位商人在食案前相对跪坐,青袍商人对小厮吩咐道:“上两壶秫酒,一盘腊肉。”
“好嘞。”小厮应了一声,作了个揖就离去了,临走还没忘合上隔间的门。
青袍商人名云,字叔纯,弦氏,祖上是商王朝赫赫有名的宫廷乐师,后来王朝覆灭,他这一支家族无处安身,就在各国间做起了小生意。生意越做越大,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商队。事实上,在当时,类似于他家族的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大周统一天下之后将大多数的商朝遗民分配到了商丘一带成为了一个诸侯国,宋国,以“子”为姓。有一小部分遗民被分配到了洛阳,而剩下的便在各国间流浪,顺带着做些生意,“商人”一词最初就指的是这些人。
弦云面容清矍,正色下双目闪闪发亮,颇有几分潇洒正气,他恭敬地向紫袍商人拱手道:“会长今日找我,想必有要紧之事相托,望不吝赐教。”
此时紫袍商人正在房间角落的一个大木桶前洗手。他闻言笑了笑,甩了甩手,再用衣襟擦了擦。
紫袍商人名一,字伯淮,黄氏,现任郑国商会会长,此次会面就是他向弦云提出的。
黄一捋了捋胡须,眼神和蔼地开始端详起弦云来,片刻沉默后突然笑问道:“叔纯兄从商有十年了吧”
“是,”弦云如是答道,“我自十五与两位长兄随家父行商于列国,二十岁大哥病故,二十二岁二哥亡于盗贼之手,二十八岁我承领家父之商队,至今确已有十年了。”
黄一闻言叹了一口气,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实在可悲可叹啊!”
说话间小厮已把酒肉摆上案,略显浑浊的秫酒冒着腾腾的热汽,这种用黏性高粱酿成的美酒浓香沁人,边上一盘腊肉色香俱全。黄一捏起一片腊肉放在嘴里,再就一口秫酒,舒坦地呼了一口气。
“叔纯兄,世道坎坷啊,生活着实不易。若想维持下去,我商人理应互帮互助。”黄一接着道,“今日我约兄出来一叙,就是代表郑国商会和你谈一笔生意。”
“哦?会长不妨细说与我。”弦云道。
“我听闻叔纯兄此次途径新郑是在运一批货物到吴地,不知可有此事?”黄一问。
“确有此事,这是一批铁器,我准备卖到吴国换些珍贵兽皮、象牙等物。”弦云皱眉道,“不知会长为何提及此事?”
黄一把玩着陶制酒杯,叹道:“吴地遥远呐,叔纯兄。其间密林遍布,荒野莽莽,山贼横行。若是中途出了什么变故可就得不偿失了。”
“关于此,会长有何良策?”弦云请教道。
黄一盯着弦云的眼睛,正色道:“把货卖给我郑国商会。”
弦云笑了,“据我所知,郑国商会似乎没有与铁器相关的贸易伙伴吧,不知这笔交易是商会的意思还是郑国哪位大夫的意思?”
“这笔交易是国氏卿大夫国子非先生的意思,我们很需要这批铁器。”黄一答道。
弦云沉默了,他知道在当今世界,商业与政治已经勾结在一起,甚至密不可分。各国商会已经逐渐被少数贵族掌控,显然,眼前的黄一就是国子非大夫在商会的代言人。他不了解国子非,但是他知道郑国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国君的权力被完全架空,由七大家族轮流当国和执政,这七大家族都是当年郑国的国君郑穆公的后代,所以人称“七穆家族”。现在郑国当国的是七穆家族中的驷家,而在两届之前,郑国当国的就是国氏的国家。在国家当国期间,作为国家家主的是国乔国子产,这位家主影响力巨大,在列国间享有盛名,因此就算在他死后,国家依然在郑国政治上有着一定的话语权。国子非就是国子产的弟弟,郑国的卿大夫。
“感谢大夫为我着想,就是不知大夫愿意为这批货付出什么价钱?”弦云问道。
黄一伸出五根手指,道:“五十镒黄金,外加二十匹绢帛。”
弦云又沉默了,这批货对于他意义重大,对于他的商队更是无比关键。他的商队运营并不好,由于天灾人祸,商队已经连续一年入不敷出了。为了拯救商队,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吴国寻找买家,终于找到了一位贵族愿意以珍稀兽皮和象牙饰品作为交换,订购一批铁器。这批铁器价值很高,对于商队来说能赚取的利润也很大,不过相对的是,风险也极大,如果这批货出现了什么差错,代价是商队无法承受的。弦云觉得这是商队的一次转机,于是他应下了这个风险极大的订单,并亲自赶往晋国筹措货品。寻找买家一个月,筹措货品一个月,运到新郑又两个月,为了这批货,他已经足足付出了四个月的精力。
商人做生意是有规矩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要买家订购的不是太过于珍贵和冷门的物品,都不需要付定金。为了筹措齐这批铁器,弦云足足花费了六十镒黄金。六十镒黄金是什么概念?将近三十四斤黄金,普通的家庭花一辈子也花不完。
原本,这批铁器运到吴国换来的兽皮等物至少能在中原列国卖出超过一百镒黄金。而现在黄一打着卿大夫的旗号想用五十镒黄金加二十匹绢帛就在郑国把货物直接收购,这六十镒黄金的铁器,再加上一路运到新郑的成本,如果弦云同意了,弦氏商队将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黄会长,这个价格恐怕我是很难接受的。”弦云尽量把语气压得恭敬委婉,“这批货对商队很重要,我还是想冒险把它运到吴国。”
黄一神色不变,劝道:“叔纯兄不要急着做决定,多加考虑一下吧,毕竟得罪一个卿大夫可不是件小事。”
弦云抱拳道:“谢会长提醒,我明天就动身离开郑国。”
“离开郑国?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吧。”黄一笑道,“叔纯兄慢慢考虑,什么时候考虑清楚了,什么时候再离开。”
“会长这话是什么意思?”弦云心中咯噔一声,脸色顿时变了。
“在这郑国地界,还没有子非先生想得到却得不到的东西。”黄一笑容不变,语气却略带阴沉地说道,“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交易的事,凭你一个又怎么能和整个国氏家族作对呢?”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弦云感到他的毛孔一下子就被冷汗冻住,他只是一个小商人,光是维持家庭就已经不堪重负,现在黄一的话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弦云说道:“郑桓公曾与商人定下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此为郑国商业之基础,郑国之民皆须遵守。黄会长今日之言实在有违此誓,若流传出去,想必对商会乃至国家的名誉都是一种损害。”
郑国之所以商业发达,有大量的商人聚集于此,不仅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得益于早年郑桓公代表郑国和商人之间定下的这个盟誓:只要商人不做背叛郑国的坏事,郑国从贵族到国君都没有权力在与商人交易时强买强卖、讨要或抢夺商品。甚至于发现商人参与一些垄断、投机贸易、贿赂官员的事件,郑国政府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虽然实质上郑国商业确实掌控在贵族手里,但明面上谁都不敢违反这个誓言,这也给了商人们一个相对的自由。现在弦云戳破了这层窗户纸,就等于是向黄一表明了他坚决不从的态度,若是现在谁都不肯退让一步,此后之局面必是不好收场了。
此时隔间的门外忽然传来悦耳的琴声,缓解了紧张的气氛。只见门开了,一名艺伎正跪坐在地上鼓琴。纤细的手指灵巧地在五根琴弦之间拨动,琴声如流水鸣溅。艺伎身形佝偻,面容苍老,看上去春秋已度四十余年光景,虽面容尚风华犹存,但眼中却有着难掩的疲惫和沧桑。
黄一凝视着弦云,笑容依然,只是眼神微闪。他放下手上的羽觞(一种酒碗),对弦云说道:“多谢叔纯兄提醒,我都忘了有此盟誓了,既然有誓言在先,那么桓公之所说确实不好违反。”随即他叹了一口气,又道:“也罢也罢,这笔交易我就不勉强叔纯兄了,还望日后一同谨遵誓言,恪守商人之节。”
弦云勉强回以笑容,心中暗想终于是让他逃过了这一劫,冷汗随鬓角从他下巴流了下来,浸湿了胡须。
年老艺伎双手愈加灵动,十指翻飞出一片碎影,乐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若是有后世唐朝诗人在此,定会脱口而出一句“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乐曲缓缓结束,余音久久不散。小厮从一旁探出头来,哈腰道:“两位客人,琴声如何?此女原是王宫艺伎,暂住本店,今日看两位气禀不凡,特为演奏一曲助兴。”
“既为王宫艺伎,今日我能得一闻,实为荣幸。”黄一说道,然后从腰间解下了一串郑国布币放在方案上,叮叮当,青铜制的布币相互碰撞发出好听的脆响。
小厮满脸堆笑,急忙上前揣在怀里,拜谢连连,谄媚无比。
“听闻叔纯兄祖上也为弄弦之人,今日乘兴,何不坐弹一曲?”黄一说道。
弦云方才惊魂尚未安定,闻言急忙推辞道:“我自小随父行商,从未弹习过琴艺,今日便是想献丑,却也有心无力。”
黄一遗憾道:“实在可惜了,我观兄手指修长,耳聪目明,本应是弄弦之才。”言毕,咂了一口酒,颇有感叹之意。
弦云见黄一再未提强买铁器之事,也定下心来,便跟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两人直聊到太阳下山才各自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