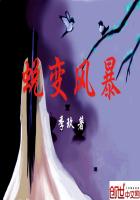深秋,凉意如霜。
夜幕慢慢拉开,不远处的群山,渐渐朦胧成一团团灰黑色。
山脚之下,星星点缀着几十户人家。
这是大青山下,微不足道的小村落,王家村。
大青山山头林立,地势起伏,山民拥有田地稀少,大部分都靠着在大青山里采药、打猎为生。
随着黑夜来临,王家村静谧无声,整个村落黑灯瞎火,灯油金贵,不是寻常人家能够点起的。
叹息声从其中一间破败的屋子传来,屋顶是用圆木做支撑,茅草捆扎在一起铺盖,四周的墙壁是由黄泥混杂着稻草和竹条组成,有些地方已经开裂。
在门口靠右侧,有一个土灶台,黄泥砌成,表面上涂抹了一层薄薄的石灰,灶台上架着两口锅,一大一小,小的那口灶火正旺,一股浓烈的药味从锅中传来,气味刺鼻难闻。
门口靠左边,黄泥土的墙上被钉着几根手指粗细的硬木条,木条上挂着水壶、背篓、草帽和几串细细的烟熏肉条,墙角落里则放置着一口泥陶烧制的水缸。
正中间则放着一张小木桌,木桌上放置着竹蔑编织的筛子,筛子上面摆了一些晒干的草药。
屋子的最里面,放置着两张木板床,紧挨着在一起,床上的被褥黑漆漆的,又薄又硬,其中一张小的床上睡着一名十一二岁的男童,脸色蜡黄,缩在被窝里,不时有寒风从泥墙上的缝隙灌来,冷的他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
炉灶口火烧的正旺,给茅屋里增添了一丝暖意。
王老田坐在炉口旁的木凳上,不时的向灶台里添一根干柴,黝黑四方的脸上满是褶皱,沉闷不言。
借着灶台底下的火光,王婆娘娴熟的缝补着一件满是补丁的外衣,嘴里不停的唉声叹气,脸上布满了愁苦。
“娃他爹,二娃这病怎生得这么严重,医师不是说只是感染了风寒吗?二娃都昏睡了半个多月了,身上时冷时热,他不会就这么没了吧。”
“今年草药难寻,价钱又不高,你去大青山里采药,拢共就挣了五六两银子,二娃治病花了四两多银子,还不见好转。眼看着隆冬将至,年底就要来临,黑风寨的征税还没有着落,今年这个大年怎么熬过去...”
“大妹年初才去镇中倪家当丫鬟,没攒多少钱,前几日已经托人带了二两银子,也帮衬不了家里了。”
王婆娘叹着气,手上没有停歇,絮絮叨叨的说着家里的艰难。
黑风寨是大青山里的山匪,在大青山里就是规矩,山脚下十几座村落山民采药、打猎都要向其每年缴纳二两银子。
只要给了银子,就不会来侵扰山民,否则黑风寨轻则来人打砸抄家,重则让山民家破人亡,那帮土匪可是杀人不眨眼,又因为老窝在大青山里,道路崎岖,易守难攻,官府也奈何不了,几次剿匪都无疾而终。
对大青山脚下的山民来说,黑风寨比豺狼虎豹更为可怕,他们人数众多,武艺高超,下手又狠毒,老实巴交的山民根本不敢反抗。
炉火还在烧着,屋里的药味越来越浓,王老田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只是个采药的山民,有什么办法?
这几年里,草药越来越难找,多数都要去大青山更深处才有些收获,可大青山更深处...那是他们这些没有武艺的山民可以去的吗?那是要人命的!
县城里的药堂收购的价钱不变,忙碌一年也攒不下几个子。
家里还有二两多的银子,可是上交给黑风寨的银钱必须存着,要不然黑风寨会要了他们一家老小的性命。二娃的命虽然重要,也重不过一家子的性命。
王老田看着小床上躺着的二娃,叹了口气,大床上还有一个三丫头,年仅八岁,因为天冷,三丫头将整个人蒙在被子里熟睡。
“娃他爹,要不,将三丫头卖了吧…卖点银子,二娃也能有个活路。”
王婆娘神色哀愁,三十多的年龄,发丝上已经有几根白发,脸上更是苍老了许多。
她寻思了好久,才想出了一个法子,虽然对不起三丫头,但为了二娃,还是值得的。
“闭嘴!三丫头能卖吗!”
王老田大怒,手指着王婆娘,咬牙骂着,憨厚的脸庞竟有些狰狞:“卖给人牙子,娃还是自己的吗!签了卖身契,命就是属于人家的了!”
王婆娘当然明白这个理,签了卖身契,就划入了奴籍,被卖到心善的人家,还有一口饭吃。被卖到凉薄人家,主人家即使将你虐待打死,顶多陪点银钱了事。
况且三丫头生的清秀,人牙子多半会把她卖给春楼妓院,那里更不是好去处。
可是二娃子病了,需要救命钱,不卖三丫头又该怎么办?
但凡有一点办法,王婆娘也不想卖三丫头,三丫头也是她十月怀胎所生的,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娃他爹,三丫头毕竟是个女娃,家里就二娃子这么一个男娃,二娃是要给咱们家传宗接代的,可千万不能这么没了的!”
王婆娘哭着,嘴唇蠕动:“这就是命,是三丫头命不好…”
望着自家婆娘哭哭啼啼,王老田沉默了,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婆娘说的对,这就是命!
许久之后,王老田抬起头来,狠心咬牙说道:“三丫头俺绝对不会卖的,喝完这副药,把药停了吧,二娃子...就让他挺着吧,挺的过去就挺,挺不过去就是二娃子命不好!”
“二娃子昏过去半个多月了,也请药堂医师看过了,俺也尽力了…”
王婆娘听到王老田这么说,不由得哭的更伤心了,这是要放弃二娃了啊!
她放下手中的活计,起身走到炉灶旁,小锅里的汤药已经熬制好,揭开锅,刺鼻的苦味随着热气腾腾的水汽弥漫了整个屋子。
把汤药盛起,装进木碗里,王婆娘端着药来到二娃的小床边。
二娃面色蜡黄,额头上高烧不断,小脸因疼痛而紧皱,惹得王婆娘一阵爱怜,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滴落在二娃的脸上。她将二娃搂在怀中,一勺一勺的将药喂进二娃嘴里。
“苦...苦死我了…”张鹏飞在睡梦中,只感觉脑袋昏沉,嘴巴里似是被灌了黄连一般,苦涩难挡。
他感觉身体提不上劲来,无比虚弱,眼皮子更是难抬,让他不能睁眼看清楚外面的情况。
“二娃!是你在说话吗?你感觉怎么样!”
王婆娘听到二娃嘴里的呢喃,惊喜万分,抬起头冲着王老田喊道:“娃他爹,二娃...是二娃在说话,二娃要醒了!”
王老田一怔,连忙来到床前,二娃...要醒了吗?
“二娃?二娃是谁?是在叫我吗?”
张鹏飞恍恍惚惚的想着,感觉浑身上下都是酸痛感,外面好冷。
他不是出了车祸,瘫痪在床吗?他的身体早就没了知觉,为何还能感觉到疼痛?
他是死了吗?
死了也好,成为了一个废人,早就应该去死了,他的存活除了拖累父母还有什么用!
他就是个废人!
家中还有弟弟替他尽孝,他死了,父母的负担会轻许多吧…
张鹏飞脑海里想着,耳朵里却传来一阵阵焦急的呼唤声,熟悉又陌生。
到底是谁在呼唤他,张鹏飞想睁开眼睛看看。
下一刻,他眉睫微动,慢慢的睁开了双眼…
借着灶台里还未熄灭的炉火,昏暗中,一个农妇坐在床头,哭肿着双眼,惊喜的看着他。她将自己搂在怀中,右手上还端着一只木碗,难闻的味道从木碗里传来。
旁边还站着一位面皮黝黑的汉子,穿着一件麻布衣,上面打满了补丁。
见到二娃苏醒。
王老田满是褶皱的脸上,布满了惊喜,紧皱的眉头微微舒展。
大青山王家村里的一家贫苦山民传来了久违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