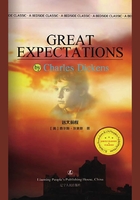北京当之无愧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在这繁华中,有深厚沉淀的历史文化作底蕴,所以它的繁华是有根有据有内涵,南方的那些城市与它比起来显得有些浮漂。可在这有深度的繁华中,因为有全世界各种不同新鲜血液的注入,所以难免就带点浮躁的嚣张之气,而这嚣张的繁华似乎钻进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连那博大的文化底蕴也有点心浮气躁了。在这里,有的是精英中的精英,权贵中的权贵,奢华中的奢华,老北京的京腔京韵都似乎不再那么有板有眼地沉稳了。
北京的天空在怡然眼里总是有点苍茫茫的,雾沉沉,那繁华和喧闹的市声,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个城市,带给她有种热辣辣的生活感,现在那种市声好像也离她遥远了一一这个城市对她是虚掩着门的,里面充满着神秘的华丽,她有点懒怠,脚前脚后总有羁绊似的迈不开步去推门进去。虽然她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两年多了,可是走在热闹的王府井大街上,那种热闹对她仍是陌生而排斥的,在热闹中的寂寞,比寂寞中的寂寞,更深了一层,深到了骨子里去,脸上不自觉地便有点油然哀起的模样。
白皓的公司刚开始运营,资金人员等诸多问题亦非想象中的简单,每天回到家都是一副焦头烂额样子,怡然忙着端茶倒水,一岁多的儿子蹒跚地走到他面前,扑在怀里,他抱着儿子,有时候会拉着怡然坐下,笑着说:“你们两个就是我工作的动力。”怡然说:“只要过得去就行,不要一味地争强好胜,累坏了身体……”白皓很简短地截断:“我不想输给别人。”
白皓的这种心理让怡然感到不胜其累,孩子感冒发烧,小区门口的医院都可以治得了的,白皓却是一定要去妇女儿童医院,早上七点钟起床开车去,如果输液,要晚上十点钟才能回的来。因为那是全国著名的医院,没有一次不是在焦灼的排队、哄孩子、漫长的等待中一点点地熬过来。此时,白皓妈也搬来同住,白皓往往把她们三人送到就匆匆赶往公司,怡然知道婆婆也是有怨言的,但她绝不会附和媳妇的思想去反对儿子——现在,在她眼里儿子和孙子都是无可挑剔,唯有媳妇,仍是怎看怎不顺。
白皓妈时常在屋里念叨着,这大城市物价如何的贵,儿子一个人挣钱养活一家人怎样不容易,还时不时要怡然汇报一下当天买菜的开支,教导她学习自己多年积累的勤俭节约经验,夹在一个追求贵族化生活的儿子和一个极度刻薄的婆婆中间,怡然左右不是。好在怡然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朋友,一个和她们住一个单元的年轻女子,名叫翠华。
两个人常在电梯中相遇,有一次怡然抱着儿子,手里掂着一些菜,儿子不知为何哭闹着,把怡然累得满头是汗,翠华主动地帮她提起菜,又逗弄孩子说笑,一来二去,就熟了。有时在小区的花园里,两个人坐一起边哄孩子边聊天,翠华是一个好看的女孩子,二十五六岁,属于那种鼻子是鼻子眼是眼,分开看是端正,聚在一起就是俊俏的女人,头发是大卷的波浪形,披在她的肩上却不是妩媚,仍是俊俏。衣服也多是名牌,但没有穿出丝毫的咄咄气势,一点都不张扬,还有点羞答答的意味。她的名字顺便带出了她的出身——她本来是叫翠花的,她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把“花”改成了“华”,一个四川山区出来的女孩,初中文化,十六岁就来北京,饭店服务员,保姆,工厂女工……吃了很多苦,但她是不觉得,笑嘻嘻的:“当时想着只要从家乡走出来,吃点苦也是新鲜的。”但她是漂亮的,那漂亮还有大山的纯净,好像被大城市的灯红酒绿污染不了似的,所以她比同出来的姐妹幸运点——如果可以叫做幸运的话,她被一个台湾老板包养了,在小区以她的名字买了房子,她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三岁,上了顶昂贵的幼儿园,老板隔仨月俩月地飞回一趟,所以平时她比怡然要清闲,说到自己的家人,她很爽直,“我们家只是含含糊糊地知道,但他们都不肯来,觉得丢人,哎呀,有时候我想想,有什么丢人的,他不找我,还会找别的,有钱男人都这样,我比起同来的那些姐妹要少奋斗多少年呀。”她捂着嘴吃吃地笑着:“你知不知道,现在小三们还得竞争上岗哪,你看我,除了漂亮什么都没有,你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翠华是个心无城府口无遮拦的人,没有多久就把她自己的事全盘说给了怡然。只是包养她的人多大年纪,她始终没有说,怡然也不好意思问。
两人更多的时候坐在一起是谈家乡的事,小时候的事。翠华描绘他们那里的风土人情,大山的清爽,纯净,贫穷,眼里有一点点伤感的缅怀思念,这符合了怡然的心境,不管哪个地方,再大的城市,不过多的是更高的楼,更多的娱乐场所,更不可思议的见闻,自己家的小城在她心底却永远是可爱的纯净的,没有太多的小心谨慎,尽可能地随性恣意,俩人虽不是一个地方的,却同是北京城的外乡人,有点他乡遇知己,“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只是怡然的感伤是实在的,翠华的的感伤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便是对目前现状“苦尽甘来”的自豪感,翠华也是有思想有憧憬的人,她说:“其实我觉得当小三比当老婆压力要小点,你看看现在的有钱男人,哪个对老婆有多忠贞的?我喜欢看偶像剧,是真正的被爱,轰轰烈烈的地久天长的爱,有钱,没有生存的压力,我也渴望做一个不依赖男人的女人,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己支配好多事,好好地谈场恋爱,找个自己喜欢的男人……钆胎然喜欢她的没有修饰的语无伦次的坦诚,她喜欢怡然温柔亲切的脾性,于是俩人不是一块哄孩子,就相约一起做美容,偶尔逛街,渐渐地形影不离了。
白皓注意到了,刚开始倒不在意,后来问起来翠华是干什么的,怡然如实禀报,他就嗤地笑了:“这样的人,你也和她为伍?”怡然辩驳举出翠华的种种可爱之处,白皓仍是固执地命令:“以后少给她来往,小身份!”怡然也不高兴了:“不要把别人都想得那么坏,我也不是没有判断力的人,你知道和太精明的人我相处不来的。”她想了想又问:“有一天,你很有钱了,会不会也金屋藏娇?”白皓一边笑她胡思乱想,一边又一次严厉地命令:“以后少和她来往,在这种人身边你能学到什么好?”
所以后来两人见面不免有点偷偷摸摸的,白皓在家她接到翠华的电话只说有事不能出去,他出门了,才慌忙带着孩子去找她,还得避开婆婆的眼光,暗笑自己真如干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不过就是个女朋友,白皓就这样!可是她通常在家里见他接电话,心里也不舒畅,“哈罗!陈女士,哦不,陈小姐,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压低了声音,有点款款情深,脸上的神情似曾相识,“想就对了,哪天请你吃饭啊,不,你知道我不会让女士埋单的……那批货可以吧,你要帮忙的,我请的饭可不是白吃的……哈哈,好好!”这些电话让怡然觉得极其窝心,而白皓连解释都没有,又坦然地坐在电视机旁了。回到卧室,怡然说:“你好有能耐哦,在女人堆里长袖善舞。”白皓冷笑道:“你不体谅我的难处,还吃这样八杆子打不着的醋!”一会,又把她搂在怀里“傻瓜,我对你的心你还有怀疑吗?以后别再有这种可笑的猜疑。”这是夹杂有甜蜜的安慰,还带点恩威并重的口气,这样怡然虽蹙了眉头,却说不出什么合情合理的话来。慢慢地她知道,在他们家里,白皓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不可质疑的。
怡然父母来的次数很是有限,原先对这个女婿就没好感,现在,是来到他的家了,双方都有点心存芥蒂,白皓不冷不热的态度,白皓妈那种多少带点倨傲的表情,明显女儿在这个家是并不做主的,怡然父母有点伤心,也有点不自在,所以往往住个四五天就走了。怡然妈拉着女儿的手,总是不知不觉地就红了眼圈,从小就当作宝贝的乖巧漂亮的女儿,如今真的是相隔天涯了。对女儿的处境她似乎也能看出几分,总不免要规劝一番:“他生意上的事,经济上的大权,你也要留意一点,虽说现在不缺你吃花的,谁能保证到日后,他当初能抛弃那个女人,你就敢保……俗话说得好,你有他有不如自己有,问丈夫要还隔层手哪,孩子,你要有点心眼啊。”怡然攀着妈的脖子笑道:“妈你多心了,白皓对我真的很好,经济上我心里有数着哪。”这样说着,心里对自己竟是叹息不已。后来,也曾问过公司的运营状况,投资的数目等,白皓一句话打发了:“你不懂,给你说说有什么作用?把儿子带好就是你的功劳。——多少女人想过你这种日子还过不来呢!”
白皓常出差,少则三四天,多则十天半月,这个时候,怡然常常被一种深深的寂寞和莫名的恐惧攫着心。有时她会问翠华的感受,翠华说:“如果说实话的话,”语气缓慢,似乎很冷酷的样子,“我一点都不希望他回来,如果不是还寄希望于钱——我不可能只有这一栋房子吧,孩子总归是他的,可是,吓!你知道吗,他比我父亲年纪都大,你说我会有多大的快感和他在一起,我是闭着眼睛……”闭上眼睛做出极其痛苦状,然后自己又笑了,“我拿青春做的交换那,有一天他死了,我才是出笼的小鸟呢。”怡然笑着打她:“死丫头,不要说这样的话!”怡然知道自己是不比翠华的,那是一个在苦环境里滚打出来的女子,对这个世界有了很多的免疫力,而她不是。
北京冬天的冷和他们家乡的冷是不同的,外边冷风飕飕冰到骨子里的凄寒,可是有太多有暖气的地方,地铁里,超市里,饭店里,自己家里,冬天和春天像只是一墙之隔,所以那种冷在无处遮蔽的地方,就仿佛冷的不近人情,回到家里,脱了一层又一层,穿着单衣单裤,隔着窗户看外边那个凄冷的世界,觉得格外隔膜,让她恍惚不安,这是一个玻璃房子,她的世界只有白皓和儿子了,万一有一天,是的万一,万一他有什么意外,或者很多年以后万一他有新欢,——啊,现在,她对他们的感情最多能保证个十年八年,或者更少,以后,如果有这些万一,她该怎么办,她想起她以前的家,至少她在易正身边是有安全感的,现在呢,不但失去了工作,还失去很多很多,虽然也许无关紧要,但毕竟那时她是坦然安心的。
夏怡然觉得大概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说不出的漏洞百出吧。
十六、幸福是朵什么样的花儿
在夏怡然眼里,北京的春天比起家乡的春天似乎要短暂不少,暖洋洋的太阳在风沙的搅合下时不时地透出点寒意,似乎在警告着冬天尚未彻底隐退,——而冬天真正遁形的时候,春天的鸟语花香适宜温度还来不及好好展示,夏天就就像一个愣头小子一样,冷不防地蹿了出来。北京夏天的灼热同冬天的寒冷一样,都带点嚣张的意味,且那步伐反而有意地拉长一些,秋天已经敲明叫响地宣布来临,商场里的夏装基本绝迹,学生们开始了另一个新的学期,连他们两岁多的孩子也被送进了幼儿园,可是夏日的炎热转变成秋老虎的猖狂,那种热,是一种急头急脑的,不耐烦又无可奈何的热,步子迈得真慢哪,秋天的秋高气爽还迟迟不见踪迹。
如今,真正的秋天也不怎么讨怡然的欢喜,依她的意思,儿子明年上学不迟,她愿意再多带他半年,白皓笑她落伍,至今他还对儿子六个月时,依了怡然没去到东方爱婴上课而耿耿于怀。虽然他带孩子玩的时间屈指可数,但是他白皓的孩子,在各方面的条件上,是不能输于别人的。白皓妈在孙子上学后,也回老家了,北京纵有万般好,也比不上她生活半辈子的小城,只有这一点上,怡然觉得和婆婆还是有那么点心有灵犀。
每天把孩子送走后,家里一下子就变得空荡荡了,地板已经擦得铮亮,所有的物件都各得其所,她躺在沙发上,电视的频道调来调去,总是没有合意的,韩剧不再新鲜,太现实的剧情看了徒增烦恼,综艺节目也不再那么有趣,翠华随那台湾人出国已有半年,她在小区里散步形单影只,一群老人围坐在那听京戏,京剧里总是有种无限江山的苍凉感,离她太过遥远;越剧里是痴男旷女的哀怨,让她更生幽怨;只有他们家乡的豫剧,好像那抑扬顿挫的声音里全都带有日常柴米油盐的可亲可爱,是与她亲近贴心的。有时自己在家里,拉上窗帘,她也会随着音乐唱歌,跳舞,突然,手臂僵硬,颓然垂下来,自己倒讪讪无趣起来,回到卧室,她倒在床上,看着阳光的影子在窗帘上慢慢移动,慢慢地移到那个古色古香的首饰盒子上,四周的空气就有点云烟氤氲的样子,她坐起来,抚摸着那盒子上的细细的雕刻,却是一种温良漠然的感觉,这个盒子总会不适时宜地给她一种温馨之感,而这温馨里埋藏着的是一种不可触摸的伤痛。
白皓的生意好像总不大如他的愿望,回到家里话也不多,自己在书房里噼里啪啦算账,白皓的世界就是过去,在她眼中也是虚虚实实,不可捉摸,现在愈发扑朔迷离,这绝对是一个比易正更加偏执的大男子主义,她看出他生意上的不顺心,问他几句,总是会被冷淡地回一声:你又不懂,知道那么多有什么作用!把孩子带好就是你的职责!在作情人的时候,他们还是势均力敌,现在,她觉得自己在他面前似乎要低到尘埃里去了——仿佛现在他的不顺利统统是她一手造成的,而且在他不经意瞥她的眼神中,似乎时刻在怀疑他所做的这种牺牲到底值不值得。怡然因为这种揣测,心里瞬间就会凄凉如水,他不值得,难道她就值得?!只有儿子,哦,只有她的儿子,是完完全全属于她,不需设防,可以倾心倾情地肆意去爱,当她带着孩子在小区散步,当周末的时候,白皓开车一家人去游乐场的时候,当白皓偶尔不再有应酬,两个人拉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她才体验到那总是虚无飘渺的幸福的滋味。
怡然对白皓表达出要出去找份工作的愿望,白皓皱眉说道:“我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花了?我对你说过无数次,把儿子带好,家收拾好,你的责任就尽到了!多少人想过你这种日子还过不到呢!”末了,他唇边浮出一抹笑意,“再说了,你出去工作,我还不大放心呢,谁再把你骗走怎么办?”这话可以当作玩笑话来讲,听到怡然耳里,却是种莫大的讽刺,她脸红了,扭头就进厨房,从此,再不提找工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