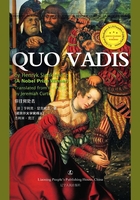回到我的小屋,已经吐了一路的诗人,仰面躺在我的小床上,断断续续说了一番话:“小……党!你……记住啊!咱……咱俩……现在……是朋友!等你……日后……成了名,咱……咱们……就不是朋友了,别说……你会对我怎么样,我……我都会……躲……躲你远远的!你……你们……这些唱歌的,都他妈……是戏子!素质……狗日的……太低!灵魂……狗日的……太卑贱!是经不住……名……名利考验的!不就是……成了个……名吗?名……是个什么……狗屁玩意!”
我想:这才是他今晚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让我颇感震惊的是:原来这位诗人骨子里头根本瞧不起我们这些唱歌的!
第二天上午,我俩在同一张小床上一觉醒来,饥肠辘辘,一起到村口吃早点,吃完之后,罗马用公话给他的一位关系很铁的大学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半小时后,这位在公安局当科长的仪表堂堂的同学便开着一辆桑塔纳来接他了。
临走,他还塞给我三百块钱——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我把他送到车上,紧紧握住他的手,有些动情地说:“大哥!记住我的话:咱们永远是朋友!”
罗马:现在,机会来了,北京在向我招手
我顺利接到了父亲,顺利返回了长安……但这注定将是一次我在事后不愿回首更不愿跟人提起的旅行,很希望它不曾发生过。
母亲身患绝症势必将改变我的生活,它所激起的我的第一个行动是:毅然决然一刻不等地从基地辞职了——向我的顶头上司并有过四载床笫之欢的女人辞职,真是一件太过刺激的事!好在她也快调走了——调到她丈夫所在的军区下属的单位去。没有正式调动工作的任何可能,我便拿着报纸去一些单位应聘,两个月后,进了一家新成立的《都市晚报》社,做了一名文体记者——我看上它的是工资奖金不低,以长安城里的收入水平来说,甚至可以算作“高薪”了。刚刚上岗,急于作出成绩,我为报纸做了一个好策划:想通过自己的私交约请著名歌星汉唐写一篇长篇自传(歌星写自传正是时下一大热),可以一边写一边在我报连载,最终由我报与出版社合作出书……为此,我克服了北京见面后的别扭心理,主动打去电话向他约稿,又没想到的是:他连一秒钟都未加考虑便一口回绝了——连婉拒都不是,是回绝!这回我没客气,立马反唇相讥:“好!你丫牛B!那就自个儿牛B着吧!我等着看你究竟会有多牛B!”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
到了这时候,我对此人和所谓“兄弟之情”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
时间过得飞快。
重返城市我发现:城中的时间比山中的时间要快得多,不经过。
一晃又是两年过去!
在此两年中,我的生活急剧地发生着变化:我结婚了,并用最快的速度做了父亲——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母亲,随着病情日益加重,母亲已知道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向我表达了想抱孙子的愿望,我便和她亲自介绍来的她的一位老同事兼好朋友的女儿结了婚,这女孩是一名军医,在四医大附属的西京医院工作,模样不难看,人也不讨厌,在我看来,有什么不可以结婚的?现在的我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生活的压迫已经消灭了我的自恋。更何况人家还很快给我生了个儿子呢!还让我母亲如愿抱上了孙子呢!结婚生子,也算是解决了人生中的两大课题。
事业方面嘛,也算有所成:报社的位置算是坐稳当了,工作关系也调进来了,还一不留神地混成了个“名记”,不光能写报道写采访,还经常写些文艺时评,主要以音乐评论为主,又是一不留神,竟混成了一位“著名”的“乐评人”……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报社这摊子只是职业而非事业——我的事业当然还是写诗,在此两年间,我一连出版了两本诗集,制造了诗坛上的轰动,经历了轰动后的成名,摇身一变而成“名诗人”。掐指算算,我还三十未到,连一贯严以待我近乎苛求的父亲都说:“儿子、本子(指出书)、票子(虽不多)……你都有了,古人云‘三十而立’,你基本上算是‘立’起来了!”
这是1995年,秋天到来的时候,我接到了发自于《诗刊》社的一份邀请函:请我去北京出席本年度的“青春诗会”——这个始办于80年代初的传统诗会享誉诗坛,有着“中国诗歌黄埔军校”的美誉,参加过该诗会的诗人意味着得到了官方和主流的承认,像我这个从“地下”从“黑道”杀出来的“急先锋”能够得此邀请,更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我是喜出望外,欣然接受,提前请假,准备进京——两年前的夏天那次窝囊不已狼狈不堪的进京记忆,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在心中暗发毒誓:再也不自去北京了,要去也得等它请我去——现在,机会来了,北京在向我招手!我可以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走一趟了!
大名鼎鼎的“青春诗会”竟在北京某高校的招待所里召开(这也恰好说明诗歌在当下的尴尬处境),条件虽然简朴,但与会者依然很风光:每天,在会议的议程之外,总是有人上门来找——找我的自然是其中最多的,有北京当地的诗人,还有诗歌爱好者,有个下午来找我的人尤其多,其中有两个还是我的大学同学,自然认得汉唐,便鼓动我把他叫来见见面,并得到在座者的相应——为了满足大伙想一睹名歌星真容的要求,我便临时放弃了此行不见汉唐的事先安排,用房间里的电话呼了他,他在电话里的表现尚存一丝余温,问我:
“你在哪儿?我马上过来!”
汉唐:好似昔日重来——可昔日又怎么可能重新来过呢
我也搞不清为什么或者说自己也不愿正视这一点:这二年——准确地说是自1993年夏天以来,我跟罗马的关系开始有些疏远了。只是偶尔打个电话,每次还得由我来打;他几乎从不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还在电话里不冷不热的,明显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激情澎湃热情洋溢的诗人,也不是那个古道热肠侠肝义胆的“二哥”了……我曾经想到过:这是否与他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当了爹有关呢?人总是会老的,一个先锋诗人一旦步入到世俗生活的轨道上去的时候,是不是就会一夜老去?我确实没有想到过自己这边是否存在问题——这人啊!遇事总是容易先想到别人的问题而对自己可能存在的问题不愿正视,尤其是在自己比较得意的时候。
这天下午,当他从电话中突然冒出来并说自己就在北京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几分惊喜!并有急于见面的心情(世事不像过去那样迫切了),有一些音乐上的想法我也想与之交流——我在北京这些年,也算是越混越开了吧?人一出名就越发好混了。见过的人也不老少,但说句老实公道话:还真没遇着一个像他这样能够并且值得交流的主儿!看来,罗马这号人也不是随便就能撞上一个的——我还是应该珍惜才是。
我带了足够多的钱,准备请他到高档餐馆吃顿饭。出门下楼打上车,直奔他说的那个大学招待所……未见其影,先闻其声:刚走到楼道里,我便听到了他那为我所熟悉的洪钟般的大嗓门,正在侃侃而谈,仿佛演讲一般,从某间屋子里轰隆隆地传出来……扑面而来的气氛让我感到分外亲切,但又感觉有点怪异和滑稽,好似昔日重来——可昔日又怎么可能重新来过呢?传出其声的那间屋子的门是大敞着的,我有点冒失地一步跨了进去,却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原来,这儿有一屋子的人!满满当当地堆在里头,都在听罗马布道——这太像在“S大”的时候了……我走进来,他没看见,还在那儿眉飞色舞地宣讲着他自以为是的“道”,唾沫星子四溅!
我站了一会儿,听他讲完,才笑着说:“又在布道哪?”
他恍然道:“你……来了?”
在场的其他人中有人跟我热情地打着招呼——我一看,都是故人哪!感觉很亲切,但也怪怪的,让我不知所措。
罗马是脱了鞋盘腿坐在床上开讲的(就像坐在炕上一样),坐在他旁边的那位主动给我让出了地方,说:“你们哥俩好好聊!”
我这才落了座。
掏出我的骆驼,递到他面前,他说:“对不起!我还是不习惯抽洋烟。”
我便自己点上一支,抽了一口,然后问他:“干吗来了?”
“参加诗会。”他面带其惯有的得意与自嘲相混杂的微笑说,“牛B哄哄的青春诗会终于请到我了!”——他的话激起了一片笑声……
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笑。我曾经也是一个诗歌青年,所以听着他说“青春诗会”感觉有点耳熟,但已有多年没有关注过这个坛子的事儿了,表现得有点麻木不仁——这似乎引起了罗马的不满,有点阴阳怪气地问我:
“怎么?老三,你不打算祝贺我一下吗?”
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便随口反问道:
“这么多人都来给你道贺——还不够吗?”
罗马默然无语了——我有点不近人情的答复为他的下一个反应埋下了伏笔。
罗马:如果我俩是因此而掰,分道扬镳,那就不庸俗了
我越发感受到身边坐着的这位爷的自私:长期以来,他早已习惯了周围的朋友把他当做“天才”一样敬着爱着呵护着,习惯于来自他人的关心而从不去关心他人——在他眼里:自己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人的事再大也无足挂齿……我不是到今天才发现这一点,只是到了今天,我对此已经失去了容忍之心!心里想的是:凭什么呀?
他进来之后一直做麻木不仁装,装B装得倒满像,只是当周围有人谈起他上市未久的第二张专辑时,他才活了过来:两只难看的蛙眼开始骨碌碌转动,耳朵也像兔子一样高竖起来,所有感官在一瞬间里全都打开了,仔细捕捉着与己有关的信息……我不是当着众人的面故意要扫他兴,只是觉得对待此人再也不必像从前那样客气,完全可以实话实说,无须遮掩,也不必再讲什么兄弟情面了(情之不存,面之焉附?)——我便单刀直入地说:
“老三,鉴于你一贯装B,连兄弟都不送,你的新专辑我只好自己买一盘听了——不好!没想到你的状态下滑得这么厉害,怎么一下子就给疲软了?都不太像摇滚了,歌词也写得语焉不详含混不清……有些歌我听了真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
此时此刻,我终于像我写酷评文章那样说话了,话痛痛快快说出来我才发现了一大事实:这二年(不止),我在给报刊写乐评时,对这位老朋友这位“自家兄弟”给予了批评豁免权:只表扬,不批评——现在终于把实话说在了当面。这位如日中天的红歌星,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来自于他人的批评了,一下愣在那儿,张了半天嘴才说出来话(也不叫我“二哥”了):
“胖子!你要觉得我疲软了,那我就疲软了——只是我在对软和硬的理解上跟过去不大一样,跟你更不一样——你愿意跟人斗就去斗好了,像毛爷爷说的那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斗争中显示的你的硬表现你的强……说句牛B话,我已经超越了这个境界!我跟人跟这个世界已经和解了!相看两不厌!”
也许旁人听不出来——他的话里很有内容,而且说得相当厉害,话锋很劲啊:其中包含着他对我的主要认识——与人斗其乐无穷,主要指的是我的诗与文。他竟然是这么理解我的?这就是他的认识水平?如此巨大的认识分歧他一直憋着不说,现在终于说出来了……此时此刻我想到的是:如果我俩是因此而掰,分道扬镳,那就不庸俗了!当然,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汉唐,你是不是在……吸毒?”
“我只抽大麻。”
“你最终还是免不了这个俗啊!”
“大麻是植物,不能算毒品。”
“你的高境界是大麻给你的?”
“就算是吧!那又怎么了?”
“我觉得你——问题大了!这么想你迟早会完蛋的!”
“你的乐评我基本上都看了,我感觉你还是在把你文学上的想法强加给音乐——说明你并不真懂音乐……”
“我承认我不懂,我写的所谓‘乐评’都是从文化建设和人生体验的意义上来谈的——既然我不懂,就请你明以教我:什么才是音乐?”
“操!你自己爱给人上课,又逼人给你上课,我从来就不喜欢上课……不过,说真的,你太不了解了——你知道那些老外都把音乐玩到什么程度了:在一辆汽车上装上一个黑匣子,等哪天这辆汽车出车祸了,黑匣子里的录音就是音乐——牛B吧?”
“不牛B!这就是你现在理解的——音乐?!”
“反正我现在要搞的是纯音乐,不想那么苦大仇深,不想那么忧国忧民……我记得当年在你们学校的时候我就对你说过:我要做的是贝多芬!我记得你还有点不以为然不屑一顾……”
“实话告你:我现在听了还是不以为然不屑一顾!你记住我的话:你跟贝多芬搞的是两个行业,别以音乐的名义生拉硬拽在一起,你现在的想法嘛,就更是跟贝多芬八竿子打不着了!”
如此碰撞的结果也只能是不欢而散了:他说了“我想请你吃顿饭”,可是晚上我另有安排:来的这拨朋友搞了几张人艺新剧《北京大爷》的票,我大学毕业离开北京之后就再没看过话剧了,不想为他而放弃(他也不想随我们去看演出)——更大的真实是:即便今晚无事,我也宁愿跟这拨诗友聊诗而不想听他再扯什么黑匣子音乐了……便说:“那就算了吧——我心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