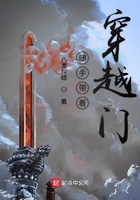“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江虨无奈地看着眼前慢慢吟出逍遥游的少年,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这里阳光明媚,透亮的光辉从窗纱掠影,洒进这间房屋之中。这间房屋在江府之中也算的上隐蔽。从江府的大门进入,穿过一片假山荷池,两边是抄手游廊,中间是正堂。正堂之后是穿堂,放着一只紫檀木架子的大理石屏风。后面则是内屋,几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垂花拱门后面是花园,花园之后是厢房,又有小路通幽,禅房花木,江虨几人此时所在的房屋,正在花丛掩映之中,是江家待比较亲近的客人所在的房屋。
是的,此时坐在江虨身前的除了自己的仲堂兄江恂之外,还有另外三个与之年纪相仿的少年。一人江虨之前见过,正是高子远的独子高坦,另一人江虨还是今日第一次见到,据说名曰蔡裔,乃是圉县蔡氏族人,最后一位,自然是江恂的弟弟,江彰了。
江虨面前这四位少年,以江虨观之,自是各有风貌。堂兄江恂,不愧甚肖乃父之名。在江虨面前吟诵逍遥游的少年,便是他了,真与江勖相似多矣。高坦,自坐那之后眼睛就一直往江虨这里瞟,眼神中带着掩藏不住的好奇,这可能就是咱的堂兄把咱带来这里的原因吧。
至于江彰,听着江恂吟诵逍遥游,也不能说不耐烦,只是眼神总是游移不定,可能他对摆在面前的投壶的兴趣,比他兄长吟诵的章句更大些。最后一人,蔡裔,身着白色深衣,宽袍长袖,好一位俊朗少年。胳臂有力,手掌修长,眼神中带出了几分凌厉之气。听他们刚才所言,这蔡裔是长乐太守蔡士宣之侄,是阴平太守蔡宏之孙,是蔡邕的曾侄孙,也算是名门望表。
至于江虨堂兄江伦,可能是在他房中读经,不在此处。
江虨中午刚见过老太太,下午正要去私塾继续念论语,却不防老师家中有些事情,因而让江虨不必去私塾,自在念书则可。江虨堂兄江恂听说了这件事情,恰逢高坦与蔡裔前来拜访,便不由江虨分说把他拉来这里,听四人谈天说地。
据江虨观之,这四人之中,便数蔡裔最有才能了。不是江虨灭自家志气长他人威风,实在是自己的堂兄江恂,听他谈老庄,不过中人之才罢了。略有点薄才,还是在诗赋上面,故而他对自己也略有亲近。但比起王粲左思,还是别比了,差远了。另一位堂兄江彰,不过十岁少年,生性又好动好玩,不好这些清谈,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才能,或许技击之上,略有一点微末的技能罢了。再有就是,江家的优良基因,倒是给了他一副好相貌。
说是好相貌吧,但也不算多好看。不说比江虨,比起江恂甚至都差了不少。而旁边的高坦,说一句中人之才江虨觉得都是看在他是自己粉丝的面子上了。实际上,他诗赋作的都没自己的堂兄江恂好,也就长得比江彰好看点。
四人之中,最为有才的,还是那至今不怎么发言的蔡裔,他几分凌厉的眼神中带着玩味,偶尔打量着江虨,竟让江虨觉得有些刺痛感。他言谈虽不多,然声如雷震,其中亦暗含哲理。
玄理之中,若让江虨点评,自是蔡裔不知超过另外三位少年有多少了。而武勇之上,看着另外两位弱不禁风的样子,江虨眼神转向了江彰,打量了两眼,顿时砸了咂嘴吧。这也不怎么样啊,那深衣之下掩藏的肌肉,看起来堂兄江彰就不如这蔡裔。
“”如何,吾弟,觉得汝兄之言逍遥游,尚有玄谈哲理否?”江恂摇头晃脑地大发一番议论后,目光转向了江虨,兴致盎然,想听听江虨点评的意见。
呃,江虨嘬了嘬牙花,看来这位堂兄把自己拉过来就是为了炫耀啊。刚才议论诗赋,这位堂兄就想让自己当场赋诗一首,以惊众人。然而江虨自家知道自家事,以近日多学论语,无有灵感,兼之佳句难再得拒绝了。如今清谈玄理,这堂兄又让自己点评,噫,该说什么好呢?
刚才听四人谈老庄,江虨也不是没有往心里去。通观下来,江恂常常长篇大论,多以话语,却不能言之切然。常常无用之论,抛之弥繁,辞达之言,吐之弥少。高坦这位仁兄,言辞华丽,略有骈赋之风。然其排比铺陈,江虨听来用的都十分尴尬,不过意象堆砌,无有通贯之感。江彰且不去说,因他不曾发一言,又如何去评价呢?至于蔡裔,言辞不多,却常常切中要害。声高音宏,自带一股气势。至于玄理通达,江虨难以评价,只觉他说的比另两位仁兄有道理的多,跟自己前世语文老师解释这逍遥游虽然言不同,然意有一些相通。
但这要自己怎么说,总不能打击这两位兄长的自信心吧,也不能伤了自己这位小粉丝的心吧。那句话怎么说,胳膊肘不能向外拐啊。目前看这四人,除了江虨堂兄那三人,就连蔡裔也是目光流转在江虨身上,眼神中也没有不以为然。看来江虨那首诗中天外一思玄句也让蔡裔略有重视,对他的评价也不太会忽视。
纵然江虨一二岁幼童,然能出口赋诗,暗含玄理,便比他们这十岁谈玄更为不易了,怎能以其年幼,可能未读老庄,便认为其未通玄理,不能点评自家呢?江虨感觉蔡裔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那要怎么说呢?泛泛而言,或者直接拒绝,定会让眼前蔡裔看轻自己。就算最好的情况,也可能认为自己嶷然稀言罢了。虽然酷肖吾父,但这不是我想塑造的形象啊。
江虨暗暗思考着,忽然,他眼珠一转,淡眉一挑,想到了一个方法。
“几位兄长世兄且先别急,”江虨笑吟吟地开口了,“我一垂髫幼童,未读老庄,纵玄理之妙,令我闻之,亦觉清味雅然。然吾之未尝能谈玄理,其理明也,又如何能够点评四位兄长之玄谈呢?”
顿了顿,看着江恂似要插话,江虨连忙将话接了下去:“然兄长之命,不敢辞也,此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义。我闻前朝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叔慈侄孝,兄友弟恭,方能鼎沸如汤沐,华盖运交,天下知名。故而兄友弟恭之义,自古然矣~”
江虨这段话说完,其他人尚未如何,蔡裔的眼神中顿时散发出难言的光芒。也不知这江家幼童如何理解的,汝南袁氏,袁本初袁公路各据一方,互相交兵,如何可称兄友弟恭。却不知江虨这段话便是在顽笑。江虨如何不知袁氏叔侄兄弟,只是在说到兄友弟恭,不自主就想到袁氏这一对活宝,此时不玩梗,简直愧对自己啊。反正看着面前的四人,好像也只有蔡裔懂了自己的意思。至于另外三人,毕竟汝南袁氏鼎盛时期距今已有一百年了,虽然面前的高坦家祖之一便是袁绍女婿高干,但毕竟汝南离陈留不近,又时光磋磨,纵然家中长辈偶尔谈起前朝袁氏,他又不一定尽听,长辈又不一定谈袁绍袁术兄弟相争。故而看他面上,应也是不知这段往事。
果然无才矣,江虨暗暗叹了口气,但无才也没办法啊,自己也不能贬低他啊。纵然自己会得一个识鉴美誉,但这关系就坏了。“以小子微末学问,闻诸位兄长倾谈玄理,实在如闻邵乐,如闻仙音,若兄长们不止,小子真不知今夕是何夕了。不过,小子偶有听下人传谣,以之形容诸位兄长,倒觉言辞恳切。”
“哦?是何谣?”江恂果然被勾起了好奇心,就连蔡裔也是眼眸略弯,掠过一丝惊异。
“陈留四英皆俊英,高才卓砾容止清,江氏二郎文武备,高君昳丽蔡君灵。”江虨笑吟吟地说出了这四句歌谣。说是下人们传谣,实际上江虨哪里从下人们那里听过啊,还不是他自己现场编的。只不过虽然江虨身为一个二岁幼童,也不想背上识鉴不明的名声,再加上自己编谣吹捧兄长总是有些不好意思,因而假托下人之名而作。至于你问咱哪个下人?不知道啊,等今天过后,咱就把这个歌谣传唱出去,到时候谁还知道源头在哪里?
这也是江虨刚才想出来的办法,既然不好批评,那就都吹吧。你高坦玄谈不行,我吹你容貌昳丽,你江恂江彰没什么特别的才能,那你们总有偏向,一文一武,文武皆备,多好。至于蔡裔,那就是真心诚意了,赞扬你灵。所谓灵,既有圣明的意思,也有灵敏,聪明的意思,江虨记得钱起就写过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灵总是一个好词。
然后,把四个人捆绑,这就是江虨的私心了。这歌谣若是传唱出去,陈留四英的名声应该就会坐实。反正大多数乡人都没见过他们四个,哪知道谁有才谁没才,歌谣朗朗上口,只要一传唱,四人就捆绑成陈留四英了,到时候出去吹也好吹啊。虽然其中三个都没什么才能,但起码面相上都是过得去的。再说有蔡裔这个真有才能的人在,看来他才是文武兼备,最基本不会拉胯。
毕竟,魏晋的这些名士,其实跟江虨前世的偶像团体没多大差别。只不过偶像团体靠的只是颜,魏晋名士不但要看颜,还要看才,还要看德。江虨记得他们蔡家的蔡谟就很有名,所谓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这中间的葛,就是自己未来的老岳父啊,不过也可能不是,咱还没见到人家诸葛文彪呢,总要看看她好看不,可爱不,对吧。
你看这陈留四英,高坦有颜,蔡裔有才有武,江家这两位吧,起码有德不是,毕竟也是江氏子弟,家风熏陶。
这偶像团体,不是,名士雏形不就搭建起来了,四位少年,本来就需要乡里扬名,才能在乡评里选中获取优势,因而必然不会反对这歌谣的传播。看眼前自己堂兄江恂惊喜的样子,看江彰那不甚在意的眼神终于变得郑重起来,看高坦那俊朗的外貌一脸臆笑,就能知道了。虽然看蔡裔眼神略有不满,略有不以为然,不过毕竟也只是一十岁左右的少年而已,虽然不称这几位同伴的才能,但总有几分交情所在,就算自己没交情,家里也有交情不是。再说这歌谣也不过是下人传唱起来的,其中略有溢美,不实,自己也不能跟江家下人计较是吧。
再说了,江虨开始那么谦虚,然后说这首歌谣比较贴近四人,这首歌谣又将四个人都夸了一遍,确实是令人不好掀桌。
“江家门风,便连下人都如此有才,有赏鉴之能,”高坦连连叹息,颇得其父之风,那俊秀的外表,甚是唬人,“我今儿真真的见了,陈留四英皆俊英,高才卓砾容止清。江氏二郎文武备,高君昳丽蔡君灵,好谣也。”
“当传之乡里,令乡人亦知也~”堂兄江恂倒真是不知脸皮为何物,江虨暗暗吐槽道,竟然如此没有自知之明。
不过这也是江虨想要达到的效果,因此违心的点了点头,笑着道:“二兄之才能,高世兄之美容,蔡世兄之文武全才,本就应让乡人尽知。更何况此歌谣如斯贴切,若能传之乡里,陈留四英之名,人尽皆知也。”
“是哉,是哉~”室中充满了三人欢快的大笑,至于江虨和蔡裔,则附和地假笑了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