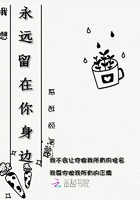“怎么会是毒药?”黑甜惊讶道。
“在我还小的时候,父亲就为我请了一个能干的厨娘,教我制作饼饵。我唤她作师傅。”
“师傅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说:糖是穷人的一剂良药,富贵之人偶尔食之,可以驱除愁闷,抚慰心灵。而对以制糖制饼为业之人而言,若不加节食地食糖,那它就是一剂慢性的毒药,日久年深,足以致病,甚至夺人性命。”
“她为我立下规矩,日后若是制饼煎果,只可品尝少许,绝不可多食!”
“这是为何?”黑甜不解道。
“若是非要一个理由,还是那句——物极必反!适量怡情,过量伤身。如同饮酒、‘打马’(麻将的前身)、掷骰子!”
“想当年,我在大户人家的蜜煎局做事,嫁到黄家后,虽未以制作饼饵为业,然而每逢庆典也少不得要做些。若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只怕早已患病,哪里还能像如今这样,站在你面前好好说着话。”
“既是如此,我又何必学了这些制饼煎果之术?更不应以此谋利,挣了别人的银钱,还让别人患上疾病。”黑甜皱紧眉头,心里隐隐觉得失落。
“话虽如此,又岂可因噎废食,饼果还是要制!”黄罗氏微笑道,“想想看,饼果给黑甜带来多少快乐?”
黑甜点点头,道:“黑甜嗜甜,人尽皆知。”
“为人制饼,其实是为人制出快乐!即便以此为业,也是在售卖快乐,有何不可!”
“入口之物中,岂止糖有此害,过量皆能致病。你只需提醒他们,适量食用即可!我师傅立下的规矩,你也须谨记在心。”
“我记住了!”黑甜听话地点点头,黄罗氏这才松了口气。
第二天,黄罗氏便将黑甜带去厨房,教她制饼之术。黑甜聪颖,很快将饼做得香甜酥软,品尝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
这边,初何的婚事还在向前推进着。
虽说彼此已经相识,礼俗不可更改,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样样不可少。
炳炎一家人还是去‘过眼’了。相好之后,男方家人担着盛有少许酒的大酒瓶,装八朵大花、八枚手作饰品,用花红系在担子上,送往女家。
女家则用两瓶淡水,三五条活鱼,一双筷子,放入送来的大酒瓶内,用这“回鱼筷”作应答。
到了下聘这一步,炳炎一家颇费了些心思。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是水珠儿出嫁时,将得到二十亩良田作陪嫁。
既然女方大方如此,黄家长房的大郎娶妻,聘礼自然不能显得寒酸,让旁人小看了去。
炳炎本就好面子,此时更是咬了牙要重下聘资。征得黄罗氏的同意后,典了十几亩上好的田地,加上家中多年积蓄,出金五钱,银四两,彩缎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
又打了金银钏、金银鍉、金银帔坠,即俗称的“三金三银”。
老二炳乾的脸色有些个不好看,还是桂兰宽慰他道:“我们的幺儿还小,冰语和翠夏两个丫头出嫁也要等个几年,到那时,典出的田地早已收回来了。”
“再说,有的出还有的进呢,水珠儿的二十亩良田不可小觑。算起来,我们也不吃亏。”
“公公不在了,现在黄家上下全由婆婆作主,我们也不好说什么。”炳乾听了,觉得在理,这才颜色稍解。
老三炳坤自是不会反对。从小到大,黄罗氏的话他没有不听的。倒是有些担心过不了秀芝那一关。没想到秀芝难得通情达理了一回,不但不计较,反而直夸炳炎做事大方得体,为黄家挣足了脸面。
“实在奇怪得紧,”秋云将一块喜饼塞进嘴里,吃得津津有味,还不忘排喧秀芝几句,“这太不像她!都说事出反常必有妖,我看此事不简单。”
“哪有那么多妖来?我看你是想多了!”黑甜心想,秋云最是个爽直、心无丘壑之人,不知为何单单跟秀芝较着股劲。
“如此美味的喜饼,竟是你做的?”秋云惊奇道,“桂花的香味极浓郁!以前阿奶也说加了桂花,可总不比这回的更明显。”
“用了金贵的白沙糖来制饼,通共就这么几个,能不好吃?白沙糖清甜,不会夺了桂花的香气,自然就明显了。”
黑甜看着下面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的大人们,忍不住地发笑——她们正坐在屋顶上玩儿呢!
秋云喜欢坐在高处看风景,常把黑甜也捎上。换个角度视物,就算是最熟悉的风景也变得跟平时很不一样。
“饼的样子也俊,上头还有一男一女,就像哥哥和未过门的嫂嫂!”
“我特意挑的饼模!还有‘鸳鸯戏水’、‘凤穿牡丹’两种样子的。”
“你真应该在东市上开个饼铺,生意一定好得很!”秋云咬下一大口饼,细嚼后,不由得闭上眼睛,脸上绽出一个无比惬意的笑容来。
“我也想啊,可饼铺不是想开就能开的,那需要本钱!”黑甜轻叹一声道。
“我听说,阿奶把她那个宝贝箱子给了你!”秋云换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里面竟是一箱子的饼模!你知道吗,在这之前,阿奶从不让人碰它,没人知道那个箱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阿娘和二婶婶说,那里藏着阿奶当年的嫁妆,秀芝最财迷,竟说那是一箱子的金银珠宝!”秋云轻笑一声,“细雪说,那里藏着整匹的蜀绣——”
“我倒想知道,你觉得那箱子里藏着什么,定是人人都想不到的稀罕物件!”黑甜笑道。
“我自小就在想,那箱子实在神秘得紧,说不定就是个魔盒!人若钻进去,就像穿过一个山洞,山洞的那头,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天地了!”
“完全不同的天地?你是说到了神仙住的洞府?”黑甜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以前我跟你想的一样,可现在——不一定非是神仙的洞府,也许就是人世,不过不是现在,而是过去,像前朝,前朝之前,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
“或者不用那么久,就是一年前,数月前,昨天!我真想回到过去看看,哪怕只是看看昨天的自己!”秋云若有所思道。
“我知道,你的小鱼儿上月没了,你是想去看看它!”小鱼儿是秋云养的田园小犬。
秋云默然良久,才说:“我是想回到过去看看它,它走得突然,我甚至没来得及跟它道别。”
“我待它并不算好,想起来总觉得后悔。”
黑甜心想,煜华公子也一定有过这样的想法……桥头上的那簇火光在她脑子里一闪而过,嘴里却说着:“它一定游入了大海,变成一只幸福的小鱼儿。”
“如果真有这样的魔盒,我倒更想到以后去看看。想看看以后,是不是家家都能吃上白沙糖!”
“家家都能吃上糖!那岂不是家家都是有钱人了?”秋云突然哈哈笑起来,“怎么可能!都说我的想法如同天马行空,我看你才是异想天开呢!”把刚才的烦忧瞬间抛诸脑后,竟把黑甜惊得一愣神。
“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外婆也说,物以稀为贵。如果人人都能吃上糖,那糖就变得不稀罕了,说不定那时的有钱人反倒不吃糖呢!”
秋云笑得更厉害了,前仰后合。黑甜只管抬头看着天上的流云,沉浸在对未来的无尽想象之中……
黄家下了重聘,水家也极爽快,除了珠翠缎匹、花红礼盒,果然还随嫁了良田二十亩,一时在遂州城郊的十里八乡传为佳话。
到了迎亲的前三天,男家开始送催妆花髻、红盖头、花粉盘、花扇、画彩线果等物品,女家则回送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等,备好被褥帐幔,又去男家铺设房奁器具。
为了“铺房”,黄家的人几乎全部出动,秋云、细雪她们自不在话下,黑甜也跑前跑后地帮忙备床席桌椅。
到了迎娶那一日,黄家请来的几个乐人吹吹打打起来,一时欢天喜地,热闹非凡。
黑甜、秋云、细雪,还有同族的黄姓姐妹们,都是十来岁的年纪,由年长些的亲戚们引领着,各拿花瓶、照台、灯烛、香球、裙箱、妆盒、衣匣、青凉伞、交椅等物,跟着送“迎客”的花担子前往女家。
细雪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围观,心里一慌神,脚步突然乱了,差点把自己绊倒,秋云忙腾出手去扶她。
“没事儿吧?”黑甜忙问了句。
“还好!今儿太忙,没顾上吃早饭,人也太多了些!”细雪额上尽是细密的汗珠儿。
“成个亲竟麻烦至此!”秋云抱怨道,“换作是我,什么都可以省了,聘礼、嫁妆、铺房、迎亲队伍……我只要黑甜的喜饼!”
“还有新郎官!”黑甜回了句,三个女孩嘻嘻笑起来。
待迎亲队伍到了女家门口,女家自有人将他们请入后院,卸了礼物,又用酒礼款待,并散“利市钱”,孩子们顿时哄抢起来。
此时乐官忙着作催妆乐,克择官报着时辰,茶酒司仪互念诗词,促请新人出屋登车。
约摸过了半个时辰后,一身吉服的新人终于被搀扶着走出家门。登上车,轿夫却不肯起步,直到女方家赏了利钱,轿子才起动了,朝男方家走去。
迎娶的人先回男家门口,又吵吵嚷嚷地拦门,向男方要钱物。有人还唱起来:“拦门礼物多为贵,岂比寻常市道交。十万缠腰应满足,三千五索莫轻抛。”
黄家亲戚不知是谁接了句:“洞府都来咫尺间,门前何事苦遮拦。愧无利市堪抛掷,欲退无因进又难。”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阵阵哄笑声。
拦门过后,媒人拿着一碗饭,叫道:“小娘子,开口接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