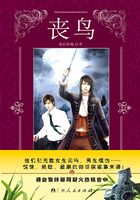蔡云德垂眸,视线落在她白皙的手指上。
她正沾湿一块绵团,弄了些酒精,在给他的瘀伤消毒。然后再小心翼翼倒出跌打药水,手指稍微用了点力气,给他在瘀伤上揉散。
她的动作虽然称不上特别熟练,但比第一次给他上药时不知道进步多少。
他抬眸,视线再次落到她脸上。
大概因为这次他伤得并不重,都是些皮外伤,所以她没有太惊惶的表情,只是有些哀伤的模样。
他按住她的手,“我来吧。”
他没回答自己的问题。
沈灵的手一顿,没有挣扎。
其实答案他早说过很多次的。那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常态,他所处的环境。沈灵默默站到一旁,不再强求他的答案。
“谭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接下来会有一场正式的公演。这些天,我可能要花费很多时间在排练上。”她主动坦白。
蔡云德的动作一滞,没说话。
沈灵不喜欢两人之间的这种沉默,很无力,明明很想要做点什么去改变,但却什么都没办法做。她永远无法接纳他生存的方式,而他也无法融入她安稳的生活。
‘分手’两个字在嘴边徘徊许久,才想起,自己其实是来道歉的。
“对不起,那天没有及时赴约,让你不开心了。”
蔡云德神色淡淡地将衣服穿上,抬眸问她:“如果再来一次,你依然会那样选择,对吗?”
这话将沈灵问得哑口无言,也彻底将两人稍微缓和一些的关系,再次推入冰点。
沈灵按住发酸的鼻子,努力让自己没那么难受,“对不起,我做错了,我跟你道歉。你饿不饿?我特意去买了点菜,可以给你煮饭。”
蔡云德沉默了许久,才声音干涩道:“我已经吃过了。”
连做饭都不被允许了。
沈灵垂着脑袋:“那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
她背过身去,往眼睛上狠狠揉了一下。
直到关门声想响起,直到脚步声渐渐消失,蔡云德空落落的心终于有风狠狠灌进来。
她没有给出她的选择,但他已经猜到。他是被忽视那一个。他难受,却毫无办法。
他摊开身子倒在床上,丝毫不顾牵扯到伤口的痛意。
他和她,怎么忽然哪哪都是矛盾了呢?
之后的几天,两人短信电话都不通了。两人似乎都在给对方一个冷静的时间,沈灵在这段冷静的时间里没有闲着,她拼命地压榨时间练琴,不方便频繁去排练,她就在家里练习,实在要去排练时,她就只能扯谎同学有邀请。
蔡云德也没有闲着,虽然啃下码头那么一大块香馍馍生意,但有道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因为没沾手过码头生意,上手难免有难度,而且为了防止新抢来的地盘守不住,他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跟头儿在重新调整人手。
当然,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地盘是蔡云德抢来的,说好听点是手段高明,说难听的,就是阴来的。本身他们混混出身最不怕的就是打架,阴来那么大个地盘,之前豪爷的手下当然不服气,时不时都会来砸场。
而今天晚上的这次砸场,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
人数高达百人之间的斗殴。
人群中,打得最猛的当然仍然是蔡云德。尽管他是被伏击的一方,可他的气势却更像是进攻的一方,手里抄着小板凳,势如破竹,好几个人一起围攻就没办法近身。
有个胖子特别不怕死,试图用人肉当盾牌,跳起来直接往蔡云德砸过去,那么重的吨位,蔡云德自然是扛不住的,让他给撞到地上,差点没压出一口老血来。
豪爷的那些手下纷纷趁机冲过去,拳脚都往蔡云德身上招呼。
“云哥!”耗子急得不行,偏偏自己没办法走开,他也被几个人给围住了。
蔡云德反应还算机灵,抄起手边的凳子砸过去,往旁边一滚。但转眼,一根木棍敲过来,重重打在蔡云德肚子上。
蔡云德闷哼一声,死死忍着,一脚那人踹翻,然后他捡起那根木棍,双眼猩红一片,煞气满满,冲到人群里开打。
这一架,愣是打了一个小时。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斗得不可开交。最后,蔡云德这一方以微小的优势获得了胜利,直接将带头伏击的那人揍得脸被按在地上摩擦。
救援的兄弟们终于赶到,蔡云德整个人仿佛死过一回,瘫倒在地上,身上分不清是别人的血还是自己的血。
事情闹得非常大,最终,还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大批人慌忙撤退,谁都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事情被拉到警察局里喝茶。
蔡云德在耗子和东子的搀扶下,离开现场。
他们转移到附近自己的地盘,一个比较安全的酒吧。蔡云德躺在沙发上,脸上几乎已经没办法看了,眼角和下巴被揍出一大片瘀痕,昔日的帅气都没有了。
耗子和东子也伤得不轻,但耗子还是勉强撑着身子翻过来,问他们两个:“云哥,东子,你们还好吗?”
东子累得不想说话,手摆了摆,相当于是回答,我还好。
蔡云德伤得比较厉害,毕竟那些人的目标是他,狠招都是往他身上招呼的。他手都抬不起来了,话也没力气说,只轻轻哼一声,表示自己还好。
耗子叫来自己人送来医药箱,爬起来道:“医院肯定是不能去的了,警察那边最近盯咱们也盯得很严。咱们还是不要冒险了。委屈点,自己随便弄弄就成。”
豪爷的事情闹得很大,不仅仅是江湖上轰动而已,警察那边也是有关注到的。近来警察频频关注他们的动向,大有看情况不对就把他们一窝端的架势。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这段时间做事比以前谨慎很多。
但再怎么谨慎,该打的架还是要打。就好像今天晚上,虽然明知道会招来警察注意,但根本没办法不打。
耗子将医药箱里的跌打酒什么的扔给东子和蔡云德,三人就这么静静地喘着大气,给自己涂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