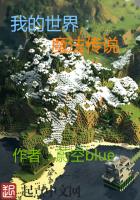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看来四字有害,不如一笔勾销。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断人稀。无财世路难行,无气反被人欺。看来四字有用,劝君量体裁衣。
刘芙与弟弟妹妹们作了个比较,发现贪富差距明显,她的心理落差很大。一股寒意从脚底涌上心头,刘芙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倘若余毅以后继续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自己一家人终将会沦为城市贫民,在生活品质方面,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刘芙心烦意乱,闷声不响地坐上了刘子墨的摩托车。
刘子墨回过头来对抱着盼归的余毅说:“毅哥,你过来,把盼归放在大姐怀里,胜利哥马上就到了。”
说话间,邝胜利已到跟前,他面带着微笑用力地朝余毅招了招手说:“大姐,毅哥,过年好,毅哥,你快过来,上我的车。”
“胜利兄弟新年好,你先掉个头,我马上过来。”
邝胜利骑摩托车的技术并不过硬,不会原地掉头,只会转大弯掉头,等他掉完头,刘子墨已到了和平。
刘子墨一路狂奔,不一会儿,就回到了家中。
邬星和隔壁的豹子和彪子在板格(打撇撇),邬月在刘子墨的房间里嗑枯豌豆听音乐,邬梅逗弄着刘丽怀中的小秋月,小秋月“哦啊”反过来逗邬梅,倒把邬梅逗笑了。
两岁多的小盼归听到音乐,从刘芙的怀里挣脱,随着音乐的节拍,跟着扭动起来。
刘子墨笑道:“盼归,你还听得懂音乐?你们看,他还蛮有节奏感的。”
邬梅扭过头来,朝余盼归张开双臂,笑着说:“乖宝贝,快过来,让丫丫抱抱。”
余盼归也张开双臂朝邬梅扑了过去,甜甜地喊了一声:“丫丫,新年快乐!”
“谁教你这么说的?看来,这个压岁钱是免不了啦!子墨哥,快把封筒拿来。”
“盼归,你要改口喊舅妈,喊舅妈,我给你个大封筒。”
“舅妈,新年快乐!”
“好,这个是你的,这个是小秋月的。”
“我们两个的娃儿都有小名,秋月叫盼盼,盼归叫么事?”
“盼归叫睿睿。”
“秋月叫月月不好听吗?偏偏叫盼盼,很容易和盼归搞混,改个别的小名不好吗?”
“那就中舅娘的叫月月,哦!月月,月月好乖哟!”
“睿睿,你今年几岁了?”
“三岁,我快三岁了。”
“你最喜欢哪个?”
“喜妈妈,不喜爸爸。”
“喜不喜欢舅娘呢?”
“喜舅娘,舅娘美美。”
“你们听,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喜欢美女。”
“食色性也,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是个男人都逃不过酒色财气四个字,佛印在相国寺曾题诗一首: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余毅肚子里墨水不少,随口说道。
“我记得关于酒色财气,苏东坡也题诗相和过:饮酒不醉是英豪,恋色不迷最为高。不义之财不可取,有气不生气自消。”刘子墨难得有机会表现,也借机卖弄了一番。
“墨儿,你对这四样都沾过,最有发言权。”
“我是酒中之神,色中饿鬼,财中之霸,气中之王,论酒量我无人能敌,论色暂不可提,论财是自带三分财运,论气是一气之下把人打成残疾,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你的酒量大,容易心生傲气,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得罪人,对你来说,酒量大并不是好事;你用色中饿鬼来形容自己更不可取,两情相悦,应当细水长流,不可饮鸩止渴;钱财似水,悖入悖出,来得快,去得也快;为人不冷静,不计后果,冲动莽撞,遗害无穷。这些事情,你都应该反思一下。”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在学校里教书的这段时间,就深有体会,可能是因为喝酒,我抢了校长徐苟四的风头,在徐苟四的授意下,那些同事拼了命地打压我,排挤我,孤立我,我哪里是在教书,纯粹是在找气受,现在听了你这番话,才明白症结之所在。”
“所以你要时刻反省自己,在酒色财气四个方面,把握好尺度,你才能成为人生赢家。”
“这个尺度应该怎样把握呢?”
“有人将酒色财气作了个总结,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看来四字有害,不如一笔勾销。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断人稀。无财世路难行,无气反被人欺。看来四字有用,劝君量体裁衣。酒可以喝,逢知己而饮,适可而止;色也可以沾,只能当菜下,不能当饭吃,有好多皇帝都是英年早逝,全都是因为房事过度,将身体掏空,才导致命丧黄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贪财,损人利己,少攀比,不仇富,活出精彩的自己;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字头上是把刀,有时候是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损尊严,坏形象,拂我逆鳞的事,是坚决不能忍。”
“我不攀比,也不仇富,毅哥,这录音机上的歌比妈妈唱得好听,音乐比你吹的单音好听,回家后,我们买个录音机,这摩托车风驰电掣,比自行车快得多,我想在沿湖大道上飙一下车,回家后,我们买一辆摩托车,梅儿身上的这套衣服很漂亮,我也想买一套,能问问,录音机多少钱吗?摩托车多少钱吗?梅儿身上的这套衣服多少钱吗?”
“梅儿,录音机是多少钱啦?”
“录音机是800块,电视机是1400块,总共是2200块钱,我们卖BP机的钱,还多出了五百块钱,你不记得了吗?”
“对,还有BP机,你要是找不到我们,或者我们找不到你,都可以拨打BP机呀!买一部BP机要多少钱?”
“大姐,你不要激毅哥,毅哥的工作并不是挣大钱的那种,现在大环境不好,并不是人人都能挣到钱,你们家三个职工,日子过得那么安稳,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你是吃根灯草,说话轻巧,三个职工怎么啦?爸妈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六七百块钱,毅哥一个月不足两百块钱,全部加起来都没有一千块钱,还比不上胜利一个人在外面挣得多,你说有什么意思?”
“不会吧?我看到的那些老师们好像都很了不起,高高在上的样子,赚这么点钱,怎么能养活一家人?”邬梅觉得不可思议,她不清楚为何这些师尊长者,居然会如此清贫,便插了一句嘴。
“你问问他,看这些年,他们都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在乡下,我们有粮食吃,有瓜果蔬菜吃,常年不缺鸡鸭鱼肉,水产品不断,可以换着花样做好吃的,他们是一日三餐除了稀饭馒头,就是白菜、萝卜、菜苔、菜心,换着花样吃乡下人喂猪的下脚料,我不挑食,倒也无所谓,要是你们中间的任何人在那里生活,可能一天都呆不下去。”
“毅哥,大姐说的都是真的吗?小盼归也是这样生活的吗?”
“没有你大姐说得这么夸张,我们一个星期,还是有一顿肉吃的,鱼经常可以吃到,你看小盼归长得多可爱,像缺乏营养的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安贫乐道也好,不是有这么几句话吗?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过那种与世无争,恬静平淡的生活,夫唱妇随,恩恩爱爱,也可以羡煞旁人。”
“现在不是古时候了,大人倒也无所谓,我的孩子能低人一等吗?”
“我们家是诗书传家,怎么就低人一等了?不是什么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你太俗了。”
“我就是个乡下人,能不俗吗?你高雅,找个高雅人去过。”
“大过年的,你们吵什么吵?这是在我家,不是在你们家,梅儿,把大姐拉到房里去看电视,毅哥,我陪你到河边去走走。”
刘芙气得发抖,她蹲在地上流着眼泪,余盼归从邬梅怀里溜了下去,跑到刘芙面前,拽着刘芙的衣服说:“妈妈乖,不哭。”
刘芙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乖宝贝,抹了抹眼泪,把他抱了起来向厨房走去。
刘子墨陪着余毅来到长渠边,长渠经过几场雨水的冲刷,臭味已经逐渐消散了,加上麻田板结,不可持续种植,已经没有什么人种麻了,周围的环境逐渐好转,偶尔可以看见一两只乌鸦在空中盘旋。
刘子墨与余毅敞开心扉,推心置腹地聊起天来。
刘子墨说:“毅哥,你也看到了,胜利哥一个人养活了一家人,还能做新房,购置摩托车,这样的经济实力,一不是靠祖上留下来的家产;二不是靠做生意做买卖赚的轻松钱;他是靠自己一双勤劳的双手产生的价值。大姐之所以生气,是看出了差距,你如果一直呆在邮递员这个岗位上,前途是黯淡无光的。”
“我也看出来了,芙儿她心理落差有点大,并不是我想说她什么,实在是,我作为一个教师子女,并不觉得赚钱少就很丢脸,你也说过,安贫乐道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我不羡慕有钱人,我只佩服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精英,而不是那些沾满铜臭的可怜人。”
“金钱至上的观点不可取,我也不喜欢那些有钱人,但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进步,都在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我们还能故步自封,原地踏步踏吗?”
“我何尝不想出去外面闯一闯,可是我没有一技之长,到外面能做什么呢?”
“你有知识,有文化,精通音律,会书法,堂堂大学生,还比不上那些庄稼汉,泥腿子吗?梅儿的爸妈和叔叔伯伯都是打渔的,他们在广州收入可不低,就连梅儿,她刚到广州也是什么都不会,现在一个月也能做两三千块钱,比你一年挣得都多,她的爸妈帮忙打杂,一个月也有七八百块钱的工资,叔叔伯伯从事的工作更简单,帮别人拉货,一个月下来,也不低于四千块钱,你和他们相比怎么样?”
“我听别人说,广州黑白颠倒,日夜不分,人们愁眉苦脸,不知道什么叫快乐,在这种地方生活,简直就是在贩卖青春,就像一个个行尸走肉。”
“的确,在广州生活的人都是些没有情感的机器,但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你赚钱是为了你自己的孩子,为了高品质的生活,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羡慕别人,这不是攀比,是让你的孩子在同龄人中,能够抬得起头来,能够充满自信。”
“我爸妈是教师,社会地位高,我的儿子以爷爷奶奶为荣,他很有自信啦!”
“爷爷奶奶是爷爷奶奶,与爸爸妈妈不是一回事,你是希望活在你爸妈的阴影之下,还是希望活出自我,让盼归长大后,只介绍自己的爷爷奶奶,而把你们直接忽略吗?大姐在服装设计方面很有天赋,手艺也不错,你为什么不让大姐出去发展呢?”
“我身边的那些同事,都比我家的条件差,还没有哪一家是三职工,在岳阳生活,我们毫无压力,生活安稳惬意,夫妻也很恩爱,为什么一到仙桃来,却什么都变了?我们结婚这几年,从来都没有吵过嘴,红过脸,芙儿善良脾气好,也懂得包容,可今天,她怎么变得这样俗气了?”
“这不叫俗气,这叫现实,她看到了现实的表象,也看到了生活的实质,物资基础不牢固,精神世界也会崩塌。”
“财是下山猛虎,果然不差,真想不到,我们相濡以沫的爱情,在金钱面前,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看来,我们要两地分居了。”
“也不至于两地分居吧!你们可以选择创业,先到常德小打小闹,等攒点钱了,再到广州去淘金。”
“常德搞个档口需要多少钱?”
“差点的边摊3000块,中摊3500块,头摊4500~5000块。”
“我们总共只有不到1500块钱,搞档口的钱远远不够。”
“要不这样,我给你们投资,买一个档口交给你们,你们赚到钱了就分点我,赚不到钱就算了,白给你们摆,你看行不行?”
“你想投资入股?行啦!只要你不怕钱打水漂。”
“我对大姐有信心,关键是,你要把盼归交给你爸妈带。”
“那恐怕不行,妈妈还有几年才退休,我不能把她的事业给毁了。”
“在外面做生意,带个孩子怎么做?看档口需要一个人,进布裁货发加工都要人手,生意好的时候,三个人都忙不过来,何况你们只有两个人。”
“那就没办法了,这边的妈能帮忙带吗?”
“这边肯定不行,你的要带,丽姐的也要带,万一我们也有了,那不是乱套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
“只有让你当全职奶爸,大姐出去打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