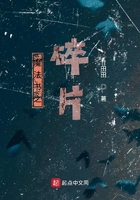司马衷身上源源不断地散发着热量,透过那层层叠叠的,单薄的春衫,不住地朝着孙窈娘袭来。
合着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苦香,一时,竟让孙窈娘忘记自己身处何地了。
她只是目带迷茫地朝着司马衷靠了过去,让她的身子,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二人的距离,只剩下至多不过半寸了。
远远望去,这两人就像是一对亲密无间的爱侣般紧紧地贴在一处。
甚是……叫人觉得刺眼。
换了旁人或许觉得无感,但有一个人却本能地觉得不对劲。
她将目光不住地放在依偎着的二人身上打量着,越来,那眉头皱的越高。父皇莫非是脑子出了问题不成,怎会离这女人这么近?
她这姿态,妖妖娆娆的,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比之谢氏娘娘更加让人觉得厌恶。
父皇曾上过那么大的一个当,莫非,他还觉得不够?否则,父皇看她时为什么没有异样,甚至,似乎对她这副模样瞧得甚为顺眼似的。
莫非,父皇也被这妖女蛊惑了不成?
她,到底使了什么妖术?
“父皇,你,你……”宣华刚要开口,却被司马衷打断了。
在她的疑惑中,司马衷淡淡地开口了。他嘴巴张张合合的,说出来的那番话,不论是宣华公主,还是这偏殿中的其他人,都被他这话惊呆了。
唯独孙窈娘面上闪过一丝窃喜。
“窈娘,你既如此担忧你表妹,又这么害怕她孤单,不如,日后你长长久久地留在宫中如何?”
顿时,孙窈娘心中一阵疾跳。她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傻傻愣愣地将司马衷望着,足足地望了好一会儿,才有些不敢置信的开口了:“陛下此言……当,当真吗?”
她不知道自己是哪里触动了司马衷。但她知道,皇帝金口玉言,既是他开了口要自己入宫,那这事,就成了定局……
日后,待她做了这后宫中的妃子娘娘,这些贱人奴婢们
她有些迫不及待的:“陛下,您要让小女入宫,不知……您会给小女一个什么样的位份呢?”
若只是个美人才人的,那可不行。她可是堂堂江东孙氏的嫡女,又有舅父在身后为自己撑腰,若那个位置太低,却是不行!
竟然明晃晃地朝着自己讨起封赏来了。
司马衷眼中闪过一丝冷芒,但声音,更加柔和了。
他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身子站得离孙窈娘远了一些,这才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她身上,那股香粉的味道实在是叫他觉得难受,若不是为了某些原因,他是定不会叫孙窈娘靠近半分的。
“窈娘想要什么位份,朕都给你。如何?”
说吧,说出来。这样,大家都会知道你的野心,也会知道孙氏一族的野心了。
他几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果真如此?”
瞧,这上苍,果真是待自己甚厚的。原本,在她的想象中,即便自己的身份与旁的姑子不同,但这大晋后宫,却也是等级森严的。如自己这样的,一旦入宫,最好的,也是要从淑仪。淑媛一类的开始熬起,然后在一次次的倾轧算计中双手沾满敌人的鲜血,踩着旁人的人头才能一步步地登上那个高位。
可他竟说,让自己选?
一时,孙窈娘竟觉得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小心翼翼地望着司马衷,缓缓地伸出了一根手指。
那手指,既白皙又纤细,叫人一望,便要忍不住想要把这只手握在掌心里肆意地把玩。
她不偏不倚地,将自己那根纤纤玉指按到了司马衷坚硬的胸膛上,几乎是吐气如兰的说道:“陛下觉得,这皇后之位……”
宣华公主急的满头都是汗。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了司马衷面前,有些急躁地拉住了司马衷的袖子:“父皇,您,您是不是忘了皇后了?”
“皇后?”司马衷有些不解,“这与皇后有什么相干?她不是正躺着么?宣华,你若担心她,不如回你房间去守着她好了。”
那语气,就像是在说一个不相干的人似的。
甚至,就连他的手,也放到了宣华公主的手上,坚定不移地捏住了袖子,从宣华公主的手上一寸一寸地将自己的袖子扯了出来。
“宣华,你回去把皇后守着便是了。朕还有要事……”他说着,将自己的手从宣华公主的手背上挪开了,而是转向了孙窈娘,将她一双玉白的手牢牢地抓住了,放在掌心里认认真真地把玩着。
那目光,更是浓情蜜意地,几乎能从中滴得出蜜水来。
孙窈娘大为得意地瞥了宣华公主一眼。
这一眼,既是炫耀,也是警告。炫耀自己超然于众人的地位,警告宣华公主不可在轻举妄动,没有眼色地说出更多她不喜欢听的话来。
宣华公主被那样满怀深意的目光一盯,顿觉遍体身寒。但她是公主,自不会惧怕这小小的孤女,反而更加挺起了胸膛,毫不相让地对着司马衷道:
“父皇,皇后殿下……我的母后,她不过进宫数月,连弘训宫都还没来得及住暖,甚至,如今她还在缠绵病榻……她还没有醒来,您这就要纳新欢,完全不顾她的想法了吗?您这样做,是不是有些欠妥?”
不是欠妥,是大大的不妥。
但这话,只是在喉咙里千回百转地绕了数次,她才终于艰难地说的这样婉转。
这世上的男人,竟都是这副模样?一旦有了新欢,就忘记了自己的旧情?
可是,这,这不应该啊?就在上一刻,父皇还在悉心地照料着羊氏献容,将她看的像自己的眼珠子一样。一转眼,他却又对着这孙氏窈娘做出这样的姿态,浑然忘记了羊氏献容还在病榻上……
她想起自己的亲生母亲还在时的情形。
那时,父亲远不如如今这般成熟,后宫中也甚是干净——
能在后宫中横着走的,除了母后,便只有一个谢氏娘娘,即便是谢氏娘娘,不管她私底下是什么模样,但见了母后时,却总是恭恭敬敬的。
至于其他的,不过是为了平衡各方权利而选入宫中的棋子罢了。
父皇从来都视她们如无物。至多,不过是当真这禁宫中的摆设一般,就像一个花瓶,或是一个器皿。
如这样地紧张一个人,却是宣华公主从未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