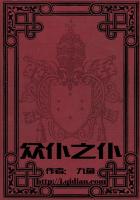袁宗达回锦衣卫衙门没多久,妓女红莺也到了,褚平充满期待的看着红莺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大声喊冤,被狱卒制止,袁宗达让红莺对质,不料红莺却扭头对褚平道:
“褚爷你昨晚干完好事子时就走了啊,你这死鬼都不肯多留一会,说是有要紧事要办,你这办了啥好事啊,怎么都到了锦衣卫大牢了啊!”红莺说完眼波流转对着袁宗达直抛媚眼。
袁宗达心里一阵厌恶,同样在莱仙院,这专门以色侍人的红客到底是红客,骚成这样,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干嘛的。
相比之下,自己心心念念的头牌青客雪三娘可真是出淤泥而不染,只舞乐清谈从不曾露出这淫靡之态。
“行了,好好说话!”袁宗达喝道。
“大人,这娘们撒谎,我清晨出门的时候,后门的龟奴可是看着的,大人问那龟奴便知小人受了天大的冤屈!”褚平扣头如捣蒜。
好吧,既然不死心,那便叫那龟奴来问问便知道了。袁宗达只觉得褚平在做锤垂死挣扎,便让左右去找那龟奴来。
“慢着,大人,那龟奴儿白日是不在莱仙院的,毕竟白天没啥人寻快活谁养他啊,他白日里串接卖水,大人要寻他得让人去北城的三王井候着。”红莺一脸媚色柔声道。
等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一个小旗带着莱仙院的龟奴回来了。
是个十来岁的少年,还挑着一副水桶,身形瘦削的像被风就能吹到一样,让人怀疑这水桶要是灌满这弱身板能不能扛得住,清淡的五官,眼神透亮,看上去怯懦又单纯。
“叫什么名字?”袁宗达陡然问道。
“大名不知,小名叫王四尾。”少年怯生生的回答。
估摸是个穷孤儿,不然长这么大连个正名都没有,袁宗达也没兴趣了解太多,他只关心到底是谁在说谎。
“昨夜可在莱仙院?见过牢里这人没有?”
“在,见过。”
“那人几时走的可曾知道?”
“知道,约莫子时从后门出去的”
褚平知道自己完蛋了,瘫在地上已经吓得说不出话。
袁宗达挥了挥手让手下将红莺和王四尾带了出去,继续盘问褚平的杀人动机和杀人过程,褚平一边尿裤子一边扣头只是喊冤,已经语无伦次了,一句有价值的话都讲不出来。
袁宗达只好作罢,却犯了难,按理说人证物证有了可以勉强结案,可褚平为什么要杀张式衡,那密室杀人的手法究竟是怎么营造的压根不知道,这强烈的激起了好奇心。
“大人不如查查褚平的为人和家里的情况。”一直不说话的越同舟冷不丁的扔出来这么一句倒是点醒了袁宗达。
一番调查下来,褚平的情况大致清晰,跟张式衡一样早年科举不中就托关系进了大理寺,一个做库头管出入库,一个做书办管案卷记录整理。
两人工作上平时没什么太多交集,私底下也没什么交往。
褚平妻子早死,家里只有老母亲和一个小儿子,其妻死后一直也没续弦,只是经常流连烟花之地。
那莱仙院因收费高昂,褚平只在每月薪水发放的当天晚上才能潇洒一次,而且固定都是点妓女红莺。
这些情况跟他交好的同僚都清楚,可除此之外褚平也没什么其他的嗜好或者异常。
袁宗达陷入沉思,张式衡家里并没有财物丢失,很明显不是图财,褚平跟张式衡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显然也非报仇。
难道褚平真是被冤枉的?可物证人证确凿,说冤枉也没道理啊,一个妓女一个龟奴能跟一个大理寺的库头有什么过节,还那么巧串通冤枉。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放班之后,袁宗达换了衣服悄悄溜到了莱仙院,他要问问自己的心头好雪三娘,看能不能得到些线索。
莱仙院号称京师三大青楼之首,背后老板从不现身,据说是太祖时候从龙起事后来退的一个老将的后人开的。
那老将退隐时得了免死铁券和世袭罔替的爵位,家族低调营生,深得朝廷敬重,年年赏赐不断,财力丰厚。
也因此莱仙院的场面最大,规矩最多,无数达官贵人争相前去采花猎艳,却从无一人敢做那些酒后撒泼强占名花的事。
坊间皆传莱仙院有三绝,红绝,青绝,食绝,意思是红客绝色,青客绝艺,宴食绝美。
莱仙院最大的特色便是将妓女分为青红客,红客是签了卖身契的,无论妙龄少女还是半老徐娘皆可入幕,只要身材脸蛋姣好。
青客则多本是良家幼女,打小便签用工的契约,每月付予养身钱,差师傅调教诗书画艺,每三年一考,不合格的即便想留也要解约,若是有天赋的上品就是想走也须赔大笔银子方可。
红客专门供那些的登徒子,开价高昂,但给妓女的分成缠头也多,青客则专事那些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开价极高,但基本都收归院里,除非有嫖客自愿给小费,那些女子也只能靠院里养活。
若是有青客耐不住寂寞坏了规矩要么卖身转做红客,要么由相好的嫖客出资赔上大笔银钱讨回去做妾室,若是拖到年纪大了便直接扫地出门。
因此那些青客都很乐于接近各色人物,以期将来有个好出路。
唯有雪三娘是个例外,既不主动讨好客人索要缠头,也从不巴结客人盼着出楼阁登厅室。
真名姓无人知,因着天生肤如凝脂赛过冬雪,又顾盼生姿窈窕婀娜,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得了个“雪娘”的混号,原本莱仙院列为第一,那清冷的性子得罪了老鸨,硬生生的排到了第三,从此便被人称“雪三娘”。
可这丝毫挡不住来访者的热情,常常是外地的到了京城一进莱仙院便吵嚷着要见雪三娘。
今天又是门庭若市。
袁宗达偷偷给老鸨塞了些银钱,老鸨心领神会地带着袁宗达去了二楼的雅间,临走前老鸨开心的许诺,等雪三娘房里的客人出来,便带袁宗达先上阁楼。
袁宗达喝茶打发时间,却听到楼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袁宗达出了雅间翘首一看,只看到楼体的拐角一个红衣身影闪过,再往楼下看时,那人又极快的跑出了门。
袁宗达总觉得那身影有些熟悉,正思量时,老鸨已经笑成一朵喇叭花似的来请人了。
“公子听曲还是清谈?”雪三娘柔声道。
袁宗达知道她的套路,极善揣摩人心,看出他是想聊点事了,不等雪三娘开腔找话题便主动开始问询起红莺和拿龟奴儿的情况。
雪三娘也没说出什么所以然,只道和红莺交好,大概都是些平常身世之类的,袁宗达听得索然无味,只好作罢。
“公子今日怎么聊起这些了,莫非对我红莺妹妹有兴趣,贱妾倒是可以帮公子探探美人心底。”雪三娘吟着笑意调侃。
袁宗达连连摆手,爷的心在你这还不知道么,什么时候见我招惹那些红客了,袁宗达有些不悦,父亲大人去辽东办差也快到回来的日子了,袁宗达不敢逗留太久,找了个托辞便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莱仙院。
袁宗达走后,雪三娘便以头风发作为由跟老鸨告假不见客,寻到红莺那里,刚好红莺在化妆准备,便闲聊起来。
“姐姐放心,今日我和四尾那小子可是说的滴水不漏的,保管那登徒子吃刀子,只是我有一事不明,姐姐和那登徒子到底有什么仇怨,要如此作为?”红莺一边抿着口红一边问道。
“人死过烂,旧事不提了,我只告诉你那恶棍死的不冤。”雪三娘淡然回道。
“好了,姐姐不肯说我也不会问,那登徒子每次都粗野的要命,老娘也见他不顺眼,早想修理他了,正好应景。你开心就好!”红莺转过头拉着雪三娘的手笑嘻嘻道。
雪三娘看着她灿然一笑:“你果真是个知心的人儿,不枉我待你好,可记住以后不管谁问起只消原来那般讲便是,对我对你都好。”
“姐姐放心,当初我被人百般践踏若不是你出手相助,我早寻死去了,这条命是你给的,就算是有人拿刀驾到我脖子上我红莺也还是那般说法。”
红莺心急着表白,作势还要发誓样。
雪三娘点了点头,撩起红莺散落的鬓角绾到她耳后嘱咐她小心些便回房歇了去。
袁宗达回到家里,听到花园里妹妹令安郡主放肆舞剑的声音,心知妹妹心情不好便低着头快步往里走,不想郡主已经瞧见了他。
“袁宗达,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哪里了,爹爹马上就要回来了,你最好小心些,那个妓女有什么好的,什么青客还不是个骚蹄子,你醒醒吧你……”
袁宗达装作没听见只是加快脚步任由这个不好惹的妹妹放肆奚落。
郡主见哥哥没点反应心情更加不美好了,手上的剑法开始没章法,劈的嫩绿的枝条窸窸窣窣的直往下落,一地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