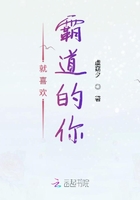“嗯!你说的也有道理。”
王郞点了点头,“贤弟能这样说,足见宅心仁厚,若能改变祖上的训诫接受朝庭的封赏,我敢保证绝不会失于一郡太守之职。唉!我真是不明白,令祖上曾被高祖倚为国之柱石,却为何不愿让后代为官了呢?”
“关于这一点,我还真没问过。”
宗勖想起了张梁,顿时灵机一动募地想到自己之所以会穿越到这个时代,会不会又是这位老祖先在背后使了什么手段。毕竟在催桃花的幻空里,张梁是有前科的。
王郞想了想,道:“这件事情恐怕令祖父及令尊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吧?”
“嗯!”宗勖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道:“没关系,有机会我会亲自向高祖朝的那位老祖先请教,相信他一定知道答案。”
“呵呵……”王郞淡淡一笑,“贤弟说笑了,令祖故去近两百年了,贤弟又如何能见得着?民间传言终究只是个子虚乌有的传说罢了,根本不足为凭!”
宗勖知道,此刻就算张梁自己跳出来告诉他说自己就是张梁,王朗也只当他神经有问题,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当下淡淡地笑了笑。
“世事难料,这种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
汤衍点了点头,“不做官也挺好,不用为王事操劳,省心。你看看家父,郡守不算大吧,事儿可不少,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稍有差池就会受到上官的责难。若不是朝里还有王伯父这棵大树,唉呀!干不干也就那么回事儿罢了。”
“呵呵!”王郞仍旧笑着说道:“贤弟说得似乎也有些道理,我有时也蒙生山林之想,但是家父不准,我也只能勉为其难了。呵呵!让两位贤弟见笑了。”
汤衍说道:“王兄说笑了。以王兄之高义大才,这区区一个长安郡守只能说是牛刀小试罢了,依我说王兄迟早都是相国之材,甚至列土封疆不在话下。”
宗勖很听不惯这种拍马屁的话,况且历史早就已经摆在那儿了,王邙之兄王朗在长安和珞阳等多地都做过官,官阶最高也就是个郡守罢了。等到二弟王邙在朝得势之后,王朗早已去世十几年了。
“以我看王二哥的才干比起伯父来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将来的成就必定空前。只不过,呃……这个……”
程宗勖说到这里时“吱吱唔唔”不肯往下说了,因为他觉着自己现在就跟“借尸还魂”差不多少,而且他自信老祖先张远的本事肯定比不上自己,一旦言语上得罪了王家,势必会为张氏家族带来恶运。
“哦?”王朗倒是微微一怔,顿时想起了父亲跟他提到的那个传说。在他的二弟王邙出生的前一天,他们的父亲王世源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王家的一位祖先对他说王家即将降生一个子孙,乃是济世之良臣,乱世之枭雄。
这个意思就是说,王家将要出生的这个子孙未来将是一位拥有大才干的人,吏治清明时节会成为一位国家栋梁之才,而如果遇到混乱的年代就会成一代枭雄,其结果必定会为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次日,王世源的夫人临盆,后天便生下了次子王邙。合家自然欢喜,但是王世源事后几年始终对王邙心存芥蒂,不大喜欢。有一次他带着两个儿子外出打猎,还曾经趁着风势放火准备烧死王邙好一了百了。
结果是天不灭邙。当时的王邙虽然只有十岁,却能够杀死战马并且剖开马腹,将自己藏身在马腹之中躲过了一劫。事后,王邙的祖父和祖母为了这件事对儿子王世源大加申斥了一番,说他不佩做王家的子孙。
几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王世源把当年那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长子王朗。王朗当时同样深以为然,他早就发现二弟虽然才华横溢,但许多行为举止都与众不同,因此他也深深地相信王邙会成为王家的祸根。
因此,当王朗听程宗勖提到二弟的前程时,却表现出这样一副吱吱唔唔犹豫不决的样子,心里自然有所触动。尤其民间一直有传闻,说刘侯当年为自己的后人遗传下了一些秘藉,好让后世子孙能够洞察时变,保张氏家族永远昌盛。
“家父和我都对二弟的将来极为关心,宜衡既然有话不妨直言。家父和在下他日定不忘宜衡保全王氏之大恩。”
王朗说话的同时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程宗勖面前,躬身行礼,袍袖都拖到了地上。
程宗勖和汤衍见他如此,吓得慌忙起身还礼。汤衍不明所以,还以为王朗突然发了神经病,无缘无故地对着张远这个破落户家的子弟这么恭敬干嘛?
“好吧!”宗勖无奈地点了点头。他从王朗的话语当中听得出来,王氏父子似乎对王邙将来的事情全都有所预见。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看得出来王朗是出于一片致诚,当下不再犹豫道出了心中的想法。
“依小弟之愚见,王二哥将来必定会前程似锦。如遇圣明之主,必定会成为像海昏侯一般的辅国重臣;若遇到昏聩之君,势必会成一代枭雄。其结果嘛!恕我直言,似在两可之间。”
他故意把对王家不利的话改成了两可之间,自然是不愿意得罪未来将会权顷一时的薪朝皇帝王邙,同时还要为张家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因为,经此一事,张远势必会被王氏父子所倚重。
“啊!”王朗大吃一惊,没想到坊间传闻确有其事,当下对着程宗勖再行大礼,恭恭敬敬地请教道:“贤弟高义,今以实言相告,请上再受愚兄一拜。”
果然不出宗勖所料,张远施展才能的机会来了。他从张远的记忆中也找到了与自己相同的看法,深深地为这位祖先的才智所折服。只是张远似乎始终畏首畏尾,来到长安多日了,始终不敢讲出来罢了。
程宗勖更佩服的还是张梁,利用阵法超越时空,通达古今,“看起来他老人家对后辈还是蛮照顾的嘛!就是不知道留下了多少不传之秘,有机会的话,嘿嘿!非要好好地拜读拜读。”
“王兄太客气了。”
宗勖连忙伸手把王朗扶起来,淡淡地道:“对于这个两可之事,还须容小弟详加推演,善加利导必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哎呀!如此甚妙!如此甚妙!”
王朗当真没有想到被父亲勉强留下来的张远,只用了这区区数日,连二弟的面都没见到,就已经推演出了祖先的提示。“若是将此人留下,将来给二弟做个高级幕僚的话,我王家岂不是真得要飞黄腾达了!”
“请两位贤弟稍坐,愚兄这就去面见家父,实言相告,升贤弟为上宾。”王朗言罢与汤程二人行礼后转身出去了。
汤衍在旁边听了两人的话后糊里糊涂的,不明所以,待王朗走后忍不住向程宗勖问道:“张兄,你适才所言可是说二公子将来会飞黄腾达吗?”
他也听到过坊间传闻,只是不敢相信张远真有这份才能,此时倒是有点震惊了。
“嗯!”宗勖点了点头,淡淡地道:“这话只可当着大公子和王世伯的面请,在二公子面前切记要守口如平,以免在人家父子兄弟之间生出嫌隙来。”
“是是是!张兄所言极是,小弟记住了。”
汤衍急忙深施一礼,道:“将来你我兄弟同在王府做事,如果小弟有什么不当之处,还望张兄不吝提点一二,也不枉了咱们这一路上同舟共济的缘分。”
宗勖冲他点了点头,伸臂扶住他的胳膊,低声说道:“这个自然。汤兄无须多礼。”
汤衍大喜,有了张远这句话,何愁日后不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呢!
时间不大,外面有家丁来报:“老爷到!”
汤程二人急忙放下茶碗,双双站起身来,躬躬敬敬地垂手侍立一旁。
就见长安郡守王朗引着一位五十余岁的阔佬走进了前厅,阔佬衣饰不俗,可以说在这个年代算得上极为奢华。阔佬略显肥胖的身躯微微有些颤抖,进来厅中并不就坐,而上用眼睛重新打量起张远来。
“朗儿!快,快请张先生上座。”王世源同时冲儿子吩咐道。
王朗听到父亲的吩咐,赶紧过来请程宗勖上座。宗勖自然要谦让一番,最后没法只得在正对着门口长桌左侧坐下。王朗这才过去扶着父在宗勖的右边坐下,自己则垂手侍立一旁,不敢就座。
他不敢坐,汤衍自然更不敢坐了,立在宗勖旁边留神听着王世源说什么。
王世源喘息了几口气,方才开口说话,“先生高义大才,今日既然已经识了破犬子的玄机,不知道先生可有破解之术否?”
“当然。”宗勖点了点头,故作神秘地说道:“《道德》有云: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其意是说,为人处世,于心若能做到曲、枉、洼、敝、少,则于事必得全、直、盈、新、多之果,二公子正是合了此道。”
“然面,其后则有‘多则惑’之说。欲破此迷局者,务须使明人常伴其侧,时时加以善导则必能无往而不利也。未知二公子身边可有能当此大任之者?若无此等样人,则小侄愿毛遂自荐。”
“好好好!先生正该如此。”
王世源听了这一篇忽悠的高论,反倒觉得像抓住了无价之宝似的,冲儿子王郞一摆手。
“朗儿!快,快替为父及王家列祖列宗拜谢先生的大恩大德。”
“是!”王朗答应一声,行到程宗勖面前,整冠掸尘、明目正心,双膝跪倒拜了三拜。
“不敢,不敢!王兄真是折煞小弟了。”
程宗勖吓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抢着跪倒还礼,伸出双手相搀把大公子王朗扶了起来。
程宗勖请王朗在一旁就座,王朗谢后并没有坐下。宗勖不再理他,来到王世源跟前,跪倒行礼,口中称道:“老大人大义为上,小侄今受了王世兄大礼,日后定当尽心竭力辅佐二世兄成就大功,纵然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哈哈哈……”
王世源站起身来伸双手扶起程宗勖,满面春风地道:“贤侄太客气啦!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朗儿说,千万别客气。”
“多谢伯父抬爱。”宗勖再次躬身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