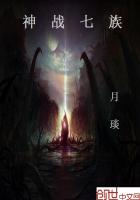然而,曾经激动过前辈文化精英们的那个奋发有为的时代氛围已经形迹难寻。林含烟与后来认识的真正意义上的初恋男友凌伟在一次郊游中看到一片茶树丛,不由得联想到自己读过的小说《茶花女》:“玛格丽特一生中唯一真正幸福快乐的时光,就是和阿尔芒在乡下时的那段日子。她还能记得在后来的译制片中,玛格丽特头戴自己用野花编织的美丽花环,在一片灿烂得让人眩晕的油菜花地里欢呼雀跃的画面……然而,这样的日子对她而言却是如此之短。”这也是林含烟个人内心感受的真实写照。对大自然的感受力和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力使她深深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距,“感受到了当下环境中所缺失的一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和悠久进化的人类所共有的那类情感:唯美、含蓄和忧思”。对不可见的世界的丰富而细腻的感知,使她对可见的、并不得不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俗的世界常常感到无法言喻的沮丧。这种对人生“目标的迷茫”,也引起了凌伟的共鸣:这是“希冀的无着和奋斗的茫然……遭逢这种状态的又何止是自己和林含烟?”其实这也是深受启蒙价值理性影响的那一类文化人典型的心理状态:这类人在已经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上,总摆脱不了“想担当什么”、却又没有什么可以担当的苦恼。而男女之爱,恰恰是有限的生命个体将自身交付出去、以获取存在感觉的无限延伸的最为直接的经验形式,就如林含烟望着自己就读的大学校园外那“灼灼一片的映山红”,“总会有一种怡然和欣悦的感觉,潜意识中,她把它们视作了生命中的一抹亮色”,让她能“觉察到生命中还有许多值得自己去努力和希冀的东西”那样。因此,作为知识女性,对两性之间的真爱追索,便构成了她们在人生中重要的情感寄托。
从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林含烟在一家晚报做文艺版编辑工作,开始在平凡的生存环境中讨生活。她在读大一时结识的男友郑哲峰在当地商业局已工作多年,就读的是电大的机械专业,对文科没有兴趣。郑哲峰的人生目标具体而实际,话题离不开单位的工作,对职务的升迁有着“永无止境的欲望”。这个男人有什么错吗?似乎没有。“一个人按时上班,好好工作,天天向上,按照机器允许我们做的事情去做事情,说各种政治正确的话,尽管无聊,但想到可以预见的提升以及大家都想的时髦休假方式就兴致勃勃。”这个世界并不想培植比“按部就班的欲望和工作”更多的念想。因此,郑哲峰是驯良的、识时务的。这也是具有不同的精神旨趣的林含烟与他相处时不能不感到乏味的根本原因。但由于性格中固有的软弱和思想中还保有着传统的一面,“她还做不到率性而为,所以才让自己这么左右为难”。两人的关系也就这么不冷不热地拖着。直到郑哲峰强行与林含烟发生关系后,她受制于传统的贞洁观念,才忍痛断绝了与凌伟的恋人关系,违背自己的真实心意与郑哲峰结了婚。这是她由于年轻而犯下的一个幼稚的错误。
由于价值观的不同,林含烟与郑哲峰的婚后生活乏善可陈。女儿出生后,他们的关系也进一步冷却下来。多年的同床异梦又经历了多年的分居后,如愿升为单位办公室主任并进入局党组的郑哲峰终于同意离婚。林含烟也重获自由,可以去追寻她那么在意和关注的、有“质量和趣味”的生活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与十来年前出差时有幸结识的大学中文系老师裴云逸再次相逢。经过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又一次为对方的精神气质所吸引,感到了心与心的默契。林含烟为真爱以身相许,还强烈地想为这个男人体验一次怀孕的过程——并非为了有什么结果,只是试图通过承担的负累向自己确证生活的真切和实在。就在林含烟想嫁给裴云逸时,却不料命运从中作梗:还未离成婚的裴云逸先是遭遇车祸,后又被诊断出肺癌晚期,很快就去世了。
林含烟的朋友、年龄稍小的章瑾如是周琼作品中的另一位知识女性。父母在她尚不能自立时就因患癌症而先后离世。从医学院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市级医院妇产科工作。对家庭温暖的渴望使她对婚姻有着太多的期待,很快她就与一个显得“很体贴”的男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与林含烟一样,章瑾如也看重生活的质量,这质量更多的是与精神、情感和自由等要素相关,而不是着眼于物质和金钱;她更看重的是自我独立、自尊和尊重别人。不料婚后一年多她发现丈夫竟瞒着自己与别的女人有染,心里容不下一点杂质的她于是毅然选择了离婚。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对婚姻都没有了信心,直到她认识了美术学院的老师赵剑青。赵的精神深度和唯美的感受力使章瑾如久已漠然的心又重新复苏。她再次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婚后不久,章瑾如竟发现自己患上了乳腺癌,且到中晚期已转移,另外早些时候因尿毒症而移植的肾也出现了排异反应。由于不想拖累赵剑青,同时也为了能有尊严地离去,她隐瞒了真相,再次主动放弃婚姻,并不告诉任何人,独自赴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地区,在天地的环抱中以洒脱的方式告别了人世。
好友章瑾如之死,对林含烟是一个打击。爱人裴云逸之死,对林含烟又是更沉重的一击。美国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朱迪丝·维尔斯特说:“我们是分离的人。我们受到禁忌和不可能办到的事的束缚,形成了极不完美的相互联系。我们通过丧失、离开和放弃(而)生存。带着或多或少的痛苦,我们迟早会认识到丧失的确是‘一种终生的人类状况’。”然而,尚未认识到这一点的林含烟选择了自杀,被赵剑青及时发现抢救过来。身体恢复后的林含烟开始重新思索自己的处境和生命的意义:已经很久了,她对自己的生命从未与它事物发生过真实的关联一直感到遗憾和迷惘。当她历经周折,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时,才真切地体验到生命有所附丽的感觉,偏偏挚爱的人又突然弃她而去,这是何等的残酷!摆在她面前的其实是如何对待身边最亲爱的人突然离去的问题:是追随他们而死,还是带着残疾生活?或者是从痛苦和记忆中学会适应?“在这之前,她一直认为有一类东西是恒久的,那就是情感、爱、友情和梦想……而今,她借以寄托的东西又在哪里?”为了躲避活着的虚无感,她渴望把自己从绝望和痛苦中超度出来:“后面的路将如何独自走下去?仅仅为活着而活着?对生活还能有所需求吗?倘若有,那又是什么?或者,自己还能为这个社会付出些什么?”这是一种想超出渺小无助的自身、通过融入什么来延伸自我生命的渴望,从而去体验生命中有所担当的感觉,就如她曾渴望为裴云逸怀一次孕那样。
经过一段内心的梳理,她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填写了一份遗体捐赠志愿书,而后以志愿者的身份独自奔赴阿里地区,那正是好友章瑾如为自己选择的最后归宿地。她在当地的一所小学里开始了教书生涯,准备度过余生。在远离都市文明的这块高原厚土上,生活是孤独、清苦的,但林含烟“一直是孤独的,孤独已与她一生为伍,即使是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都市时,这种孤独感从来都是在她的心里挥之不去。她曾经那么渴望一个有爱的婚姻,当然,现在的她,已完全清楚这辈子不再有可能完成这个奢望了。但在这里,她却找到了一个有爱并且也需要她的环境,因而她不再孤独了。”数年过去,林含烟已融入了当地淳朴的生活和奇异壮美的自然景色之中,心灵平静而充实。现在的她肤色黝黑、着装简单,“凸显了一种干练和利落。她的脸上和眼神中,除了依然的娴静,更多了一份内敛的宽厚”。她因终于找到了能与既广漠又浩繁的宇宙相贯通的浑然一体的神圣感觉而对命运充满了感恩之情。这是一种物我两忘、从小我的感受升华到大我境界的超凡体验。
周琼笔下,林含烟和章瑾如两位女性都被描写成与世俗的幸福无缘的人。她们不是在找到真正的爱情时自己不幸因患绝症而死去,就是在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爱人时自己所挚爱的人突然因患绝症而死去。人生无常的悲剧令人欷歔。小说的格调中也因此流露出一种悲凉和无奈感。林和章对真爱的寻觅和对真爱的执著的最终结果,似乎都在印证作者在小说开首的题记中所言:“人生本就是一个不断放手的过程。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们珍惜曾经拥有和已经拥有的一切吧。”
朱迪丝·维尔斯特在其《必要的丧失》一书中这样总结丧失和收获之间的关系:“为了成长,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放弃。因为只有对丧失变得更脆弱,我们才能深深地爱某种东西。只有丧失、离开和放弃,我们才能成为分离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联系着的人、内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