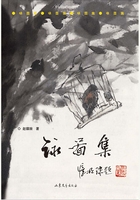他又看见她咳嗽。她咳得也不厉害,可是一咳就是一大泡痰。每回都是这样,她喊过了叫过了,过了一会儿,你以为她累了,要睡着了,她却好好地咳起来,咳着咳着就往床沿一趴,往地上吐痰。他便赶紧摸火柴点灯。他看见她的痰是白色的,黏嗒嗒的,冒着许多小泡。他想她哪来的这么多痰呢?他再去问草药郎中,草药郎中咂一咂瘪嘴,拈一拈黄须,略一琢磨,问苗幸福,她眼睛还清爽不?苗幸福说,这我说不准,有时候还清爽,有时候又好像有点那样,这些日子都是这样的。草药郎中便说,她怕是个被痰迷了心窍的人,不是被一口痰迷住的,是左一口痰右一口痰,被慢慢迷住的;以后你就看她的眼睛,要是她的眼睛越来越清爽了呢,你就放心让她吐,她吐痰是好事。苗幸福将信将疑,还是说了些感谢的话,草药郎中摆摆手,说你不要谢早了,我说的也不一定,若是真说中了,也是瞎子打老婆撞到的,是你家祖坟在冒青烟呢。
正如草药郎中说的,苗幸福看见她的眼睛确实是越来越清爽了。
苗幸福说,假如她的眼睛像一盆清水,一眼见底,他不会认为那是“越来越清爽”,因为那是傻子的眼睛。即使是七八岁的孩子,你都看不到底的。而她的眼睛呢,就拿一面镜子打比方吧,原先是灰太厚了,镜底又生了锈,根本不知道它是镜子,现在灰和锈都被揩掉了,猛一看吓你一跳,原来它把你照在里面。你的眼睛看过去,她的眼睛一闪,就把你的眼睛挡住了,顺着你的眼睛看过来了,你会觉得你被她的眼睛拿住了,弄得你头都抬不起来。以前她哪是这样的呢?以前她要么不看你,要看你也是忽一下就过去的。
到了约二百五十多回以后,他担心的只是她的瘦了。她瘦得真让他感到害怕了。他要带她到公社卫生院去,她不肯去。她说:“干什么?”苗幸福说:“你这样瘦下去不对头,还是到卫生院去,请人家把把脉。”他看见她一下一下地摇头,头发都甩起来了。他不知道她要干什么,看着她,不敢吭声。过了一会儿,他讷讷地说:“你瘦得这么厉害,不去看一下怎么行呢?还有头疼,也是要看看的。”他看见她的目光朝着房顶,又落下来,落到他脸上,一眨也不眨。苗幸福被她看得如坐针毡,好像五脏六腑都被她看穿了。看着看着,她忽然问他:“你叫苗幸福?我怎么会嫁给你,跟你结了婚?”苗幸福一下子愣住了。她不等苗幸福回答,又问他:“你说我冤不冤?”她用左手去捏右手,左手小,右手大,只能捏住一大半,但她似乎想全捏住,便变换角度去捏。她说:“你看我是不是人不人鬼不鬼?你说我活得还有没有一点意思?”苗幸福被她问得满脸愧色,他说:“这个这个,是这样的……都是事先说好了的,是不?不管怎么说,我呢也是有一门手艺的,吃穿还是顾得到的……”他还想找话说,可是她又问他:“我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他便不知道怎么说了。她把两条眉皱到一起去了,两只眼睛也靠到一起去了。她又用拳头打头,说:“我的头都裂开来了,我真是生不如死,我不服!”苗幸福被她说得惴惴不安,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夫妻都做了,还有什么服不服的?是吃的比不过人家,还是穿的比不过人家?我除了背上不齐展,手脚也不比人差……”她说:“我头疼!我不服,我宁愿去死!”
苗幸福吓了一跳。他心里没底了,只好去找水香,说李玖妍怕是想反悔呢,说她宁愿去死呢。水香问他,李玖妍是怎么说的呢?他学了一遍,水香说,你见过谁说死就死的?你管她怎么说,人都被你睡烂了,再悔她能悔到哪里去?你只管好好过你的日子,让她早点把肚子挺起来。苗幸福愣了愣,说是呀,这么久了,她是不是怀上了呢?水香说那会作呕的,她作呕了吗?苗幸福说好像没有,想想又说,只是老咳,一咳就是一大泡痰。水香便撮起嘴笑道,咳算什么?那就是还没怀上,幸福子你没用呢,还要再加把劲呢!
可是再到了晚上,苗幸福就是想加把劲也不行了,李玖妍手不动脚不动,只是将身子甩一甩,冷冷地说一句,你别动好不好?苗幸福就不敢动了。苗幸福自己也说不清这是怎么搞的,自己怎么又怕她了?她什么地方让人怕呢?他就侧眼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像什么,像什么呢,想了半天才想到一棵冬天里被冰裹住的树,看着就是一股寒气。说到这里,苗幸福咂巴一下嘴,对我说,我哪里知道她这是完全变清爽了,她是在想事呢?
那年的桃花水一下来,水甸前面的那条小河就变黄了,也变宽了,河水把岸坡浸没了一大半。芦苇也长起来了。到五月,芦苇开始簇堆了,六月就连成片了。这时候有个工作组来了,就是在这个工作组往人家房墙上刷标语的第三天,李玖妍不见了。
那天苗幸福在东家家里吃过晚饭,吹着口哨—他说他已经吹成习惯了—回家,在家里没看见李玖妍,那条叫黑子的狗也不见了。鸡鸭鹅都在。他想平常这时候她早从花生地里回家了呀。他在门口看见了那根绑着稻草的竹棍子,还看了那顶草帽。草帽挂在门框边。他说喂,喂了几声,听见了狗叫,就来到岸坡上,看见黑子沿着岸坡跑过来。月亮刚升上来不久,弯在头顶上,像挂着一把刚磨过的镰刀。坡脚边沙沙响着的是才长了两尺来高的芦苇,河水被月光照得亮亮的,波光是一副很诡谲的样子,一闪一闪的。苗幸福看看黑子,又看看河,心里凉了一下,他说黑子,人呢?黑子扭转脖子汪汪地叫了两声。苗幸福看见了一只马桶,马桶上的红漆在月色下泛着亮光,马桶过去一点是一只马桶刷子,马桶刷子过去就是一闪一闪地泛着亮光的河水了。苗幸福的头皮就麻了,他围着马桶转圈子,转了几圈又蹲下去。泥沙地上有一些字,好像是用指头画出来的,他还勉强认识几个字,他看见了“苗幸福”,又看见了“对不起,我走了”,就什么也不看了,一下子就哭起来,说我知道你觉得冤,嫁了我这个驼子,可你就是再冤你也不能走这条路呀……刚哭了这一句,又扯破喉咙叫救命,不得了啊!我老婆,她她她、她在河里呀,快来人,救救救、救命哪—!
水香头一个跑来了,然后水甸人杂杂沓沓地都来了。水甸人问苗幸福,你什么都没看见,不见衣服也不见鞋子,凭什么说你老婆在河里呢?苗幸福说在呀在呀,我知道在呀,不信你们看这些字,这是她写的字呀!水甸人说字呢?苗幸福便到处找字,他趴在地上,在地上爬着。是呀,字呢?他又哭起来。他哭着说,字都被你们踩掉啦!水甸人说,你看到她写的字啦?他说,我当然没看到了!水甸人说,那她写的字是怎么说的呢?苗幸福说,她说她走啦!水甸人说,操,走了?水香你拍胸脯给人家幸福子做媒,可你给人家幸福子弄来个什么老婆?说走就走的?水香说,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我只包得她是个女的,我还包得了别的?脚长在她身上,她要走我管得了?苗幸福跺着脚说,谁说她走了呀,她说走了就是走了呀?她是往那条路上走了呀!水香说幸福子你说一句公道话,我给你做的这个媒哪一点不好?是她不跟你睡呢,还是偷人养汉了?好的时候是你们,不好就怪到我头上?苗幸福说现在哪有工夫扯这些?她蹿了河呀!大家赶快救人吧!水甸人说,不对呀,我们看见她一天都坐在花生地边上呢,好好的她蹿河干什么呢?莫非你们吵了架?苗幸福说我们吵什么架?水甸人又问,那你打了她?苗幸福说我打她干什么?水甸人哦一声,说,那就不会,没打没骂,她怎么会走那条路?再说又没到下河洗澡的时候……苗幸福说我跟你们说不清哪,我心里知道呀,她想反悔呀,她觉得她嫁得冤哪,她闷头想这件事呀,她不想过啦,她说她活得没一点意思啊……你们看,这是她的马桶呀,她把马桶扔在这儿,还有马桶刷子,她不是蹿了河会是什么呀!
大家就看马桶和马桶刷子,看了一会儿,又看宽宽的银光闪闪的河面。他们说这怎么办呢?这么无边无际的,又是夜晚,怎么救呢,这哪里看得见人呢?水香跌着脚说,幸福子不是我说你,老婆给你说进了门,你怎么就守不住呢?苗幸福说怪我怪我,是我薄福贱命!大家赶快救人吧!救人吧救人吧!苗幸福边说边给大家作揖,我求大家帮忙啊,我给大家磕头,我明天买烟给大家抽。水甸人叹着气说,你这样说了,那有什么办法,找得到找不到,也总还是要找一找的,做人是这个样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