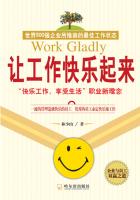山阴路上走两遍
山阴路是我这次在上海走过的最安静的一条路。
也许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个人睡着,所以不忍心打扰他的梦境,更不忍心吵醒他,就很少来这里。而来这里的,大多是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没有在山阴路上走过,又怀着某种侥幸心理,希望来了时,睡着的人正好醒来,彼此见上一面,看上一眼,留个影像在心中,就悄然离去。
想归想。我来时,睡着的人依然睡着。在他曾经召见朋友的地方,在他曾经和家人、朋友吃饭的地方,在他曾经写作、休憩的地方,在他曾经为留宿的朋友铺设床被的地方,在他曾经把最好的房间留给爱子的地方……我只能借助超常的想象力,想象当初他或沉思、或静默、或举眉、或欢笑、或投足、或弯腰、或疾笔的种种动作,想象他左手擎着纸烟,右手轻撩垂地的长衫上楼下楼的样子。
这是山阴路132弄9号,他——鲁迅——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三年半时光。1933年4月11日他搬到这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1936年10月19日去世。在这里,他撰写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并翻译了《俄罗斯的童话》、《死魂灵》等外国文学作品。现在摆设的物品,都是他当初用过的原件,保持了他生前的原貌。当然,我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我关心的,是他怎样在这里把最后的光阴一点一点数完。我想,他一定常在饭后走到寓所前的小院里,抬头看看天色,然后决定是不是该出去,在安静的山阴路上走走。天色不对,他就上到二楼的书房里看书、写作。天色还好,就出去走走,沿着山阴路的左边或者右边,朝左或朝右,嘴里叼着烟袋,随心所欲地往前走,随心所欲地一路寻思。遇见熟人了,举手打个招呼,然后错过,然后继续往前走。思绪被打招呼时打乱了,再来一个思绪,继续让心沉下来往前走。走着走着,心就亮开了,那脚下的路就不再是路了,而是一道光明,是一个方向——供光亮运行的方向。
其实,即便他不出门,即便他就站在读书写作的二楼,也能欣赏到绝妙的风景。因为那里的视野很好,可以看到天色,可以看到早在自己心中升腾起的种种物象。
离开他的寓所时,没有人送我们。他还在沉睡。一位工作人员把我们送到门口,很客气,但他的送行永远代替不了他的送行。可是,他只能以静默的方式把我们送到家门口,用不着客套,用不着寒暄,权当是一家人,可以自由地来,自由地去。
在隔壁的一间屋子,我买了一本英汉对照版的《阿Q正传》。除了曾经在课本上学过的,关于他的作品,我读得最透、最完整、最彻底的,就是《阿Q正传》。那是多年前一个我不大爱出门的夏天,蛰居在昆明环城东路那间不打开窗子也能听到外面的嘈杂声的屋子里,我静静地读了这本书。就是那一次阅读,我看到了文学真正的力量所在。现在再买这本书,我想,对他是一种缅怀,对我过往的日子也是一种缅怀。
迷惘的日子里,我们的内心总是需要不断注入某种力量和光芒。
出了他的寓所,我又回到山阴路上。
在进入他的寓所之前,走在山阴路上,一切都是陌生的,无论是山阴路对于我,还是我对于山阴路。走出寓所时,我感觉自己像是一直在山阴路上行走的人,只是我一直在把山阴路忘记,在把山阴路搁置在我的目光和记忆不常游走的地方。
也许是冥冥之中某种光亮的引领。
离开山阴路后,突然感觉又累又饿,找了好多地方,也没找到清真饭馆。折腾一番后,终于问到一家,哪想到,去到这家饭馆,必须经过山阴路。而这次走在山阴路上,我居然一点也不觉得累了。这么安静的地方,走在上面,怎么累得起来呢?只是,我走得比较小心。我担心脚步重了,会吵醒睡着的人。虽然,我渴望他能够醒来,在我彻底离去之前彼此见上一面。
而事实上,我们总是会有见面的时候,当我最终也沉沉睡去的时候。
2005年10月4日,上海
光影中的张爱玲
在准备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把陕北民间原生态歌手阿宝演唱的《赶牲灵》换成了大提琴曲《光影·殇》。这是一曲哀怨、忧伤,却又沉郁的流水一样静静地流着的音乐。我想,在写这些与张爱玲有关的文字时播放一下它,是再适合不过的。
在过去,我没有过看望某个名人的故居的习惯,这跟我内心里没有名人和平常人之分有关。但这次在上海,我却突然想去看望一下张爱玲。我想看看这位已经睡去的女子,她形影相吊的身影曾经穿行过的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这是2005年10月3日中午十二点左右,我和英穿过很多条街巷,绕过很多股拥挤的人流,问了很多的人,再搭乘一辆出租车,最后才来到常德路195号,即常德公寓(原名爱丁堡公寓)。在这里,张爱玲完成了《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封锁》、《心经》、《花凋》等。据说,在张爱玲去世之后,在我到来之前,经常有张迷来到这里,在公寓门口徘徊。
我不是张迷,读她的作品不多,只是在昆明做编辑时因工作需要读过一些评介她的文字。关于她作品的风格和创作内涵,更多的是来自英。英在大学时就读过她的很多小说,后来也经常在我面前说起她,同时说起她在小说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以及她对旧上海的人情世故“刻骨”的描写等等。所以,我想到来看望一下她——严格地说是她还遗留在时光中的另一种身影,另一种容颜,另一种姿态——完全是出于一颗平常心。此刻,她就像是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曾在某种冥想中相识,今天终于有机会了,我就顺路来看看。如果她在,我就和她小坐一会儿,品着她用灵巧的手泡好端到面前的小桌上的热茶,然后就听她说近来的心情,说近来的身体状况,说对家人、朋友的惦挂,说近来的写作情况,说她自己的忧思、孤寂、苦闷、哀怨、情仇,说某个她心仪已久的男子……
我们一点也不心急,就这么慢慢地叙说着。窗外飘着丝丝细雨,就像今天,把整个大上海渲染得朦朦胧胧的,偶尔扭头向外望去,一切像在梦里,又像在天际的某处。夜幕来了,她有些困意了,或是写作的灵感又涌了上来,而我,也该离去了,我们就浅浅地说一声再见。她送我出门,我执意让她先回去我再走,于是她扭动细小的腰身,终于转过去进了门。看着散发出胭脂香味的门轻轻合上了,我就下楼,回到车声轰鸣的常德路上,没入拥挤的人流中。
是的,我确实盼着她能在。可我的心愿总是落空。当我来时,她已经悄然睡去。
来到公寓门口,四周很冷清,很难见到有人从这里走过,即便是常德路上,经过的车辆也很少。进入公寓的楼口,一道铁栅门紧闭着。一位看上去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门前的一个近似轮椅的靠椅上,我和他说话,他一点也听不见,却显得有些激动地对我们说着什么。我想他说的一定是老上海话。看他苍老的样子,就知道是个经历了旧上海的风花雪月的人。这时,一位中年男子打开那道铁栅门走了出来,听了我们的问话后,他大声地说:“看什么看?那里面(张爱玲原来居住的房子)有人住着,谁会让你进去看?”我们一下子心凉了半截。好不容易找到这里,看到的却是一道面孔森严的铁门,当然,还有一块写有“爱丁堡公寓”字样的牌子。这实在出乎我的想象。我总以为那里会有一个“张爱玲故居”的牌子什么的。也许是我此刻的心情过于急切,且没有顾及到别人的心情。但我还是希望能看到这样一个场面:时不时地,有三三两两的人从这里进出,有的手里还捧着鲜花,或是别的要献给她的小礼物,哪怕只是一串小小的风铃。
怀着某种莫名的心情,我们往右拐出了常德路。我突然没有心思再去别的地方。在南京西路上,我们找了个空阔的地方坐了下来。英坐在一旁,拿出八宝粥吃了起来,我则看着不远处正为一座即将建起的高楼来回移动着的吊车发呆。我想,和这一切极其相像的东西肯定也正上演着,同时也在时光的水域中流逝着。
想必当初,张爱玲也这么坐在常德路上的某一处绿荫下,以近乎发呆的眼神看着很多东西上演,流逝,直到自己也成为这时光中的一道光影,沿着离自己最近的那一条隧道轻轻掠过。身后,那些曾困扰着她柔弱身心的所有情绪轻轻碎去,无声,也无息。有人拾捡起些许碎片,左也猜度,右也猜度,最后猜度到的,却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2005年10月3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