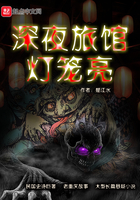咖啡厅里摆放着旧式雕花家俱,墙上挂的唐卡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佛菩萨的面像已经模糊,彩衣也有些掉色。然而,有悠扬的钢琴声,克莱德曼,流畅、优美、舒缓,只有他才能用音乐把四季表现得如此淋沥。小桌边,桔色的手工纸灯笼透出微黄的光线,时间穿梭在物与人之间,影影幢幢的,诱人的咖啡冒着热气,散发出一股焦唐的香味,虚空和心都被疼痛充盈着。
我和敬克英坐在靠窗的小桌旁,楼下就是如潮的转经人流,脚步声和寺庙的祈祷声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绕着这条千年的石板路旋转着,亘古不变。
她把封得严严实实的纸袋往我面前推了推,说这是她留给你的,我没看过!
我拿过袋子,正反两面什么都没写,寻问地看向她。
可能是钱。她泛着泪光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垂下,轻声说,她走时说要回老家,可能不来了,欠了你的钱,请我转交给你。
我抖擞着撕开袋子,取出两页纸,居然是青柚写给我的……遗书!
敬克英吃惊地看着我手上的纸,喃喃地说:她说是还你钱的,怎么不是?
我匆匆溜览了一遍,折好放进包里,看向对面沉默的敬克英,轻声说,她让我替她跟你道歉,说对不起你,她没办法爱上你,但你对她好,她很感激。
敬克英叹口气,没有说话。
我无力地说,你别难过,其实从这事上也看得出,青柚虽然不爱你,但信你更甚于其它姐妹,否则不会让你把信交给我。
但她还是骗了我,她知道我不可能贪她的卖身钱,所以就说是还你的钱。敬克英喃喃地说,整个人都被一股死气沉沉罩得紧紧的。
如果说只是写给我的信,她可能怕你不当回事儿忘掉了。我安慰她。正是因为你不同于其它人,不贪财,所以她才说是钱,这样你就不会忘了给我。
她低着头,抽了一下鼻子,眼泪终于流了下来,自己飞快抽了纸巾沾去,抬起头定定看着我,眼神沉静,说不管你信不信,我对她,是真的喜欢,只是她并不喜欢我!
我信。我说。你喜欢她,她却喜欢刘全,这就是命!
我知道她和我在一起是想利用我保护她,无论我对她多好,她心里想的还是那个臭男人!
我小心地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出生的那一刻老天爷就给我们决定了感情的取向。她喜欢男人,你喜欢女人。但她无力保护自己,只得借助你这个股东的身份。敬总,别怪她,她也是个苦命女子,万不得已不会走到这步。她对你……虽然谈不上爱,但肯定信任你,把你当亲人了。
她长出了一口气说,她完全可以不用死的,你知道我的情况,我可以照顾好她,我早就跟她说过,只要她一心一意对我,我保证让她过上好日子的,她不信,非要和那个姓刘的搅在一起,现在弄得命都没了,唉……
我转头看向窗外,夜色越发浓郁,几点寒星散落在天幕上,清冷寂寞。街道上,人越来越多,前胸贴后背,街角的煨桑炉里,不时发出熊熊大火,瞬间又被负责消防的人浇灭,留下些火星一闪一闪。
回到出租房,停电,点了蜡烛,我把信取出来铺在小桌上,借着朦胧的烛光再次仔细看了一遍。信是用黑色的签字笔写的,字迹撩草,中间还有三个地方被泪水浸染了。
青桐姐:
你看到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去天上找妈妈了。你说得对,刘全就是个骗子,他说的话全是骗我的。他老婆没得癌症,在老家好好的,还怀上老二了。我们买的房子全是他和他爸的名字,银行的贷款让我还不说,他还背着我和圆圆乱搞。他说他是受不了我和其它男人在一起才那样的,都是假话。他逼我一直做冰妹,因为赚钱多,他在广东那边赌博欠了别人很多钱。他还害得我染上脏病,跟那些来撮粉的男人说,可以不带套子,只要多加两千块钱就行。如果我不答应,他就打我,我腰上的骨头被他打断了两次。青桐姐,你说对了,他根本就不爱我,只是把我当成赚钱的机器。他还录了很多我和其它男人的像,说我要是敢离开他,他就把录像给我爸看。青桐姐,我没有办法,只有死了他才折磨不到我了。
我亲爱的姐姐,有件事我对不起你,你上次染上毒隐儿的事情,真的是刘全他们干的。还有,你要注意何加进,何加进和刘全是结拜兄弟,他俩关系特别好。边巴死后,我有天听到何加进叫刘全回老家躲一段时间,他们俩个经常在一起滴咕事情,不知道在搞什么,他们也从来不让我跟别人说他俩结拜的事儿。
将来你如果需要什么帮助,可以找敬总,她虽然是同性恋,但人不坏,很讲哥们义气。你也替我跟敬总道个歉,谢谢她给我爸寄了修房子的钱。但我真的不喜欢女人,这辈子是没办法回报她了,希望下辈子能有机会报答!
你的朋友:龚小君致上!
我抹了把泪,双手放在信纸上看着结着冰花的窗。刘全和何加进居然是结拜兄弟,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事情。记得刘全初到拉萨,还是敬克英给按排的工作,看守停车场。而何加进最初是无无的恩客,矿山老板,财大气初,每次出现都是前呼后拥。这两个人,平时也没见有什么来往,怎么看都不像一路人,背地里居然是结拜兄弟!
边巴死时,姓何为什么要叫姓刘的回老家躲一段时间,除非他俩和边巴的死有关!如此一想,我打了个寒颤,飞快拿出电话按了“110”却没拨出去。仅凭这封信是证明不了什么的,如果边巴的死真与他俩有关,现在报警,结果只能是打草惊蛇,而受惊的蛇只会缩进洞里藏得更深。
冰冷的寒风从破损的小窗灌进来,格外刺骨,我的心里却烧着熊熊怒火,一头狂暴的野兽在心火里窜来窜去,紧握着拳头在屋里快速转圈。
不能冲动、一定不能冲动,冷静冷静……我不停地告诫自己,思想却一点不受控制,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拿手机。当手再一次要伸过去时,我飞快脱了外套,穿着秋衣冲进卫生间,打开水管,任冰冷的水冲刷自己,抱着臂,紧咬牙关,冻得嗽嗽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