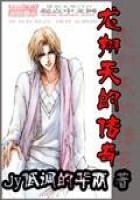菲勒看到沈晴的脸色转瞬间便变了两变,心里头也疑惑,禁不住开口来问,“怎么了?”
她的大齐话比之前有长进,吐字还算得上清晰,只是语气依旧生硬,尾调饶舌略往上扬了几分,依旧是北庭人的习惯。
不知是怎得,沈晴听见她这样来问,心里竟陡然也消了气。或许是因为她说话时的眼神里头带了担忧,表情也太过弱势,反倒显得有些卑微。沈晴舒出一口气,不多说什么径自走到偏座上来坐下,问一声,“你是从南疆过来的?”
“今天下午刚到,然后遇见了,遇见了你们齐国的四王子。”菲勒颌首回答,眼眸里微微有些闪烁,像是有所隐瞒。想来应该是被沈烨的人给抓了,又抹开面来讲。沈晴也不点破,应和地一点头说声“哦”。
菲勒一时也无话,两个人各自沉默干坐着,气氛一时有些尴尬。随着沈晴一起进帐的那位丫鬟倒是个机灵的,殷勤上来端茶倒水,碗碟相敲,汩汩的水流动静清脆地在帐子里回响开来,好歹算是打破了僵局了。菲勒咬唇思量了一会儿,抬眼望着沈晴,语气尽可能地放轻柔亲切了,想与熟客攀谈一样来问,“你,可好?”
“还好。”沈晴接过那丫鬟递过来的茶水浅酌一口,同样有些闪烁其词地来问,“是...是他叫你来的吗?”
“不是。”菲勒忽地抬起头来,语气焦灼,似是急于澄清。待意识到自己唐突时又重垂首低语,“是我自己要来的。寒哥他并不知情。”
听到这个答案,沈晴先是松下一口气,紧接着那种空落落的被遗弃感更深几许,勉强扯起嘴角望着菲勒,却来不知对谁一笑,“那他还好吗?”
“不好。”菲勒挺直了腰杆,目光决绝而坚毅,像是下了什么回不得头的决定,对沈晴回敬一笑讲,“他很不好。总一个人在书房,谁也不见。偶尔胡师爷进去找他谈事情,他也常常只是听,一句话也不讲。哦,对了,那是在镇南王府的书房。那座王府还没建好,可已经停工了。他叫匠人们都回家了。”
“为什么不建了?”沈晴口快问了一句,又戛然止口。再抬眼看那菲勒,果然她的眼中闪过一丝苦楚,只点头苦笑着重复,“嗯,不建了。哦,还有,那把刀也找回来了。”
“嗯?”
“就是那把黑色的长刀。寒哥用了十年的。现在也挂在书房。桌子上还摆着一把刀,小的。”菲勒抬手给她比划了一下长度,“大概一尺左右,上面雕着一条龙。那是你的吧?”
沈晴回想了一会儿,却是摇摇头,“不知道,我不记得。”
“那弓呢?也是黑的,巴掌那么大。还有锦盒,盒子里是银针一样的箭,有红的,黑的。这个还记得吧?”菲勒见沈晴眼神微微一颤,紧接着又别过脸蹙眉望向别处,不由微出口气,果然与她料想的一样。北野寒把自己关在书房,每次她进去送膳的时候,总见他望着这两样东西出神。她问过那个叫山豹的,尽管他每次支支吾吾或是打哈哈瞒过去,可她又不傻,一早便猜得那是沈晴的旧物。
说来也奇怪,若是以前,她必然会勃然大怒,会砸了桌子,抢了盒子,烧了刀弓来发泄,又或者威胁北野寒自己把这些东西都丢了。可她却只是默默地走开了,照旧地每日为他送去他根本不吃的膳食,然后再在他的沉默里微笑着转身,离开,然后关门。就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
不得不说,她装的很像。有时候甚至逼真到她真的看不见桌角的那两个锦盒,然后就会看到北野寒拿着汤勺伏在案上,一边专心致志地批阅折子,一边一口又一口地吃她带过来的汤羹。
有时候甚至还能看见他改着改着忽地皱着脸,孩子一样低头盯着那把汤勺,然后满是嫌恶地抱怨一句,“谁做的,真难吃”,这时她便赶紧跑过去给他捏肩陪笑,说“这是自己熬的,刚刚学会,还不熟练呢。”再然后的话...再然后他依然不肯原谅,会罚她再多多捶一会儿,然后依旧一口一口地将她带来的汤羹吃的一干而尽。
可是这种幻象她看到的次数并不多。因为不等着她跑过去为北野寒捶背的时候,她便常常会听到有人说,“还有事吗?”然后她眼前的景象就像终于曝露在光里的晨雾一样,一瞬便晕开去了。眼前依旧是低头伏在案上的人,咕咕冒着热气的汤,还有那把原封未动,雕塑一样坐在碗上的汤勺。她只能低下头,咧开嘴笑笑说,“没了呢,那我先走了?”
不出意外的话,这时候他常常能听到北野寒与她说的第二句话,那是从鼻孔里发出来的,他说,“嗯。”
那声音像是钟声一样低沉,也像石罄一样稳重,到了末尾的时候又带着鼓面余震的音韵。她总是会听完那最后一点尾音的。
可是又有时候,她又什么也听不见。因此她也常常恍惚,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听到的声音也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沈晴坐在下面,通红的烛火用光晕遮掩了菲勒的脸色。她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来看,可依旧看不真切,仿佛她整个人都与身上那件红容成了一体,随着那烛火一同模糊了边缘,虚幻的可怕。好像再过片刻,上面坐着的那个真真实实的人就会烟消云散一样在她的眼前骤然被那风吹散去了。
可帐子里并没有风。她忍不住出口,像是想要证明那人还是真实的,“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嗯?”菲勒也回过神来,借着摆正自己头冠的动作,悄然抹去不知何时溢出眼角的那滴泪。
“呃...我的意思是,你要在祁州城呆一阵吗?”沈晴觉出自己的话有些逐客的味道,又忙改口。
“你回去吧。”菲勒却避而不答,只说,“回北庭,回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