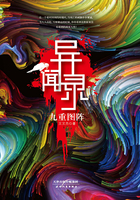二○○三年十月,我随步履蹒跚的爹离开天马山,开着车,迅速奔到岳屏公园前。我们下车,步入了衡阳岳屏公园。
这一天的公园里有众多天真可爱的孩子在玩耍,是老师带孩子们来公园秋游什么的。另一处林荫道旁,有几十名中老年女人在跳操。她们紧随录音机播放的旋律跳着。一旁是人工湖,有人在划船,欢声笑语随风飘来。岳屏山不高,一条褐色的石路直达山顶。两旁有很多树木,树木不是很古老的大树,而是几十年树龄的树木,大多是樟树,还有松树和法国梧桐树。那些古老的大树都于一九四四年夏被日本人的飞机、大炮炸毁了。爹要看“衡阳抗战纪念城”这座石碑。这座石碑建于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七年,在当时的人看来一定是很气派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自然有些小气。我搀扶着爹缓缓走到岳屏山顶,爹围着石碑缓缓转了一圈,我们在石碑旁的亭子里坐了下来。爹仍然举目久久地凝望着石碑,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转。我不敢打扰他,在一旁坐着。
“到处都是尸体,我军的,日本人的。到处、到处、到处都是。”爹深深叹口气说。“哦。”“从八月一日到八月八日,那八天是衡阳保卫战中打得最残酷的。”爹回忆着说。“那八天里,我只吃了几餐饭,后面的两天,连饭都没有吃,大家都饿着肚子打,饿着肚子与日本鬼子拼杀。都疯了。日本人疯了,我们也疯了。”
我看着爹,爹泪花花的。我生平第一次对爹产生了极大的尊重。爹回忆着说:“那些天里,日本兵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疯狂扫射。”我仿佛听见了炮弹爆炸声和机枪扫射的哒哒哒哒声。“弹尽粮绝啊,小毛。弹尽粮绝啊,小毛。”我只能表示理解地回答:“哦,哦。”“后来我们发明了抵制饿的土办法,”爹说,“我们勒紧裤带,就是把皮带系得紧紧的。如果皮带系到最后一个扣眼还不行,我们就把死去的弟兄的衣服脱下来,撕成布条,用布条捆紧肚子,减少胃活动的场地,以免肚子饿得咕咕叫。”
“战争是很残酷的。”“残酷、残酷——残酷!”爹一连说了三个“残酷”,“我们奉命死守,日军却要死攻,自然两边都变得穷凶极恶,都不要命。”穷凶极恶,我觉得爹这个词用得真好。
一群外国人走到了“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石碑前,叽里呱啦地说着话。我看他们是黄种人,说的却不是中国语,就问一个一时讲中文,一时又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说话的年轻女人:“请问小姐,他们是哪里人?”
年轻女人看我一眼,一笑——她笑得很好看:“日本人。”“日本人?”我愕然,“日本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年轻女人一笑:“来纪念他们的父辈。”我望眼抗战纪念碑,它突然变得很高大了,像把巨大的利剑,直刺天空。“这可是为战死在这里的国军官兵建的纪念碑。”我说。年轻女人又一笑:“来这里的日本人很多,这些年里,每年都有好几批。四月份时,我接待过一批日本游客,有三十多人,其中有几个日本老妇人还在山下烧冥钱。”
我看这些日本人,他们并不是老头。有一两个老太太,但也不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而是那种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另外都是一些中年男女,还有两三个较年轻的男女。“他们都是日本人吗?”我问转过头来的年轻女人。
“他们是日本人。”年轻女人回答我,马上又用日语与一个日本男人交谈。我走回到爹身旁,坐下,对爹说:“他们是日本人。”爹那花白的眉毛一拧,目光就一亮,扫了眼这群叽哩呱啦的日本人。“他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爹问了我问女导游同样的话。我望眼日本人,回答爹:“我不晓得。”爹说:“这些人都不显老,他们一定没打过仗。”也许他们的父辈在衡阳打过仗,也许他们的父亲或爷爷在衡阳负过伤,向他们提到了衡阳这个地名,或者是他们的父辈战死在衡阳,而这些日本人的后代便来祭祀。我告诉爹:“刚才女导游对我说,一些日本人来祭奠多年前战死在这里的亲人。”
前面有一处卖烟、饮料和食品的服务部,我走上去买了两瓶娃哈哈矿泉水。“这里经常有人来参观吗?”我问那个为我拿矿泉水的中年男人。
“有,有,经常有,”中年男人说。“都是些什么人?”
“什么人都有,”中年男人为我找钱,边说,“中国人,外国人。这是衡阳抗战纪念碑,总有一些人来看看。”
“有国民党的老将士吗?”我问。中年男人想了想,回答我说:“好像日本人还来得多一些。我在公园里工作了二十几年,经常有日本人来。国民党老兵也有来的,三三两两,有的还被子孙这一辈人搀扶着。”
“为什么日本人会来得多一些?”“这我就不晓得了。我听老一辈人说,衡阳保卫战当时震惊了日本,也震惊了全世界,”中年男人望我一眼,“我小时候听人说,抗战中日本人说‘要灭中国,先灭湖南’。”
“真有这句话?”中年男人咧开厚厚的嘴唇笑笑:“我听老一辈人聊天中说的。”“他们没有灭湖南。”我说。“他们灭不了湖南,”中年男人很自信的样子,边把零钱找给我,“日本人是痴心妄想,他们灭得了我们湖南?无湘不成军。抗战中,日本人在湖南打的仗最多,吃的亏也最多。中日最后一仗,是在雪峰山,日本人要过雪峰山炸毁芷江机场,国军官兵坚守着雪峰山,那一仗,我爷爷参加了,说打死了四五万日本兵。日本人硬是没打过雪峰山,最后退了。”
“那你爷爷也是国民党老兵啊。”我说。中年男人骄傲道:“是的,当时我爷爷是团长。”我很想带我父亲拜访一下他爷爷,忙问:“你爷爷还在世吗?”中年男人说:“我爷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死了,七十多岁死的。”中年男人又说:“我父亲是衡阳师专教历史的,他对历史有一些研究。湖南这个地方,在两千年前汉人很少,叫做蛮夷之地,都是些苗族、瑶族和土家族人。我父亲说大量的汉人大多是唐、宋、元、明、清这些朝代中陆续从北方迁徙来的。有官方有意迁徙的,如宋朝和明朝,朝廷曾下令安徽和江西的部分汉人移居湖南。另外一部分汉人则大多是兵、匪。我父亲说湖南人大多是兵、匪与少数民族通婚的后裔。血液里有爱讲勇斗狠和不屈不挠的一面。我是江永人。我的祖籍是山东青州。我的祖先随宋朝的军队来镇压湖南境内的瑶民起义,从此就在瑶民的老窝江永县定居了。很多那个年代的官兵,大多把瑶族女子抢来,通婚,有了后代后就索性不走了。”
我说:“你父亲认为,湖南人大多是北方移民?”“对,”中年男人说,“我父亲说,元朝统治的那一百年里,有很多优秀的有骨气的中原人士不愿在忽必烈的铁蹄下生存,带着家眷逃到湖南,在湖南隐居。还有各个朝代里的大量钦犯,犯了事杀了人,躲藏到湖南,从此在湖南生根、开花、结果。”
中年男人递支烟给我,自己点上支烟,又说:“我父亲说湖南人的祖先都是于各个朝代里不肯屈服和低头的人,他们因为不肯向朝廷低头就逃离了家乡,在当时相对没有被铁蹄侵略和蹂躏的蛮荒的湖南隐居了下来。湖南在历次改朝换代中,并不屈服于北方军队的铁蹄下,因为她不是处在中原地带,她一直就不是一个发展得不错的省份,这是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形成的。因此在改朝换代中几乎每次都是屈服于大势所趋的讲和中,没被铁蹄践踏和征服过。比如湖南和平起义就是例子。”
“所以湖南人不肯屈服?”我问他,“因为湖南人没有被征服过,不怕死,是吗?”
中年男人肯定道:“没有被征服过。好胜、好斗、好讲狠的血性就没被泯灭。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军当年沸沸腾腾且势不可当地攻入湖南,围攻长沙那么多天,最后以失败和撤退告终。当时的长沙很小,按说是可以将长沙的守军打得屁滚尿流的,但偏偏就没有,太平军反而损失了一个王——萧朝贵,把翼王石达开都气晕了。最终消灭太平军的就是湘军,湖南人。日本侵略军当年横扫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扫到我们湖南就卡壳了。日本兵四次进攻长沙,只有第四次才打入长沙。当时驻守岳麓山的是国民党第四军,军长名叫张德能,他直接受薛岳的副参谋长赵子立指挥。赵子立是个蠢人,不懂打仗,马谡似的人物,只会纸上谈兵。他命令张德能将炮兵部队的大炮搬到岳麓山的山腰上,隐藏起来,好突然百炮击鸣,发挥威力。但岳麓山上那么多树,炮兵根本看不见日本兵,日本兵却不从大炮布控的方向进攻,而是从侧面和绕过来从后面进攻,结果大炮丧失了威力。”
“所以长沙失陷了。”“有马谡似的蠢人,哪怕给你一个最好的地理位置和一百个师,你都会失陷。”“那是那是。”我说。中年男人脸呈骄傲地说:“林彪打四平时,我堂伯伯当时是陈明仁手下的一名营长,他那个营大都是湖南人,打得很顽强。林彪的部队四次打进四平,四次被陈明仁的部队打出来。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战场上,林彪唯一一次吃亏就是栽在湖南人陈明仁手上。”
这个中年男人是个战争迷和湖南自恋狂,对曾经发生的战事非常留意。中年男人见我很乐意听地看着他,就又说:“在解放军里,会打仗的湖南人也不少,彭德怀元帅打仗厉害,把胡宗南的部队打得焦头烂额。陈赓大将打仗也相当狠,他是黄埔一期生,还救过蒋介石。粟裕最了不起,我父亲说,粟裕是湖南将领里最会打仗的,他应该当元帅。毛主席没让粟裕当元帅。我父亲说粟裕于解放战争中曾指挥了几场非常漂亮的战役。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较量,是在江苏中部,接连打了七仗,七仗七胜,简称‘苏中七捷’,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好几个师和旅,十来万人。‘苏中七捷’就是粟裕指挥的。我伯伯说,粟裕有韩信的军事天才,又有张良的谋略。著名的淮海战役,就是粟裕打的。”
我瞧着他说:“你对军事史蛮感兴趣啊。”“我喜欢看这方面的书,”中年男人说,“我家里,这方面的书很多。”我看着抗战纪念碑,想着这位中年男人说的这些话,心里颇有感慨。中年男人的目光也随着我的目光投掷到灰色的纪念碑上,他略带几分钦佩地说:“日本侵略军打上海只死了一万多人,打我们衡阳却死了两万多人,还有两万多日本兵负伤,日军第六十八师团长,一个日军中将就是在衡阳负伤后,送回武汉医治时死的。日军第五十七旅团长,一个少将,被打死在衡阳。而守衡阳的国军,不过是方先觉的第十军,只有一万多人。”
中年男人又说:“日本人打我们衡阳伤透了脑筋。”我觉得有必要让他的脑袋清晰下,别太自大狂了,就遗憾地告诉他:“我想写一本衡阳保卫战方面的书,我查过资料,守衡阳的第十军中将军长方先觉是安徽人,第三师少将师长周庆祥是山东人,预备第十师少将师长葛先才是湖北人,第五十四师少将师长饶少伟是四川人,一九○师少将师长容有略是广东人。可惜这五位黄埔军校毕业的主要将领——他们因守衡阳有功,后来都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没一个是我们湖南人。”
中年男人点头:“那是,将领虽然都是外省的,但战斗的还是我们湖南人,打仗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大多是我们湖南人,将军们又不直接面对面与日本兵厮杀。”
我说:“战场上,指挥官很重要,指挥官是一支部队的灵魂。”中年男人答:“士兵更重要,士兵不勇敢、不顽强拼杀,你怎么指挥?”他不等我回答又说:“后来的国共两党开仗,指挥官还是这些人,为什么就打不赢共军?因为士兵和下级军官不愿卖力打。杜聿明、邱清泉、张灵甫、廖耀湘和王耀武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抗日名将,守衡阳的这五位将领后来也与共军打过仗,但结果怎么样呢?一败涂地。所以,战斗还是得靠士兵拼杀,共军一冲锋,士兵们就放下武器投降或溃逃,指挥官再厉害都没用。”
我觉得中年男人说的话有道理,还觉得他是个对军事感兴趣的人。“双方都很重要,”我说,“战斗的士兵和指挥打仗的将领。”
他揿灭烟蒂说:“是都很重要。战争让人只记住了将军们,却忽略了直接参与战斗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衡阳保卫战,如果没有顽强的士兵,是守不了四十七天的。”
为他说的这句话,我为父亲的这段光荣历史而骄傲。“我父亲当年就在这里打过日本人,”我指了指坐在亭子里发呆的老父亲,“我特意陪父亲故地重游。”
“您父亲当年也参加了衡阳保卫战?”“参加了、参加了。”我说。
中年男人的目光顿时就十分尊敬,从我的肩膀上越过去,钦佩地投到我爹身上。“请代我向您父亲问好,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中年男人一脸坦诚道。
顺便说一句,中年男人长一张方脸,脸色略有几分黝黑,目光却炯炯有神。现在我要将本书结尾了。假如一列火车是从广州开往北京,火车已过了长沙、武汉、郑州,此刻已过了石家庄,正向北京终点站驰去。还有一两个小时,乘客就要下火车了,那么我的读者也将合上此书,另一名读者可能会从你手上接过去,进行情感和思维的旅行。我总觉得阅读是情感和思维一起旅行。